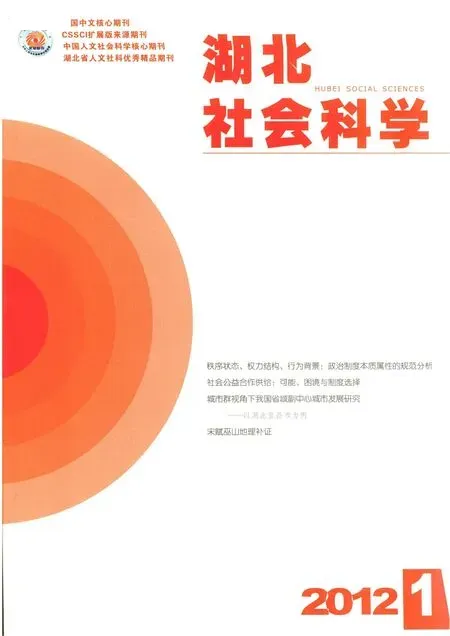汉语熟语生成的理论基础研究
2012-04-12王岩
王 岩
(南阳理工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6)
汉语熟语生成的理论基础研究
王 岩
(南阳理工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6)
从发生学的观点分析,熟语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受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汉语熟语必然是跨学科研究,我们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等来探讨其产生的理论基础。
汉语熟语;语言学;哲学;理论基础
熟语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受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汉语熟语必然是跨学科研究。首先,汉语熟语属于语言学范畴,研究它的生成必然与语言学有割不断的联系,而熟语所表现的民族性、文学性、具象性、美学性、地域性等,显然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等密不可分。此外,由于语言与宗教、文化等相关学科密不可分,汉语熟语的研究可能牵涉到人文科学所有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这里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等来探讨其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语言学基础
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本质要素,此外还有两个非本质但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文字和修辞。因此,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和修辞等五个要素也就成了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重要内容。自然而然地也就形成了语言学的几个分支: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和修辞学。近年来,由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人们研究在各个领域的不断深入,各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语言学研究更丰富、细致、科学,又产生了语用学、计算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或学派。
这些不同分支的学科,有的是以研究对象来分类,有些却是研究目的定位不同,或以采取的研究方法或手段不同而形成的。有人认为,“凡属语言研究,不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研究,不外乎规范、描写、解释三种”[1]“当代,从研究方法的取向上看,语言研究实际上存在四种主要趋势:描写的、分析的、形式的和技术的研究。”[2]我们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比较侧重于描写的研究,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和修辞学等是侧重于描写语言是什么,而西方的语言学研究侧重于分析的、形式的研究,善于经过数学的、逻辑的演算来对自然语言进行形式化的处理,分析揭示语言的“为什么”问题。我们现代的语言学研究开始重视分析的研究,比如: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等,随着计算机的迅猛发展和现实生活的不可替代性,对语言在计算机运行的技术程序研究也日渐升温。
汉语熟语是汉语言的精华,是汉语的组成部分,我们对汉语熟语进行研究,必然要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关于熟语的界定、熟语的概念、熟语的分类、熟语的特征、熟语的功能等侧重于描写的研究方法,可以从汉语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修辞学等语言学基础理论来对汉语熟语进行研究;而对于汉语熟语的生成的文化机制、生成的文化理据、熟语的发展演变侧重于分析的研究,可以依据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等理论基础,比如,对于汉语熟语语义的形成应该用认知语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
二、文学基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基础。汉语熟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很多层面上都是得益于中国文学几千年的深厚的积淀及结晶。
第一,汉语熟语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
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从发生学观点看,诗歌和谚语的生成的基础是相同的。都是起源于生产劳动,在文字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或琅琅上口的口头话,表达出去,互相交流传诵。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有这样的诗句:“朝跻于西,崇朝其雨”、“有渰萋萋,兴雨祁祁”(《诗经·鄘风·大田》),这其实就是谚语,前一句是以虹出现的方向测定天气变化的谚语,后一句是用行云测雨的谚语;还有《诗经·幽风·七月》里“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等其实也是总结农耕及生产经验方面的谚语。你能说这些句子是诗歌?是谚语?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谚语,以及后来产生的歇后语、俗语等熟语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形式。之后,随着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按照各自的特点发展,与诗歌等文学形式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按照发生学的观点看,应该称为同源,就好像同源器官或是同源的行为方式,会显示出相同的躯体或基本构造,因为环境的不同而进化成不同的外形或功能。
第二,大量的汉语熟语来源于中国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从古代神话、先秦散文、汉辞赋、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现当代小说,以及传说、寓言、文学批评等文学形式丰富多样,所展现的内涵世界多姿多彩。这为大量汉语熟语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基础。其中,很多熟语原句都来源于文学作品。比如,格言因是以书面形式流传的,所以大多是来自古代典籍或名人作品。“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等都来源于孔子《论语》,“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出自《荀子·劝学》,“有志者事竟成”出自范晔《后汉书·耿弇传》;谚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源自《楚辞·卜居》原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源自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词;成语“顺水推舟、过河拆桥”源于元代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等。也有很多是对文学作品原句进行加工,或对原文进行概括而成。比如:成语“举一反三”从《论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剪裁而成;成语“瓜田李下”是从古乐府《君子行》“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中把“不纳履、不整冠”剪裁后而得。成语“揠苗助长”源自《孟子·公孙丑上》、“自相矛盾”源自《韩非子·难势》等等,是对文学作品中所记的故事的综合概括而来。歇后语“孙猴子变山神庙——漏了尾巴”、“周瑜谋荆州——赔了夫人又折兵,刘备借荆州——有借不还”等是对文学作品中某些情节的概括和总结而形成的。还有部分熟语是在原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也就是指对于原有的文学作品中没有的而是老百姓根据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而赋予的内容和情节,或是对原有人物性格的深化和细化,用熟语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歇后语“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关公卖豆腐——人硬货软”、张飞遇李逵——黑对黑”“黛玉焚稿——忍痛割爱、贾宝玉看林妹妹——一见如故,”,俗语“宁愿挨一刀,不和秦桧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谚语“要学桃园三结义,莫学瓦岗拜把兵”“尽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败走麦城”,等等。这些二次创作的熟语体现了老百姓的价值观,既有通俗的教育意义又幽默生动,从客观上也起到了宣传、传播这些文学作品的作用。
三、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汉语熟语是一种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汉民族人民生活状态和心理特征的语言现象,它的生成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一是保留、传播社会经验是汉语熟语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心理。
汉语熟语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心理是保留、传播和利用社会经验。很多熟语基于此而不仅代代流传下来,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力和最有效地传播工具。
就拿谚语来说,谚语的产生是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有必要也必须把自己在生产劳动中获得的知识,积累的经验和体会,传播给社会,传给后人,人们用口耳相传的办法来传授,形成了很多谚语。比如,生活谚传授生活的经验、体会以及传统的人情世故处世之道;农耕谚是传授人们在农业耕作过程的知识和经验等等,自然谚传播自然知识的,帮助后人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还有风土谚、事理谚、社交谚、修养谚、工商谚、文教谚等等,谚语传授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可以说凡是人们所接触到的事物,认识到的领域,谚语中都有反映。所以说谚语是民间传播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最有力的工具,被人民群众称为“生活百科全书”和“简明百科全书”。
再比如,近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对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生活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而由儒家学说和思想产生的熟语起到了传播和加深对其认识的作用。就拿儒家经典的《论语》一书,书中的很多言论被广泛地而且频繁地引用,而由此形成为谚语、格言、成语、惯用语等,据粗略统计,来源于《论语》的熟语达150余条之多。如:犯上作乱、巧言令色、言而有信、三十而立、知之为知之、见贤思齐、文质彬彬等。这些熟语在形成的过程,在使用的过程,也就是这部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对社会、对不同层次的人群产生影响的过程,也是对儒家思想学说传播的过程。
同时,汉语熟语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的过程,那么熟语就是有时间性的,所谓时间性是指熟语从非熟语到熟语的时间过程,有些熟语是稳定的,跨越时间较长,那么它保留、传播自然知识或社会经验的时期就长,也说明它的生命力是强的。而有些熟语只能在某一时期起到传播社会知识的作用。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广泛使用的熟语“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造反派”“关牛棚”“游街示众”等等。另外,熟语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经验的传播是有空间性的,我们认为这个空间性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地域空间,一是指不同文化层次空间。也就是说,不同熟语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层次对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的保留、利用和传播是不同的。谚语、俗语、歇后语和惯用语主要来自人民群众对自然和社会经验、认识的概括和总结,主要在人民群众中保留使用和传播,主要传播渠道是口头,成语、格言、锦句主要来自书面,内容和寓意要深刻和丰富些,主要在教师、学生等具有一定文化层次人中传播和使用。同时,不同的地域由于地理、气候、文化习俗等不同,还表现为在一定区域内传播的文化和社会知识。当然,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和交通发达,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群交往和交流日益加深,这些知识和文化的传播的空间性日益缩小。
二是熟语的形成是喜新求异心理和仿效从众社会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断创新是人类普遍的社会心理。人们往往希望通过与众不同的个性显示自身的价值和追求。这种心理表现在语言活动中就是追求语言上新奇求异,创造新词语、新格式或赋予词语以新的内容。喜新求异是汉语言创新活动中的一个社会文化心理。这也是汉语熟语形成最初的社会心理。没有这种心理,熟语不可能产生,没有这种心理,语言不可能发展。在这种心理下,也就出现了一个个色彩鲜明,标新立异的汉语熟语,表现形式的多样奇异,有三字格、四字格、有短语、有句子,还有世界上唯一的歇后式或说谜语式的语言形式,等等。都是人民群众喜新求异的心理产物,于当时的时代给人耳目一新、与众不同的感觉。
同时,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言语等等活动中还存在着模仿从众的行为。这种从众可能是不自觉地,在言语生活中,当人类个体发觉某人(或某作品)的言语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时,就会因喜欢该言语作品而倾向于接受其影响,并采取与之相类似的言语行为;也可能是有意识的,因为喜新求异,创新势必突出个性,而突出于社会之外,显得另类,“树大招风”,造成一种不安全感,为了躲避这种不安全感,于是便有了从众的行为和语言,使自己的行为和语言符合群体的标准和规范或习惯。
汉语熟语就是在这两种社会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着、发展着。求新求异心理促使人们不满足于一般使用的语言或语言形式,于是新词语或新的语言形式出现了,表达打破了常规,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它必须符合人们共同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就会被人仿效,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和传播,从众心理促成此词语在更广泛范围内传播和接受;当这个词语具备熟语的特性,一个熟语便形成了,然后再继续被使用和传播,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熟语随之也发生着形式或内容的变异或泛化。
如果没有求异求新心理为动力去创新,就没有语言的发展变化,更没有熟语的出现。但如果没有从众心理为动力,创新的语言会一直停留在新奇的阶段,永远不会被认同,不会被传播,更不会发展为熟语。当然熟语生成发展的过程不是那么有次序的变化,而是一个相互交叉、复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心理相互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哲学基础
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和摇篮。我们国家语言学研究主要注重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对语言进行哲学的研究还很欠缺或者说很滞后。许嘉璐先生曾说:“千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和理论的建设……大约从乾嘉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了哲学,重实证而轻思辨,重感性而轻理性,不善于把实际已经使用的科学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认识论去阐释和论证这些方法……直到今天,语言学界,特别是训诂学界,偏重考据忽视理论的倾向犹在,懂得哲学,能够沟通哲学和语言学的人很少。这恐怕是我们的语言家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因。……我们的语言研究既缺少东方哲学的底蕴,又遗弃了古代语言研究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在汉语研究中,我们太注重技术性、太偏爱技巧了,没有花大的力气发现其中包蕴的哲理……可以说,我们的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心太少了,而我们的语言学家对哲学的了解就更为可怜。”[3]然而“语言哲学在20世纪一直是英语国家的哲学家的重要研究领域”。[4]可以说,对语言的哲学研究应是我国当今语言研究一项重要使命和重要课题。
哲学是汉语熟语生成发展的内在基础。
“社会历史因素固然是词语发展、词义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其内因来源于使用者的认知思维。历史社会因素只能说明变化的必要性,而认知因素才能说明词义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可能性,”[1]人类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来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转喻(Metaphor))和隐喻(metonymy)是最基本的两种手段;语言深深扎根于认知结构中,隐喻和转喻这两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词汇和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对于汉语熟语来说,尤其如此。隐喻和转喻作为一些常规化的或无意识的映现模式,不为我们所察觉,但却是汉语熟语产生、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一是我们汉民族本身就擅长于具象思维方式和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去类比、意会,擅长于用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二是隐喻和转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为熟语产生发展提供了一种手段、一种理据。如果没有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思维,许多汉语熟语就不会这样产生和发展。比如:成语“入木三分”。这个成语来源于唐·张怀瓘《书断·王羲之》:“王羲之书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此语本义是说王羲之把字写在木板上,字迹能投入木板三分深,形容其书法笔力强劲。本身已经是具有比喻和非字面的意义,后使用语境超越了原来的语境,用来说看问题、见解和议论深刻和精辟。也就是说在目标语(看问题,分析问题)和来源域(书法笔力)之间具有了映现的对应关系,“入木三分”所指的范围扩大了,意义丰富了,可以形容书法,也可以形容看问题的尖锐和深刻,也可以形容人物刻画的深刻等等。正是由于词语意义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人们使用也就日益频繁,它就越具备了“熟语”的“特质”,于是“入木三分”也就成为熟语了。
另外,在许多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富有哲理的熟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再灵巧的人也做不出饭来,说明了物质在先,意识在后,没有物质就不会产生反映物质的意识,充分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只要有志气,有毅力,困难一定能克服看,事情一定会成功,这说明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谚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弓满则折,月满则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成语“苦尽甘来”、“否极泰来”、“乐极生悲”中的“福与祸”、“乐和悲”、“苦和甘”、“高和低”“满和亏”“盛和衰”等等,说明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是彼此对立且又统一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水滴石穿”一滴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长久地滴却能穿透坚硬的石头,所以量的积累会引起质变。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格言“铁棒磨成针,功到自然成”“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锦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俗语“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等熟语都是在质变与量变关系的哲学原理基础上生成的。等等。当然并非人们学习了懂得了这些哲学知识,然后才创造了这些熟语,而是人们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了,认识、体会到了这些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规律,或人和客观世界关系的原则,然后用具象、隐喻的思维方式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这些抽象的哲学理论,这个认知过程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这也体现了“体验哲学”(经验现实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认知的无意识性”。
[1]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周建设.语言研究的哲学视野[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2).
[3]许嘉璐,于根元.语言哲学对话(序)[J].语文建设,1998,(5).
[4][美]A.P.马蒂尼奇.语言哲学[M].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H033
A
1003-8477(2012)01-0136-03
王岩(1970─),女,南阳理工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1BYY005)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