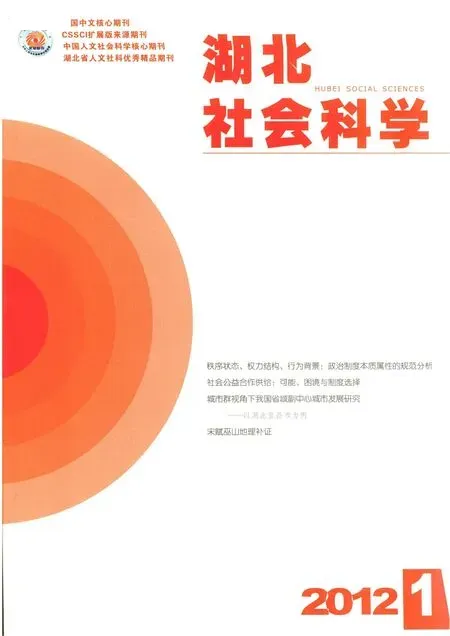秩序状态、权力结构、行为背景:政治制度本质属性的规范分析
2012-04-12马雪松刘乃源
马雪松,刘乃源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所,北京 100732;2.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秩序状态、权力结构、行为背景:政治制度本质属性的规范分析
马雪松1,2,刘乃源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所,北京 100732;2.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制度作为人类的实践性结果,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根本背景,也为政治交往和公共领域提供了必要的媒介。政治制度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及研究领域进行现实考察与理论探究的重要对象,因而对于政治制度本质属性的揭示和阐述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规范分析的研究视角出发,突出强调政治范畴的核心要素及制度概念的基本涵义,能够揭示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包括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方面:政治制度是政治领域的秩序状态、政治权力的结构与安排、约束和引导人类行为的背景性因素。
政治制度;秩序状态;权力结构;行为背景;本质属性
首先,政治制度对秩序尤其是政治秩序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秩序的确立。基于这样的分析视角,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政治秩序的确立过程。一方面,从政治秩序的实现前提来看,政治秩序需要某种规则来约束、引导、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行为,因而政治秩序在形式上表现为政治规则的制定、实施并获得相应遵守。阿伦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在缺乏一个普遍原则的条件下,不可能确立起任何的秩序”。[4](p8)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理解政治秩序的确立,需要理解作为政治秩序核心内容的政治统治以及国家的实质功能。恩格斯在论证国家的起源时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p170)从中可以发现,其一,政治制度的内涵包括具有约束作用并被强制实施的规则性要素,政治制度发挥作用就反映了社会生活在整体上或行动者在某一层次或方面的交往从无序转为有序。其二,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之内的论断,不仅探究了国家产生的根源并深刻揭示出国家的本质,这实际上也是将政治制度理解为构成政治秩序的主要力量。“国家通过自己的权力系统和法规体系建立的秩序,是把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合法化、制度化,把阶级冲突保持在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秩序所允许的范围以内”。[6](p12-13)根据这样的认识,可以认为作为国家统治重要形式的政治制度不仅蕴含着阶级统治的实质,而且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秩序状态的确立。
其次,政治制度所蕴含的秩序内容还体现在制度研究者关于秩序的理论阐述。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者倾向于将秩序状态同某种制度安排等同起来。例如,韦森在其研究中尝试性地将制度同秩序予以整合,并提出“制序”这一范畴来对译英文中的“institution”。具体而言,“制序”是“由规则调节着的秩序”,这就是习惯、习俗、惯例在成为制度以后并未失去作为一种秩序和非正式约束的特征,而是潜在地包含在作为单一规则或规则体系的显在性制度之内,同时与其他制度性规则同构在一起。因此,“制序包括显性的正式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即制度,也包括由隐性的非正式约束所调节的其他秩序即惯例”,“制序是规则中的秩序和秩序中的规则”。[7](p63)这表明制序作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复合体系,不仅构成了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也使制度概念的范围得到一定的扩大。尽管这是建立在演化博弈分析基础上的制度观,但无疑对制度的概念阐释及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外,一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者十分重视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张力,认识到由一定规则构成的制度不仅有助于促成合作均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均衡、制度和秩序三者本身也具有内在一致性。[8](p10-11)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奠基者马奇和奥森指出,政治理论尤为重视政治制度在创造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强调制度结构将秩序性要素施加于人类生活这一重要过程,因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视域下的制度包含历史秩序、时序秩序、内生秩序、规范秩序、生活秩序和象征秩序等六个方面。[9](p743-744)
二、作为权力结构的政治制度
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政治制度既可以是得到实施和贯彻的规则也可以是施加强制性影响的组织,能够对政治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因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政治利益分配本身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本质。“政治制度可以看作是政治利益博弈的结果,政治利益在不同政治主体或利益集团中的分布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本质与形态,反过来,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又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实现利益的规则”。[10]这种认识尽管深刻把握了政治利益及其分配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政治权力对于根本性利益分配的决定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政治权力构成了作为利益分配机制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权力是理解政治制度的实质要素”,[11](p32)从这个思考角度出发,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一种结构与安排,同时也是政治制度本质属性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在萨拜因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社会中的某些制度称为政治制度,因为它们代表着权力或权威的一种安排。这些制度被看作是权威的合法的运用者,它们运用这种权威为整个社会作出各种决定(如果在一定的地区或在一定的人类集体中不存在这样的制度,那也就很难说在那里存在着一个真正的社会或政治共同体)。集体和个人当然非常注意这些制度所采取或作出的决定,因为他们的利益和目的将受到这些制度的影响”。[12](p4)
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强制性政治权力的结构与安排,这也可以概括为政治制度是一种权力结构,对于这样的认识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政治制度就其含义而言,本身就同权力结构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一方面,政治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形式,它意味着人们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涉及强制性权力的运用,这也是政治学者所强调的“政治意指权力的实施”。[8](p52)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和层次性特征,政治制度也被看作是政治权力在结构性或框架性要素中的存在与实施,因而可相应地将政治制度概括为某种权力结构。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权力结构是政治制度本质属性的重要方面,并不是说两者具有等同的含义,这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内涵要比政治制度更为丰富。另外,从个体与结构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制度作为某种权力结构,并不是仅仅坚持政治权力在结构性要素中分布这一观点,而是同时坚持政治权力蕴含于制度性规则之中并在制度性组织中实施,这对个体或集体行为乃至能动性而言无疑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安排与运作。
其次,从现实政治运作方面考虑,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力具有明显的伴生关系。政治制度的生成、维系、变迁同政治权力的实施存在直接关联,政治权力在产生、配置和运行方面也受到政治制度的根本影响。一方面,政治制度存在的意义就是围绕政治利益的分配,以强制性力量的运用作为必要措施与最终手段,从而实现某种政治秩序。这种强制性力量实际上就是政治权力,围绕着政治权力进行的斗争也往往导致以规则或组织为基本形式的政治制度的创设与演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者瑟伦与斯坦默指出,“制度在针对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创造出来或发生变迁”。[13](p22)其他政治制度理论者也认为,“制度产生和消亡的过程既涉及新的观念,也涉及新的权力架构”。[14]另一方面,政治制度不仅受权力运作方式的塑造,也对政治权力的产生、分配、作用方式及范围发挥重要影响。例如,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中蕴含着明显的权力结构,而这一权力结构又是由作为政权组织形式的根本政治制度所规定的。[6](p28)因此,根本政治制度不仅对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产生影响,也必然塑造其他层级和方面的政治权力运作和分配方式。这样的认识还充分体现在制度理论者奥菲的论述中,“制度同社会权力的产生、分配、实施和控制密切相关”,“制度通过某种机制影响社会权力在行动者之间的分配”。[11](p1)
三、作为行为背景的政治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p56-60)这揭示了作为行动者的人们通过能动性的发挥和交往性的行动构建了社会生活,社会并非个体在数量上的加总,而是由实践性与能动性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产生的。有研究者在这个意义上指出,“社会既不是简单地从个人开始的,也不是外在地给定的所谓整体”。[16](p11)由此可见,一方面,人们作为具有意志的实践者,通过发挥能动性而将目的加诸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人们的能动性和实践能力受到生产方式及社会交往的限制。政治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某种结果和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它同人类能动性具有密切关联。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实践的结构模式,尽管受到能动性和实践活动的影响,但也构成了对于人的行动乃至能动性产生约束或引导作用的背景性因素。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很多学者指出制度对理性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施加重要影响。例如,历史制度主义者霍尔和泰勒认为,“制度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行为”。[17]日本政治学者加藤淳子也指出,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均关注“制度是如何塑造政治行为和后果的问题”。[18]政治制度作为约束和引导人类行为的背景性因素,对此可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政治制度对个体或集体行动本身具有约束作用。一方面,作为规则的政治制度能够限制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活动方式。具体而言,制度性规则通过限制可选行动方案的范围、约束人们的交往模式、塑造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结构,会对政策产生明显的影响,有理论者将此概括为“作为一套规则的制度决定了个体行动聚合为集体决策的方式”。[19](p179)在他们看来,具有执行效力的规则不仅限制了个体行动,而且使个体行动在制度性规则的约束下转化为特定类型的集体行动,这既是对个体行动的限制,也是对集体决策构成的约束。另一方面,部分坚持文化因素具有重要作用的学者认为,由于政治制度在规范层面上具有“适宜逻辑”的特征,也就是政治制度“对于那些位于社会系统之中并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们来说,界定了他们正当的和可预期的行为”,这导致行动者在政治制度的影响下表现出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20](p239)这说明了在行为选择受到限制的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实际上也受到了某种约束。
其次,政治制度对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激励结构或偏好具有约束作用。随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不断发展,制度理论者在思考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及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时,不但承认外衍性偏好受结构性或程序性制度的塑造,还认为某些偏好可能内生于组织性制度之中。具体来看,部分经济学者如诺斯关注制度对偏好的塑造作用,强调政治制度所蕴含的规则要素能够塑造相关行动者的激励结构,“制度为经济提供了激励结构,制度演化方式因而塑造了长期性经济偏好”。[21](p242)同理性选择理论者的分析方式存在一定差异的是,一些政治学者根据规范理论指出,“利益和偏好在人类行为的制度背景下产生”。[9]这意味着行动者在政治制度的规范作用下往往根据角色与情境的关系来界定适宜行动,从而在分析中把利益与偏好视为内生性要素。当行动者的激励结构与偏好受到制度限制,此时能动性的发挥无疑也受到了制度性因素的约束。
再次,政治制度对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具有引导作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认为,对于个体或集体行动者来说,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行动者赋予了政治制度阙如情况下不可能具备的行动能力。一方面,政治制度以促进合作的方式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为行动者发挥能动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塑造了行动者的意图,有助于引导行动者更好地发挥能动性。“制度不但允许人们通过协调其行为以达成目的,还可以创造并改变目的本身”。[11](p72)当行动者的意图由于制度的塑造而使能动性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能动性本身得到了积极和有效的引导。
最后,作为行为选择背景的政治制度对于能动性而言并非是一种外在的给定性力量,而是融入了人类能动性的实践结果。政治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由人类创设的,但具有创造能力的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能动地改变政治制度。一方面,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人类实践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14](p77-78)萨拜因也认为,“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两者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是人这个物质实体的延伸部分,人类团体经常创造制度和惯例”。[12](p4)另一方面,人与制度之间不断地发生交互性作用。“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22](p3)实际上,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中,并没有将制度或结构性要素视为决定个体行为的最终因素,也拒绝把个体能动性看作独立于制度约束或决定结构性要素的先在力量。由于人类行动与制度结构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所有社会生活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在强调制度结构的约束性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同时肯定人类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23]
[1]Friedrich 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Stephen Skowronek.Order and Change[J].Polity,1995,(1).
[4][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韦森.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Karol Soltan,Eric M.Uslaner,and Virginia Haufler.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der[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
[9]James G.March,Johan P.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3).
[10]曹晓飞,戎生灵.政治利益研究引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1]Ian Shapiro,Stephen Skowronek,and Daniel Galvin.Rethink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Art of the Sta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12][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M].盛葵阳,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3]Sven Steinmo,Kathleen Thelen,and Frank Longstreth.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4]James T.Kloppenberg.Institutionalism,RationalChoice,and Historical Analysis[J].Polity,1995,(2).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M].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Peter A.Hall,Rosemar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s [J].Political Studies,1996,(1).
[18]Junko Kato.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ity in Politics:Three Varieties of Neo-Institutionalists[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2).
[19]Elinor Ostrom.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M].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2.
[20]Talcott Parsons.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M].Glencoe:Free Press,1954.
[21]Uskali Maki,Bo Gustafsson,and Christian Knudsen.Rationality,Institutions,and Economic Methodology[M].New York:Routledge,1993.
[22][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3]马雪松.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张力与理论取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1).
D03
A
1003-8477(2012)01-0018-04
一、作为秩序状态的政治制度
马雪松(198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讲师。刘乃源(1982—),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项目编号:11JZD030;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项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1QY032
责任编辑 申 华
制度作为人类交往的产物和实践性结果,一直是社会科学考察的主要对象,因而在政治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发展中,制度分析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一般而言,可以把政治制度理解为围绕利益的竞取与分配,以政治权力的强制执行作为保证,同法规制定和政策选择活动紧密关联的规则和组织的结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制度在发挥效力的过程中对人的行为产生限制或塑造作用,从而影响行动者能动性的发挥。基于这样的认识,从规范分析的研究视角出发,突出强调政治范畴的核心要素及制度概念的基本涵义,能够揭示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主要表现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方面,即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意义的秩序状态,是强制性政治权力的结构与安排,还是对个人及集体行为与能动性产生约束与引导的背景性因素。
人类社会的组织建构与发展延续无法在始终动荡不安和争斗不休的环境下进行,因而秩序对于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来说极为重要。哈耶克指出社会生活之中存在着某种具有一致性和持久性的社会秩序,该秩序如果不复存在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社会成员不仅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他们的基本需求也往往难以实现。[1](p160)也有学者从积极方面指出秩序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一个维持着基本秩序的共同体之中,人们通过对未来的合理预期能更好地与其他社会成员开展合作,这意味着秩序有助于增强人们之间的相互信赖,从而降低合作行为的成本。实际上无论在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中,制度的重要性都突出表现为它对秩序的促进作用。例如,制度经济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所著《制度经济学》一书的副标题就是“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这是由于“制度的关键功能是增进秩序,它是一套关于行为和事件的模式,它具有系统性、非随机性,因此是可以理解的”,通过审视制度在经济交往中如何促进秩序的实现,考察共同体内部个体或集体行动者在面对资源稀缺性问题时的行为模式,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秩序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2](p33)此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者斯科伦内克也指出对于关注政治制度的研究者而言,几乎所有研究框架都把制度视为秩序的支撑性力量与政治生活的规制性结构,因此政治制度“将各种人类行为融入政治过程并协调政治利益,从而使行为同组织化的系统连结起来”。[3](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