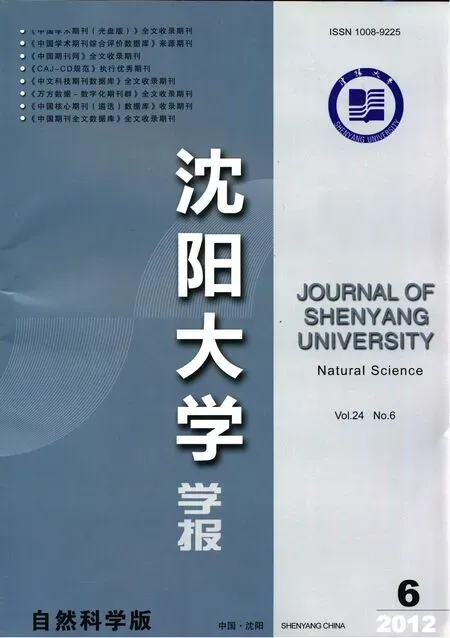论唐诗在日本传播的历程及文化意义
2012-04-12徐臻
徐 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文学都离不开传播活动。唐诗作为人类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社会性与符号性注定了其传播的势在必行。日本学者何世宁编撰《全唐诗逸》广泛收集日本逸散唐诗,加上《怀风藻》、“敕撰三集”等诗集,共同构成了现存于日本的海外唐诗。然而,至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真正从文化传播角度研究唐诗在日本的传播,中日学者间也没有实现唐诗研究视界的交融与对话。本文试想在唐代对外交往史的研究中探索唐诗在日本传播的历史轨迹,补充学术界对海外唐诗研究的不足。
一、唐诗向日本传播的历史原因
1.唐王朝的政治教化
以中国为中心政治册封体制的形成是唐诗得以传播日本的政治因素。唐朝初期,日本被纳入唐王朝的册封体系内,日廷竭力模仿唐朝,力争与唐同轨。大化改新后,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逐渐形成,而律令制官员最重要的修养是以诗文为主的各种政治文学知识。唐诗在日本宫廷的仪式和宴会中被反复吟咏并被赋予政治意味。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阐述政治与汉诗的关系:“于是三阶平焕,四海殷昌,旒纩无为,巌廊多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惟百篇”[1]3,汉诗是粉饰政治、歌颂太平的政治工具。《凌云集》序文还引用曹丕《典论》中的观点指出:“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1]47,强调文学的永恒性与政治性,认为诗文有经营国家的统治力。
2.儒佛思想的东传
儒学和佛教的东传促进了唐诗在日本的传播。儒家的史学观和文艺观是唐诗传播的思想基础。刘知几在《史通》中比喻经(诗)与史的关系:“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2],认为诗产生的实质是史的副产品,诗集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史书的一部分。日本最早的诗歌也收录于日本第一部史书《古事记》中。而唐代的“文以载道”思想认为儒家之道是文学表现的唯一使命。这样的儒家文艺观也影响到日本,《经国集》序这样阐述:“故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1]109。
佛教的东渐虽稍晚于儒学,但汉译佛经在日本的普及对唐诗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僧侣几乎都是直接阅读汉文佛典,很少翻译为母语文字。且奈良平安时期佛教鼎盛,大批日僧入唐求法,空海、最澄、圆仁等“入唐八家”先后将大量唐人诗集传入日本,加速了唐诗的越境流动。如圆仁的《入唐新求圣书教目录》记载:法华经二十八品七言诗一卷、私(杭)越唱和诗一卷、诗集五卷、杂诗一卷、自家诗集六卷等唐诗集传入日本[3]。
3.汉文教育的普及与汉字的特点
汉文教育的普及是唐诗传播的前提。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朝廷在京城设大学寮,地方上设国学,形成了覆盖全国范围的汉文教育体系。大学讲授的内容是儒家经典,《孝经》和《论语》为必修课。还学习经学著作,《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4]。日本还设科举制,京城大学寮的学生凡是通二经以上且愿意为官者,可以被推荐给太政官,参加式部省的“登庸试”,跻身仕途。
汉字自身的特征是唐诗得以广泛流布的内在原因。日本为缩小与先进的唐文化间的差距,自觉接受汉字。但日本人并非依靠翻译汉文,而是直接阅读汉字通达文意。日本人创造了音读法和训读法,不知道汉字读音的情况下也能阅读、创作唐诗。音读是选取与中文发音最接近的日语读音拼读汉文词汇,所有汉字都能通过音读获得固定的日语发音。训读是用日语发音拼读汉字。通过训读,所有的汉文都能直接转换成日文。而音训相交的“汉文和读”则是阅读唐诗的基本方法,古代日本人就是利用这种方式阅读和创作唐诗的。
二、唐诗在日本传播的历程
1.日本汉诗之缘起
邻近的地缘关系使汉诗在日本起源较早,《日本书纪》显宗天皇元年(485)三月条记录了天皇幸后苑开曲水诗宴的事件[5]。这是日本天皇附庸王羲之等东晋名士开曲水宴赋诗吟咏的风雅韵事。若这一记载属实,则是现存最早的日本人吟诗的文字记载。《怀风藻》序文记载,日本汉诗起源于天智天皇时期。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说:“天智天皇登极,而后鸾凤扬声,圭壁发彩,艺文始足商榷云。”[6]667年,天智天皇迁都近江,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开宴赋诗,吟诗之风日盛。669年,唐朝使节郭务悰率二千人访日,恰逢此等盛世自然少不了诗文唱酬。可惜这时的“雕章丽篇”“时经乱离,悉从煨烬”,均失于“壬申之乱”。
白村江海战后,赴日的百济人对日本汉诗的发轫功绩不小。支撑近江文坛与教授皇室汉诗文的正是百济移民知识分子。《怀风藻》大友皇子传结尾处有“立为太子,广延学士沙宅绍明、塔本春初、吉太尚、许率母、木素贵子等为宾客”之语。据《日本书纪》天智十年正月条记载这五人均是被冠以学士之名的百济移民,他们共同教授皇子大陆的“文章学”。作为成果,皇子“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即大友皇子的《侍宴》诗:“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1]10总之,日本汉诗的起源与东亚诸国的交涉往来密切相关。日本人在与唐朝、朝鲜等国交错的多重的交往中受容了唐诗。
2.唐诗的“顺流”
正如水从高处流向低处,唐诗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入唐的日本使节及留学生。唐日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日本拜请萧颖士为师。萧颖士以善人乐教闻名,日本愿以举国请为师。萧颖士的弟子贾邕在《送萧颖士赴东府序》中言及:“顷东倭之人,逾海来宾,举其国俗,愿师于夫子,非敢私请,表闻于天子,夫子辞以疾而不之从也”[7]。《旧唐书》又载:“是时外夷亦知颖士之名,新罗使入朝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其名动华夷若此。”[8]这里愿师事萧颖士的不是日本而是新罗,但无论是日本还是新罗争相师事萧颖士,都证明直接的人员往来是唐诗流动的重要途径。
由于当时航海技术落后,唐诗向日本传播的主要方式是书籍渡日。日本遣唐使入唐总会不惜重金求购唐人诗集。《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贲锡,尽市文集,泛海而归。”现今出土的日本正仓院文书和平城京木简中也见到《王勃集》《太宗文皇帝集》《庾信集》《许敬宗集》《骆宾王集》等唐诗集的名单,显然是由遣唐使带去的。731年,圣武天皇把六朝和隋唐书籍中与佛教相关的诗文抄录为《杂集》一卷,有王居士诗三十八首和隋炀帝诗三十二首等145首诗作,这些诗文也应该是遣唐使带去日本的。891年,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编录诗家部共十五部166卷,记录唐人诗集:
张昌龄集十卷 骆宾王集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新著王勃集十四卷 崔融集十卷 陈子昂集十卷 卢照邻集二十卷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上官仪集三十卷 杨炯集三十卷 许敬宗集二十卷 沈约集百卷王昌龄集一卷 宋之问集十卷 张文成集九卷 李峤集百二十卷 刘希夷私集一卷 贺兰遂集二卷 沈诠期集十卷 李白歌行集三卷 王维集二十卷 杜审言集十卷 白氏文集七十卷 元氏长庆集二十五卷 白氏长庆集二十九卷[9]等。从这份书目可知唐中期以前的许多诗集已传入日本,虽然这些并不是当时传入的唐诗集之全部,却能想象唐诗广为流传的盛况。
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当数白居易。《白氏文集》中提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指出日本和新罗遣唐使曾抄写《白氏文集》携往域外。《游仙窟》的作者张荐可与白居易相媲美。张荐善属文,据《旧唐书》载:“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新唐书》又记载:“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10]可见,他的诗文被新罗和日本重金求购,携回本国。
3.唐诗的“逆流”与“交流”
唐诗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少量诗文逆流回唐朝的情况。据日本《扶桑略记》记载,宽建是平安朝兴福寺的学僧,926年入唐巡礼。临行前他向醍醐天皇索要菅原道真、纪谷长雄、橘广相、都良香等诗人的诗集共九卷带往唐土流布。醍醐天皇不但接受了他的奏请,还附加小野道风书法两卷命他带往“唐家流布”[11]。最新发现的日本大阪府河内长野市金刚寺寺僧禅惠1315年所著古文书《龙论钞》中还转载了《淡海居士传》一文。据该文所记,奈良文人之首淡海三船曾委托遣唐使将所著《大乘起信论注》带给越州的祐觉、《北山赋》带给长安的丹丘。“唐灵越龙兴寺僧祐觉见《论》手不释卷有赞诗曰:真人传起论,俗士著词林。片言复析玉,一句重千金。翰墨舒霞云卷,文花得意深。幸因星使便,聊申眷仰心。……大理评事丘丹见赋,再三叹仰:曹子建之久事风云,失色不奇。日本亦有曹植耶。”[12]因此,日本也有优秀诗作逆流回唐,这种“逆流”繁荣了唐代诗坛,给东亚文学交流增添了活力。
而且,还有不少唐日诗文“交流”的现象,形成唐诗环流体系中的交融点。这种交融常表现为中日文人间的送别寄赠之作,即文人间“诗的对话”。例如,围绕盛唐时期的朝衡辞唐归国,唐人写了不少送别诗。李白、王维、储光羲纷纷赠诗朝衡,王维的诗序描述了朝衡与唐朝友人“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的亲密关系并褒扬他“名成太学,官至客卿”的显赫仕途。诗曰:“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搡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13]7朝衡吟《衔命使本国》诗回赠唐朝友人,诗曰:“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13]121表 达 了 思 念 故 土 与 不 舍 大 唐 的 复 杂心情。
中唐时期,唐日诗文唱酬更为频繁,最著名的是日僧空海与唐人马总的离合诗唱和。《性灵集序》曰:“和尚昔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夫泉州别驾马总,一时大才也,因送诗云:‘何乃万里来,可非衔其才。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14]这里所说的空海所作离合诗即《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诗:“蹬危人难行,石嶮兽无登。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15]空海、最澄回国时也得到不少唐人赠诗。钱起、孟光、毛焕、崔謩、全济时、林晕等文人,吴已、行满、许兰、幻梦等僧人作组诗《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相送。毛焕描述了最澄与唐人诗文往来的情况:“未传不住相,归集祖行诗。举笔论蕃意,焚香问汉仪。”崔謩赞扬最澄汉学、佛学修养高深:“问法言语异,传经文字同。何当至本处,定作玄门宗。”[13]32-46
晚唐时期,圆仁、圆载、圆珍等日僧也得皮日休、陆龟蒙等人赠诗。皮日休的《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讲殿谈余著赐衣,椰帆却返旧禅扉。贝多纸上经文动,如意瓶中佛爪飞”[13]83塑造了一位学识渊博的日本高僧形象。陆龟蒙的《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13]87,描述圆载收集汉典携归的情况。这些唐诗传播中的“交流”现象证明了日人能够使用经典的汉文吟咏诗歌与唐人唱酬。而唐诗的“顺流”“逆流”“交流”方式共同构成了唐诗在日本传播的环流体系。
三、唐诗传播的文化功能
1.亲善外交的手段
与语句僵硬的公文书相比,优雅的唐诗更能表达情感。中日文人邂逅或分别都吟咏唐诗,吐露“一面相逢如旧识,交情自与古人齐”的深情。尽管唐日唱和诗有不少毫无意义的外交辞令,艺术价值也普遍不高,但吟诗还是两国建立互信关系,开展亲善外交的有效手段。日本长屋王曾造袈裟一千领并托遣唐使带往中国,供养众僧。袈裟的衣缘上缝制了他的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13]119表面上这只是一件佛事活动,实质上通过诗文表达了和唐朝亲善友好的愿望。诗文赠答还能使从属地位的小国使者从政治身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宗主国的尊重。渤海使节释仁贞入日宫陪宴时曾作诗献给日皇:“入朝贡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反映了日本对渤海使的礼遇。唐玄宗赠给日本遣唐使的《送日本使》曰:“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表达了唐皇对日本使节的关怀。
东亚国家间除友好交往外也时有摩擦和冲突发生。诗文赠答可以跨越利害关系,缓和剑拔弩张的政治气氛。历史上的新罗与日本频有战事发生,白村江海战使两国邦交极度恶化。长屋王却在私宅“作宝楼”大开诗筵,款待新罗来使。席间日本文人赠诗新罗使:“新知未几日,送别何依依”“青海千里外,白云一相思”“未尽新知趣,还作飞乖愁”“赠别无言语,愁情几万端”,表达依依惜别之情。正如王勇师所言:“尽管新罗和日本在历史上作为对手政治关系异常紧张,但主客唱吟正与相互执行公事时的险恶气氛形成鲜明对比,洋溢着非常融洽的氛围”[16]。可见,唐诗作为交流感情和思想的手段,使言语不通的两者跨越政治上的差异和对立,在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上其功能不可小觑[17]。
2.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
唐诗还是衡量古代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外交场合下,“诗文遣词造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体面和个人的名誉”[18]。大唐兴盛之时,东亚汉文化圈内各国均以炫示各自的汉文实力为交往之要务。双方交往之文牍,均委以国手书写,行文典故堆砌、辞藻冗缛,还要特选国手抄写。至于双方的诗文唱酬,亦被视为力逞国格的擂台赛。渤海使的屡次访日被日廷视为番邦“海外慕化”的表现,《凌云集》所收《渤海入朝》诗云:“乃知玄德已深远,归化纯情是最昭”表现出日人的文化优越感。日廷为避免失态,曾委派菅原道真、岛田忠成等当代文豪接待渤海大使裴颋一行,菅原道真共赋诗十七首与之唱和。道真的诗格调高雅、遣词厚重,大量引用《文选》《尔雅》《诗经》《汉书》《史记》等汉典,通篇可见精心雕琢的痕迹[19]。例如“别来二六折寒胶,今夕温颜岂敢怕抛。持节犹新霜后性,忘筌仍旧水中交”“皎驹再食场中藿,仪凤重归阁上巢。借问高才非宰相,扬雄 几 解 俗 人 嘲。”[13]190-196等 句 用 典 频 繁、晦 涩 难懂。道真如此在遣词上煞费苦心,无疑是出于彰显国格的考虑。
由于外交使臣同时也代表着本国文化水平的高低,作为惯例,日廷均任命文化修养高的文人出访唐朝。选派的大使、副使、判官都精通汉学,随行人员中不乏硕学之士。716年任命的第八次遣唐使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马养皆出身名门,尤其是藤原马养极富文采,有文集两卷行世,称为“翰墨之宗”。他归国后更名藤原宇合,自负甚高。《怀风藻》中收录其诗六首,为收诗最多的诗人。又如,804年的遣唐使判官菅原清公出身文章世家,《凌云集》收其诗二首,其中《越州别敕使王国父还京》是献给送行的唐朝官员的诗,诗云:“我是东番客,怀恩入圣唐。欲归情未尽,别泪湿衣裳”[1]67,表现了菅原清公敢于展露诗才的自信。日廷选派藤原宇合、菅原清公这种当代文宗出访唐朝无疑也是为了显示本国文化水平。
10世纪前半期,东亚盟主唐朝灭亡,东亚世界的统一性丧失,古代王朝国家间规模盛大的文化交流从此中断,唐诗在日本的传播也渐渐陷入沉寂。但是,繁荣了400余年的唐诗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使其在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诗的越境流动促成了中日文人间 “诗的对话”,中日文人通过象征性的亲密诗意跨越语言的障碍,进行了高水平的意象交流。
[1]與謝野寛·正宗敦夫.日本古典全集[M].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大正十五年.
[2]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王煦华,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2.
[3]木宮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M].东京:冨山房,1955:204-206.
[4]日本国会国立図書館蔵.国史大系巻十二:令義解:卷3:学令[M].東京:経済雑誌社,明治三十一年.
[5]日本国会国立図書館蔵.国史大系:巻一:日本書紀[M].東京:経済雑誌社,明治三十年:270.
[6]清水茂,等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5:日本詩史:五山堂詩話[M].東京:岩波書店,1995:44.
[7]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5.
[8]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0.
[9]小長谷恵吉.日本国見在書目録解説稿[M].東京:小宮出版株式会社,1976:163.
[10]宋祁,欧阳修,等.新 唐 书 [M].北京:中华书 局,1975:161.
[11]日本国会国立図書館蔵.国史大系:巻六:日本逸史:扶桑略記[M].東京:経済雑誌社,明治三十年:681.
[12]後藤昭雄.平安朝漢文文献の研究[M].東京:吉川弘文館,平成五年:19-37.
[13]张步云.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14]空海.性霊集[M]∥空海.弘法大師全集:第6卷.東京:筑摩書房,1984:729.
[15]空海.拾遗雑集[M]∥空海.弘法大師全集: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84:129.
[16]王勇·久保木秀夫.奈良平安期の日中文化交流―ブックロードから―[M].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01:148.
[17]石母田正.詩と蕃客[M]∥日本古代国家論.東京:岩波書店,1973.
[18]村井章介.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M].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58.
[19]遠藤光正.渤海国使と菅原道真の唱酬詩[J].東京:東洋研究,1992(103):5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