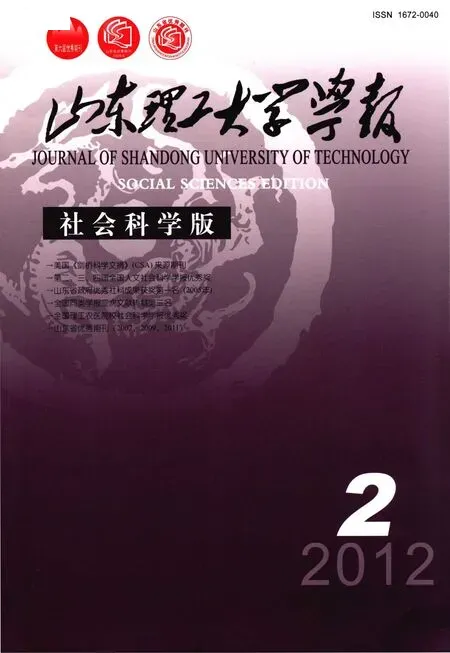从《光明天使》看欧茨的悲剧意识
2012-04-12王静
王静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一、引言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以多产而著称。其第十四部长篇小说《光明天使》(Angel of Light,1981)为纽约时报年度杰出图书;评论家托马斯·爱德华斯称赞此书为“强大而引人入胜的小说……是欧茨充分运用其想象力而创造出的另一部杰作”。[1]105-109美国《约翰·巴克汉评论》杂志为这部小说所刊发的书评中赞誉欧茨在《光明天使》中呈现出“一种钻进她笔下人物灵魂里去的能力,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有时甚至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能力”。[2]10该小说惊世骇俗的情节叙述、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强烈的悲剧色彩正在吸引越来越多评论家的关注。本文从该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入手,探析性格缺陷与人物悲剧结局的关联。但是透过性格悲剧的文本表象,展现在叙事背后的是欧茨的忧患意识。一方面颂扬了时代激昂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又内隐着她对美国当代社会弊端及问题的关注以及对青少年成长、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担忧。
《光明天使》中人物及故事情节都明显对应着古希腊经典悲剧——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是古希腊悲剧的现代翻版:美国联邦司法委员会主席莫里斯·哈勒克(对应古希腊英雄阿伽门农)在遭到弹劾后,写下一封忏悔信随后驾车意外死亡。当所有人都相信莫里斯是畏罪自杀时,莫里斯的一对儿女欧文和克尔斯顿(分别对应着俄瑞斯忒斯和伊拉克特拉)却坚信父亲的清白和无辜。他们相信是母亲伊莎贝拉和其情夫尼克(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将父亲逼向死亡的深渊,从而立志向母亲讨还正义,为父报仇。为弄清父亲被害的真相,克尔斯顿不惜向母亲其中一个情夫托尼献出自己少女的身体,而欧文则放弃学业,加入了名为“银翼”的恐怖组织。最终,欧文手刃母亲,而柯尔斯顿则在最后关头放弃杀死尼克,隐居他乡、远离华盛顿这个是非之地。
二、天使:追寻正义中凸显英雄气概
欧文,这位温文尔雅、前途远大的大学预科生与古希腊英雄俄瑞斯忒斯在人生境遇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欧茨在塑造欧文这一形象时并未满足于将古希腊英雄俄瑞斯忒斯照搬上现代舞台,而在欧文身上注入了新的内涵。埃斯库罗斯笔下的俄瑞斯忒斯只是个听从神谕为父报仇的王子,报仇后被复仇女神追逐,在众神的帮助下才被判无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是为了宣扬神的力量和人的服从,主人公只是一个命定复仇的符号。而欧茨塑造的欧文如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放弃了本来拥有的光明前途,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虽然期间也有犹豫和彷徨,但他从不曾有怯懦、退缩之意,始终坚持承担重负,与邪恶力量、与丑陋、不公的社会作斗争,直至以生命换来使命的完成,力图恢复被颠覆的秩序。在调查父亲的死因过程中,欧文接触了父亲生前的众多同事和朋友。他孤身一人的调查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然而正如古希腊英雄一样,欧文不曾因前景的阴郁而丧失信念停滞不前,仍然坚定地进行着自己的计划。在他的斗争中读者可以看到一种鼓舞人心的精神,这种“不是叫人逆来顺受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抓住不放斗争到底的精神”,正是美国当代批评家克莱格所言的“悲剧精神”。[3]19-33
与欧文同病相怜、因父亲的死而性情大变的还有十七岁的妹妹柯尔斯顿——现代版的厄勒克特拉。在古希腊悲剧中,厄勒克特拉这一角色定位在弑母弑君的支持者或者帮凶上,家族灾难的最后消除都是由俄瑞斯忒斯来完成的。而在欧茨笔下,对柯尔斯顿大笔墨的刻画使得这一形象散发出与哥哥欧文同样耀眼的光芒。尚处花季的柯尔斯顿本该如所有少女一样拥有平静的生活,享受父母的呵护与疼爱。但家庭的变故、母亲的不忠彻底颠覆了柯尔斯顿原来的美好生活,在面对成人世界的背叛与欺骗时她的内心受到沉重打击。如若是名弱女子,柯尔斯顿或许会选择妥协或者逃避,对母亲的背叛视而不见。这样,她就依然能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和光明的前途。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没有悲剧主人公会选择中庸之道;也没有任何主人公会因为想要苟且偷生而牺牲自己的目标或他所选择的‘铁血道路’”。[4]138凭借顽强的性格,柯尔斯顿选择了主动抗击,而非消极躲避;她选择追寻崇高的理想,而非懦弱的存活于世。她收集尼克和伊莎贝拉的资料寄给哥哥欧文,将其拉入复仇的阵营,从此走上艰辛的复仇之路,只是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恢复秩序、找寻正义。
从道德上分析,欧文和柯尔斯顿这两位尚处青春期的少年都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感情丰富,遭遇变故后感伤怀旧:对父亲的怀念显露出浓浓的子女情;他们坚定无畏:复仇之路即使再艰辛也阻止不了他们行动的步伐。他们是善良的,其复仇与私欲无关,复仇的动机也可以说是高尚的,而绝非出自本性的恶。兄妹俩的弱小、孤独与无所依傍辉映着内心的强大,更加凸显出其形象的伟岸与英雄式的气概。不仅如此,欧茨巧妙地将哈勒克家族设定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废奴运动领导人约翰·布朗(1800~1859)的后代,将文本延伸到历史层面,使得小说与19世纪50年代的废奴运动构成互文,从而更加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哈勒克家族的老祖宗布朗“用暴力和武器”积极投身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杀死若干名奴隶主。他因其英勇气概被当时人尊称为“奥萨瓦托米的硬汉子约翰”。超验主义作家亨利·梭罗更是盛赞他是一位“光明天使”。[5]14欧茨也正以此来命名该小说,其寓意不言而明:欧文和科尔斯顿这两位弱小平凡的普通人,因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愿意为此拼搏牺牲的无畏精神已一跃成为了“天使”,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彩。
三、魔鬼:暴力中渐行渐远的理想
然而,也正是这两位英雄般的“天使”做出了骇人听闻的弑母与刺杀事件。欧茨在叙述中并未过分表现弑母场面的凶残,仅仅叙述伊莎贝拉身中“三十七处刀伤,绝大部分只是划破皮,但有几处却极深,而且是在喉咙、肺部和胃部”。虽寥寥几句但效果依然令人震撼。而柯尔斯顿对尼克的刺杀,则更加令人骇然。尼克是莫里斯多年的伙伴,也是欧文的教父,相当于柯尔斯顿的“父亲”。此时科尔斯顿血腥的刺杀相当于弑父。兄妹俩分别的弑母、弑父之举向来被认为是伦理上的禁忌,残酷而令人畏惧。曾经一心向善、追求正义和秩序的“天使”俨然已化身魔鬼,进行着残酷的屠戮。
苏联文学批评家阿尼克斯特在分析悲剧根源时说:“邪恶还有另一根源,即不在物质财富的图谋,而在人们的精神需求。原来最高尚的动机有时也会导致骇人的后果。”[6]376-378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一心向善却偏偏走向善之对立面的欧文和柯尔斯顿兄妹俩:他们高举正义之旗,却思维狭隘,深信“正义与邪恶”、“好与坏”这些简单的二元对立,并誓死消灭世界的“邪恶”与“坏”,最终错误地选择了暴力这一极端的武器走上了复仇之路。然而,纵然是十恶不赦的人也依然顽固地保有与其他所有人一道拥有的东西——作为一个人在人身与人格上所拥有的尊严。这种尊严是人类共同存在的最后纽带,这一纽带一旦被摧毁,人性将会受到质疑,对任何理想与文明的追求都将显得毫无价值。因此,再崇高的目标也不能成为人身侵犯的理由。与他们的老祖先约翰·布朗一样,兄妹俩“将自我感觉的正确性作为评判标准,使凶残的暴行正义化”,[7]164目标的崇高性完全遮蔽了暴力行为本身具有的残忍性与犯罪特征。
如前文所述,“光明天使”第一层涵义意为如布朗般追求正义、照亮世间的勇士,在此之下还有另一层寓意。《失乐园》和《神曲》中都描述过一个掌管光明的天使长叫做路西法(Lucifer)。路西法用暴力反抗上帝权威,最终失败而堕落成魔鬼撒旦。因此,在西方经典文本中,光明天使也是撒旦的代名词。路西法这一堕落的光明天使暗示了柯尔斯顿和欧文虽然以伸张正义、恢复秩序为目标,但在复仇的过程中却已化身为暴力和死亡,与他们所追寻的正义愈离愈远。柯尔斯顿也早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知道“我的愤怒,我的悲哀,我的复仇计划,我对正义的渴望,最终会引出相反的结局”,最终两位“天使”一步步沦为令人颤抖惊骇的魔鬼却不自知,在屠杀中毁灭了理想。
因此,《光明天使》这部小说的悲剧性并不在于结尾处欧文与母亲的共赴黄泉,也不在于柯尔斯顿最终放弃报仇、复仇的未完成,而是兄妹俩长期以来牺牲一切所追求的正义恰恰毁于自己之手。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舍勒(Max Scheler)所言“悲剧的产生在于某些价值的毁灭”足以说明兄妹俩的悲哀。[8]3从选择暴力作为武器开始,欧文和柯尔斯顿便由天使化身路西法,他们寻求正义这一目标就永远不可能达到,理想注定会破灭。这种注定也即别林斯基所言的悲剧之“劫运”,笼罩着整部小说,给读者以浓重的悲怆感。
四、从天使到魔鬼:源于性格的堕落
正如哈姆雷特的死一方面撼动读者、使其涌起崇敬感佩之情,另一方面也引起人们对其延宕行为背后深层原因的关注,欧文和科尔斯顿的死亡与失败同样也具有以上两个效果:激发崇敬与究其原因。
美国批评家西尔华(Richard B.Sewall)曾说过:
在劝善喜剧和讽刺作品中的人物:“我思索,所以我存在”;在建功立业的人(史诗):“我行动,或者征服,所以我存在”;敏感的人(抒情诗):“我感受,所以我存在”;信仰宗教的人:“我信仰,所以我存在”;悲剧人物和他们不同……他的人性的本质却通过受难才表现出来:“我受难,我情愿受难,我在受难中学习,所以我存在”。[9]35
欧文和柯尔斯顿甘心放弃美好的生活而甘心受难的这种悲剧精神在他们身上熠熠生辉,也照耀了他们最终的失败。他们为追求正义和秩序奋斗,最终的死亡和失踪表现了英雄式的伟岸和人的尊严,促使人们超出日常生活的经验,激发人们去寻找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他们的毁灭中,“我们看到一种比苦难还要坚强得多的灵魂,看到一种没有东西可以摧毁的勇气,从而振作起了我们自己的精神”。[10]222与整个黑暗混乱的社会相比欧文和柯尔斯顿他们显得十分渺小,却仍然高傲地忍受着痛苦,在生与死的抗争、人的自由意志与强大黑暗社会的抗争中显露出人的尊严和价值。因此“英雄人物虽然在一种意义上和外在方面看来失败了,却在另一种意义上高于他周围的世界,从某种方式看来……与其说被夺去了生命,不如说从死亡中得到了解脱”。[11]132欧茨也赞扬了这种自由选择的死亡,通过欧文之眼描绘了一位为争取自由而被俘最终在狱中自杀的女子。照片上她那坚强又漂亮、毫无笑容的脸不仅赢得了欧文的敬佩,也让读者感到深深的震撼。此时她的自杀不再是罪愆,而是“一个必须的行动”,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兄妹俩并未因为失败而低下,反而从其失败中超出了常人与其周围的世界,从死亡中获得了解脱。
然而读者在感佩兄妹二人无畏勇气的同时,也会发现在欧文和柯尔斯顿这两个“光明天使”光辉形象的背后也攒动着令人不安的阴影,那就是他们各自性格上的缺陷。欧茨在对二者形象的塑造上,并不满足于刻画出如古希腊悲剧里至德至善的诸神形象,她将关注点放在寻常人身上,展开对人性的探索。因此,她在塑造自己的悲剧人物时,最主要的考虑不是他身上具有多少正面的素质,而是如何尽可能从各个侧面来揭示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现实性。在其笔下,柯尔斯顿暴露出偏执、固执己见的弱点,而欧文则显露出缺乏主见易被诱导。
柯尔斯顿虽然是妹妹,但在和欧文的关系中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她坚信父亲的无辜并鼓动欧文加入她的复仇。然而在行动中,她的坚持愈发显露出她性格上的偏执,这深切反映在其对母亲的态度上。与《俄瑞斯忒斯》里的厄勒克特拉一样,柯尔斯顿与母亲之间一直是一种“病态的”母女关系:女儿称母亲为“淫妇、母狗、杀人犯”,而伊莎贝拉称女儿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母女间除了深深的仇恨之外已无其他感情,对母亲强烈的敌意甚至引起柯尔斯顿的神经性食欲减退。如欧茨的评论家达利所言:“厌食是对母亲仇恨的一种表现症状。”[12]182然而,柯尔斯顿对母亲的痛恨是建立在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之上。在莫里斯死后,柯尔斯顿由始至终都坚定地认为是母亲和尼克谋杀了父亲,父亲的死并非自杀,而父亲留下的遗书也是伪造的。面对欧文的质疑,柯尔斯顿只能一再地重复“你是问,谁是凶手?——我们当然知道”。这种肯定却毫无证据。事实上,莫里斯的确是自杀,被谋杀仅仅是柯尔斯顿的想象而已,只不过伊莎贝拉和尼克的背叛间接地导致了莫里斯的自杀。她还为自己的猜测找到了理论根据,从诗人威廉姆·布莱克的诗句中寻求安慰。
我们全都喜欢布莱克的作品,欧文说,他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可耻的古怪的无可原囿的事情……
如今完全证实的,昔日仅仅是一种猜测。
啊,我喜欢这一句,柯尔斯顿说。我喜欢。
如今完全证实的——
—昔日仅仅是一种猜测。
对。欧文说,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这话。要等以后。等事情了结了。等他们俩都死了。
如今完全证实的,昔日仅仅是一种猜测……
她的声音,因感奋而颤抖着。
实际上,柯尔斯顿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目前所有对母亲的指控只是猜测,但却执拗地深信她的罪过。布莱克的诗句恰恰给与她慰籍,使她相信:暴力最终会证实现在的猜测。由此可见,欧文和柯尔斯顿的整个复仇都是基于猜测,没有肯定的证据。这也使其与正义这一目标大相径庭、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仍是柯尔斯顿性格的偏执与执拗所致。
相比较妹妹的偏执,欧文的性格稍显懦弱,缺乏看待事物的主见:最初被妹妹煽动开始为父报仇,随后又被梅诱导加入了名为“银翼”的恐怖组织。这一恐怖组织是美国众多学生恐怖组织中的一个,却声称自己并非“恐怖分子”,而实属“为维护人之天赋权利”的“烈士”。而他们接纳欧文这类富家子弟的进入,多少是出于筹募“革命经费”的需要。欧文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接受了梅的洗脑,甘心与其结成“统一战线”。这里有一例证实欧文的性格缺陷:在变卖欧文从家中豪宅里偷来的奢侈品时,一位成员感叹一象牙雕塑的美,却招致所有人的愤怒,因为“美是这世界所支付不起的一种奢侈”,是一种“布尔乔亚的堕落、腐败、腐朽、腐臭”。美遭到“银翼”成员们的排斥和鄙视,而欧文也自觉地接受这种思想,以美为丑。然而,在柏拉图的秩序理论中,宇宙是神以善为最高原则,排除混乱无序而创造的。神发现可见世界处于混乱无序的运动中,而“有序无论如何要比无序好”,于是将世界由无序变为有序。既然有序的世界由善的创造者观照永恒者创造而来,应当是美的,而且是“一切被造事物中最美的”。[13]8“银翼”成员们对美的鄙夷可以推及到对秩序的不屑,而恢复正义、重建秩序恰恰是欧文所追寻的。性格上的轻信与缺乏主见使得欧文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越走越偏,最终走向了正义的对立面——暴力与屠杀。
《光明天使》借用了古希腊故事原型,但在人物塑造上却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众神大相径庭。《俄瑞斯忒亚》中的主人公在品性上皆完美无瑕,高高在上,他们的悲剧在于命运的无常。而欧茨笔下的欧文和柯尔斯顿皆为凡夫俗子,绝非完美之人。他们冲动、莽撞、短于思考、易于轻信等性格上的缺陷而必然要为各自的失败乃至死亡负责,他们的悲剧也因此与哈姆雷特、奥赛罗等一样属于典型的性格悲剧。
五、欧茨的悲剧意识与忧患意识
渴望成为天使的两兄妹,却因性格缺陷注定只能成为堕落的魔鬼。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之言:人生而自由,但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因此,人注定遭遇着一个悲剧性的生存困境,在欧文兄妹俩身上,这一困境就展现为崇高理想为自身性格缺陷这一枷锁所束缚。然而,性格并非无根之水、天然所成,其形成受到社会与时代精神的强烈影响。《光明天使》的创作始于美国政治与社会大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虽然欧茨并不是政治小说家,但她的思想深深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欧茨于1960年赴底特律大学任教,在那度过了整整六年。这座“汽车之城”的繁华与混乱以及于60年代中期爆发的民众暴动是“整个美国社会邪恶的缩影”,[7]87它所暴露出的诸多弊端引起了欧茨的关注。可以说,《光明天使》正是欧茨通过这部性格悲剧表达其对所处时代的关注与忧虑。
欧文与柯尔斯顿属于典型的富裕中产阶级的孩子,出生成长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60年代。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并不是严格按照年代划分的,而是一个从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的时期。这一时期可谓美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示威、新左派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纷至沓来,强烈地冲击着传统价值观念。成长于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一方面个性增强、具有更强烈的反叛精神;而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弊端的侵袭,造成个性的不完善。
青年政治运动以及新左派思潮,呼吁以人为关注的中心,抗议现代工业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和把人降为物的人格解体现象。如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教授迪克斯坦所言,60年代“既推动了革命又推动了改革,并试图把追求社会正义和寻找个人真谛相结合。民权运动与‘人的潜力运动’有一个共同观点,即:人们有权在此时此地享受幸福”。[14]Ⅶ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追求解放和自由成了人们的奋斗目标,“不再一切照旧”成为60年代主导文化批评者们的口头禅。浸浴在这股思潮里长大的一代“是富裕的教育的产物。他们的前辈——50年代的青年一代——为了取胜而拼力比赛,可是他们却在向比赛的规则挑战,或干脆拒绝比赛”。[14]70也正是在这宽松自由、突破传统束缚的环境中,欧文和科尔斯顿才能产生如此无畏、强大的抗争力,才能在重重压迫之下坚持理想并为之奋斗乃至牺牲。欧文和科尔斯顿并非孤身作战,在他们身后,千万个同样充满激情和身负理想的青年在时代的激流中急流勇进。60年代赋予了青少年以无限的激情与冲劲,但同时它的浮躁与混乱也造就了他们莽撞、短于思考的性格缺陷。
家庭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影响甚大,美国批评家马林(Irving Malin)曾说:家庭向来被视为稳定的社会单元……,如果家庭不能提供安全的话,那么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安全。[15]50欧文和科尔斯顿性格的偏激与短于思考与其家庭的分崩离析关系密切。60年代的嬉皮士们倡导性自由、吸毒和群居,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开始盛行,加之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风潮抬头和女权运动的兴起,这些都对美国人强调责任、利他和自我约束的传统价值观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对美国人的家庭与婚姻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作为母亲的伊莎贝拉深受这股自由之风的影响,在生活中追求自由,整日周旋于情人之间寻求爱情,子女于她而言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在丈夫死后,面对女儿极度痛苦导致的行为失常,伊莎贝拉非但不对其进行安慰,反而讥笑科尔斯顿为得了“狂躁症”的“青春期精神病患者”;与欧文通电话时,也全然不顾儿子心里的痛苦,大谈特谈其度假的欢愉;而身居要职的父亲更是对子女的成长无暇顾及。虽然哈勒克家庭表面风光无限,但一对子女却难以享受正常的父母关爱,传统的核心家庭的观念彻底被颠覆。哈勒克一家并非特例,而代表了众多同样面临危机的美国家庭。无怪乎有评论家感慨:“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正在死亡……美国家庭机制正在分崩离析。”[16]4-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缺乏家庭关爱的美国青少年在成长的道路上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性格的不健全发展。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内部环境对他们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社会政治这一外在大环境同样也极大地影响了青少年的成长。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Kroeber)指出:“人类心智广大的可塑性,几乎全部为他周围的一切所决定,其中最大的影响力也许来自个人所生存的社会。”[17]6560年代是充满欺骗与背叛的时代——这种背叛最深刻地体现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上,反映的是政府领导人对公众的欺骗和背叛。在小说中,欧茨对美国政治的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控诉。她通过小说中一小人物之口称当下的美国政府充满了腐败和欺骗,“腐败至极、罪行累累”,是个“杀人的政府”。在这么一个政府里,在这么一个极端腐败的背景之下,“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他们全都犯有罪恶。将他们粘合成一团的,也就是罪恶”,因此,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是“地狱在人间的翻版”。政客们大肆收受贿赂,互相勾结的同时也引导整个民族走向腐败与堕落。正如欧茨所言,“如果领导人的道德和私生活败坏,那么整个国家也必将衰败:他们是具有示范和代表性的人物”。[7]161充满欺骗、背叛的政治环境激发了新左派文化运动,以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代表赫伯特·马尔库塞为首的新左派信奉激进主义,相信“暴力是净化行为”,“暴力就是自由”,[18]200由此孕育出暴力横生的社会。时任底特律大学讲师的欧茨意识到时代的弊端,曾预言道,底特律这座“汽车之城”将会因变成“美国的谋杀之城”而闻名。[7]98在这样激进的环境中成长的美国青年一代,必然会丧失思考、倾向暴力,欧文和科尔斯顿两兄妹的悲剧也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
家庭与外部的政治环境对青少年性格塑成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而教育同样也是塑造青少年个性的重要途径。莎翁笔下为父报仇,力图重整乾坤的悲剧王子哈姆雷特之所以会失败,众多评论家将其归结于哈姆雷特性格的犹豫及行动的延宕。作为王子,为父报仇是哈姆雷特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同时作为一个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思考的不是单纯的杀死克劳迪斯,而是要消灭一切罪恶,按照人文主义的理想来改造现实。哈姆雷特的思想是深刻而强有力的,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这种思考也使得整个人物形象具有了人文主义思想家的特色。他在“重整乾坤”这一重任面前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始终在探索中延宕、在延宕中探索,想要行动却不知如何行动。这正是哈姆雷特行动延宕的主要原因。诚如黑格尔所说的,他所犹豫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哈姆雷特长于思考,勇于探索,却又短于行动,最终酿就了悲剧。然而,他的悲剧也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慎重与所受教育的深厚。
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里,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本应进化得愈加注重思考、拥有更加深邃的思想。然而,相比较人文主义思想者的审慎与思考,欧文两兄妹却走上了另一极端。科尔斯顿的偏执与固执己见与欧文的缺乏主见、易被诱导相结合,便构成了轻率与鲁莽、冲动与不计后果,这无疑反映了当代教育的失败。如前文所述,60年代盛行着极度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整个社会充斥着浮躁之气。这反映在学校教育上,就是重科技轻人文、重应用轻基础。学校只重视传授知识而忽略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个性的完善,而老师则把主要精力置于发表论文、提高知名度上。欧茨在底特律大学任教时,学校为了提高竞争力,采取了一系列“激进而故意”的措施,积极鼓励老师们发表论文出版图书。[7]99教育的浮躁可见一斑。在小说中,欧文在学校受到老师同学的欢迎,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性格的可亲、思想的深邃,而只是因为他“论文已经写出”,“考试已通过”以及他“出色的答辩”。成绩、论文成了衡量学生价值的主要标准,而思考则因校园中这股浮躁之气被所有人忽略。同时,学校作为权力话语机构,需要的是学生的驯服与听从。而智商极高、充满想象力的科尔斯顿却“不肯听从任何训导,藐视权威”。在学校专制的环境下,个性受到压抑,更容易走向极端。小说中描写的自杀俱乐部正是充满叛逆精神的青少年在压抑环境下对抗压力、表达自我的极端方式。教育为国之根本,其终极目标本该是“育人”,却走上了浮躁专制之路,不仅使教育肤浅化,也压抑了青少年蓬勃的个性,使之走向极端与偏执。
60年代的美国社会海纳百川,容纳了诸多主义和学派,允许青少年最自由广泛地吸收;但其腐败堕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濒临崩溃的家庭结构以及浮躁的教育氛围却又无法为青年一代的性格完善提供好的环境与指导。欧文和科尔斯顿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却又反映出时代诸多弊端,欧茨也正是利用这部悲剧反映了其对美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担忧。
[1]Thomas R Edwards,“The House of Atreus Now”,In Bloom,Harold(ed).Modern Critical Views:Joyce Carol Oates,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
[2]谢德辉.光明天使译序[A].光明天使[C].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3]Murray Krieger,“Tragedy and Tragic Vision”,In Corrigan,Robert W(ed).Tragedy:Vision and For,California: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65.
[4]Henry Alonzo Myers,Tragedy:A View of Lif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6.
[5]Joyce Carol Oates,Angel of Light,New York:Dutton,1981.
[6][前苏联]阿尼克斯特.莎士比亚的创作[M].徐克勤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7]Greg Johnson,Understanding Joyce Carol Oate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87.
[8]Max Scheler,“On the Tragic”,In Corrigan,Robert W(ed).Tragedy:Vision and Form,California: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65.
[9]Richard Sewall,“The Vision of Tragedy”,In Corrigan,Robert(ed).Tragedy:Vision and Form,California: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65.
[10][英]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M].蒋孔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Brenda Daly,Lavish Self-Divisions:The Novels of Joyce Carol Oate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6.
[13][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4][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M].方晓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15]Irving Malin,New American Gothic,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2.
[16]Patricia Ann,The Decadent Family:Social Criticism in the Novels of Joyce Carol Oates,Lubbock:Texas Tech University,1975.
[17]Alfred Kroeber,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Hopkinton:Vintage Books,1963.
[18][美]戴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M].周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