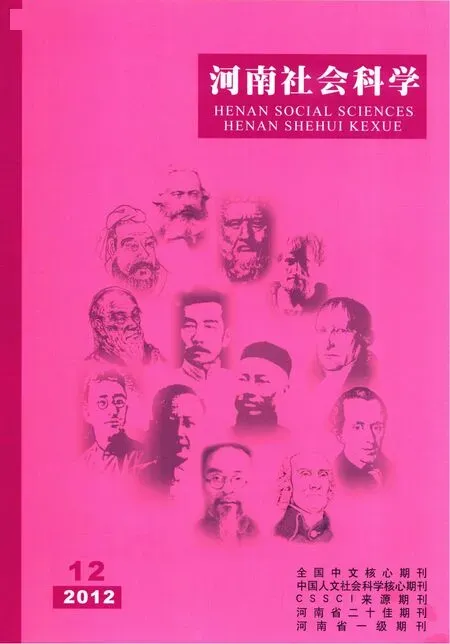从形上之辨到理气分殊——《朱子文集·答黄道夫书》与宋明理学的思想逻辑
2012-04-12谢昌飞
谢昌飞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道、形、器关系构成先秦哲学之基本逻辑,盖道与器统一于形,以形构成道与器之分殊与融会,如以形入手揭示古典哲学之逻辑可打开先秦哲学思想逻辑之开阔地(参见《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专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潜在的思想逻辑——并非去逻辑化或白描式的界说,而更蕴涵思想之缜密和语言之条理,二者的统一表达即中国传统文化之隐性形式。以此观点统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宋明理学的“理气之辨”作为此思想之表达,具有浓重的辩证意蕴,其中尤以朱子“答黄道夫书”之“理气之说”更为典型。以此为文本依据,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相互比证中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之真精神。
一、理与气之抽象
《朱子文集·答黄道夫书》对“理气”之关系如是表达: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
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此段文不过寥寥五十余字,却可分三个层次:其一,理气分殊,即强调理气共存于天地之间;其二,理气融会,即理气与生物之本具关系;其三,理气合一,即呈现为人物之性与形之一致。可逐一分析:
第一层次,即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与气盖共存于天地之间之“存在”。如辅之西方哲学的话语方式,则可类比于亚里士多德之“实体”。此实体之“实”并非单单指称“第一实体”之“实在”,也含有第二实体“理念”之意味,故两重实体既包含某种“在”性,又共存于天地之间。朱子所说之理气概也如此,故这里不强调“理气无先后”(“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或“理在气先”(“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之理气的时间关联,而仅仅强调理气之不同和理气之共存。
第二层次,即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此层次进一步说明理与气之不同与共存关系。从逻辑上看,理与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或气与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之间似乎可以用同一律来表达。但事实上A=A这一同一律的逻辑表达,是强调每个事物独立存在的资格,即仅仅依靠自身,而毋需寄生在他物之上,故当理被形而上之道或生物之本所指代或指称之时,实际上对“理”本身的某种否定的过程就已完成了,这一“非同一”的“同一”之实现又囊括何种内涵呢?以理之界定为例,理与形而上之道在这里以“者……也”之句式相连,它想要说明的是理与形而上之道的一致性。在探讨先秦哲学的思想逻辑之时,我们对道、形、器关系做了具体之探讨,认为道与器分别作为共相与殊相而统一于“形”(相)之中[1]。以此观点观之,道本身必凌驾于形之上,才能谓之“大道无形”。但理却也是生物之本,这一“本”之说法虽具有柏拉图之“理念”先在的意味,但毕竟体现于生物之中,即具有形之表达。同理气与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之间也体现为包含“形”在内的特殊性。故可以发现在朱子论及理气、道器、本具之关系时,一则强调理气对应于道器,但却将“形”本身之内涵囊括其中,即从先秦哲学的道、形、器之三者关系变为理与气二者关联,“形”融会于“理”与“气”之中,将形之于道与器之外在关联性转化为内在化,却又具有实在化之特点。二则强调理气对应于体与具,又具体体现在生物之上,是“体用一源”思想的合理表达,故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形而上之本体,而始终强调“存在者”之中的“存在”,海德格尔将“存在可以被遮蔽得如此之深远,乃至存在被遗忘了,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也无人问津”看做是西方哲学之根本病症,但存在者特别是“此在”之存在才是有意义之存在,这一点也不应被忽视。
第三层次,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类比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论述:
若当A是真实时,B亦必真实,
则当A是可能的,B亦必是可能的;
因为B虽必要成为可能,这里却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来阻止它成为可能。
同理,以“人物之生”为A,以“理”为B,以“性”为C,可得:
假使A为可能,则A为真实,必不包含不可能之因素在其中;
则C也为可能且真实的,
同理B也必然为可能且真实的;
假使B是不可能的,C亦即如此,自然A也不可能;
但A已经现拟定为可能的,所以C必然是可能的,则B也具有可能的必然性;
故A是可能的,B必然是可能的;
若谓A若可能时,B也可能同样可以表述为:A若在某个时候与某个方式上为真实,B亦在某个时候某个方式上为真实。
这样一来,理与人物之生通过“性”之内在关联既具有同等的可能性,也具有同等的真实性,也就是从逻辑上说,有人物之生就必然有“理”。同理可证得有“人物之生”则必有“气”,“理”与“气”共同完成“人物之生”的种种可能性和真实性。
不仅如此,如果前两个层次理与器之间仅仅强调两者逻辑上的关联,在这一层次当中,朱子以时间上的关联辅之佐证进一步说明两者的统一。“人物之生”由理成性,由气成形。如果从时间上看,理与气先于性与形,先有天理,才有人之性。故朱子既将“理”视之为“仁义理智信”五常之全体,两者之间乃是理一分殊的关系,故人之性来自理之逻辑上和时间上的优先性,即是普遍性的特殊化;同理,气也如此,普遍的气,构成人物之形,最终具“人物之生”。如此一来,先秦哲学的“道、形、气”三者的一体性关系产生了分化,如果说先秦时期三者关系以“道”为始,以“形”为摄,以“器”为末,形构成道与器相互联系与相互区别之关键,三者的一体关系体现为形之统摄与分离,那么,在朱子这里浑然一体的“道”、“形”、“器”既具有逻辑上的真实与可能性的理论,又具有时间上的形成关系,特别是性与形成为理与气生成人与物之中介或桥梁。于是核心问题从形而上之“道”转换为“形而下”之“人物之生”。
二、理与气之分殊
理气二分在逻辑上异于“道与器”的分别,在内容上更体现出与后者的不同。再以亚里士多德“实体”之逻辑看待理与气之内涵,可以发现“理”与“气”同样为本体或实体,这就异于道与器之共相与殊相之区分。亚里士多德对实体从四个层面界定:
其一是单纯的物体和它们的各个部分;
其二是内在的事物,即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原因;
其三是事物中作为范限与标记而后事物才成为独立个体的部分;
其四是事物的“怎是”,即公式和定义。
这四个层面可以简单概括为底层、普遍、科属和怎是,其共同构成了实体“是其所是”的所有内涵。以此观点反观“理”与“气”:其一,理与气都作为单纯的物体的各个部分,如朱子所说,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之所以在此层面上都作为“实体”或“本体”恰恰因为此二者都符合不为别的主题做云谓,而别的事物却以它们为云谓,即可以通过理与气区分不同人与物。其二,理与气都是内在的事物,即使事物成为事物的原因。如朱子在谈“理”之时,常将理与“四德”、“五常”联系理解,“理即仁”,以“仁”统摄其他“主德”,故理确定事物之“性”,而性使该事物成为“实是”。同样气也如此。朱子强调“元亨利贞”之生气,故气又称“一元之气”,气成万物之反复流动,故气决定万物之“形”,使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其三,理与气同样是事物中所存在的部分,作为范限与标记区别个体。正如上文所说,理通过“性”制约“人物之生”,而“性”即范限与标记,朱子曰: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卷五《答黄子耕》)。故性不同则事物不同。气亦如此。人物所禀,形气不同使之呈现出不同的表象。其四,理与气都可参与事物之定义。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虽强调“一统”而没有鲜明的种属的区别,但大抵的区别却是存在的。如人与物之区分,人之不同等级与物之不同等级等。故理与气所表达的事物之“是其所是”的特征必然能够揭示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
此谓之理与气作为“人物”之实体或本体乃是一致的。然则理与气又是分殊的,故朱子曰: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如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这一个”与“普遍”都作为“是其所是”之实体的基础上,还要区分出何谓“第一实体”。故亚里士多德强调本体(实体)为定义之始、认识序次之始、时间之始。本体必先于时间、先于定义、先于对事物的充分认识。以此观之,朱子的理是天地之始,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相对于气,理在时间为先,后有理与气化生万物,时间之始的本体为理。而认识之始的本体为气,如恩培多克勒指出:
他们的体质怎样的改变,
思想也常发生怎样的改变。
也如巴门尼德所说:
许多关节巧妙地组成人体。
也这样组成人的思心;
各人的思想皆由多关节的肢体发生。
而思想竟是那么繁富。
朱子也有类似的说法:
理难见,气易见。
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
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
也就是说从认识来看,由气见理,春夏秋冬是元亨利贞之呈现,元亨利贞是气之表达;相对于理来说,气为认识之始,以气见理。天地之间之理是看不见的,但天地之生气能认识到理,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之统一体现为以人合天的状态。理为时间始,气为认识始,何为定义之始呢?凡对一事一人一物之定义必包含“性”——一事物成为该事物之内在根据和“形”——一事物成为该事物之外在表现,两者结合使事物本身获得其本质性的界定。
故理与气同样作为实体或本体,如果说前秦时期的“道、形、器”之间的逻辑呈现为立体的殊相上升为共相的汇聚与共相下降为殊相的分离,那么在朱子的“理与气”中更多强调理气对于“人物之生”所具有的实体或本体意味,故朱子强调理气无先后,只在生成形与性双重作用之时,推动了人与物之产生;如果说先秦时期的“道、形、器”以殊相和共相体现类似于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的区分,那么朱子的“理与气”更多的是在宇宙世界中,在人与物、性与形的统一中把握理与气之交融;如果说先秦时期的“道、形、器”之逻辑强调事物的上升过程,强调对形而上之道之追寻,那么朱子的“理与气”统一于“人物之生”之现实世界,是在关注“理”之超越性的同时力图实现超越与现实的统一。
三、理与气之精神
由此可见,从先秦的“道、形、器”到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的“理气分殊”,表达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流变的真精神。如果说从先秦哲学开始中国哲学的逻辑就不仅仅如西方一般呈现为简单的直言命题或选言命题的模式,而呈现为三者逻辑的表达,这一逻辑通过“道”与“器”在“形”上之结合具体呈现,那么,统摄力量还在于“道”,形而上之道使器等具体事物成为可能。这类似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的论述:
第一组:如若是孤立的“一”,“一”不是一切;
第二组:如若是和“存在”相结合的“一”,“一”是一切;
第三组:如若是和“存在”相结合的“一”,“其他的”是一切;
第四组:如若是孤立的“一”,“其他的”不是一切。
也就是说,只有与存在本身(道)相结合,“一”才可能是一切。道是万事万物存在之根本,道是存在,是一元,是根据,中国传统哲学“道生万物”之主张与柏拉图之理念论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朱子之理与气则不同,其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即不仅仅强调“道”或“理念”之先在,更强调具体之“这一物”之特殊,故朱子曰:
盖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
但人物所禀,形气不同,
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耳。
尽管天地之物的理没有差别,但因着形与气之不同,它们仍然体现为不同的“性”和“心”,“性”亦并非完全由“理”所决定,它仍然受气与形之影响。故理与气之分殊又在具体的“人物之生”(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既不表述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主体之中”的“这一个”)中合二为一。这样,“道、形、器”之分殊与贯通演变为“理、气与人物之生”三者的关联,这一方面体现为宋明理学的现实主义态度,或者可以看做是类似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之典型表达,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以另外的方式延续了先秦哲学的“大一统”。先秦时期“道、形、器”之“一统”更多地通过道之统摄力量来实现,而道之不可思考与不可言说,使“道”在体现“圆满”的同时也难以表达。朱子的“理与气”则不同,其中包含着浓郁的宇宙论成分:理之四德、五常与气之运行变幻一一契合、相得益彰,自然之生灭变幻与人之德性的呈现相互印证。这一“大一统”就立足于更为宏大的视野,并实现了现实与理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更高的一致。
“理与气”之统一将先秦哲学的关系性思维更加推到实处。引证亚里士多德逻辑来说明“理与气”之逻辑固然能够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与西方哲学逻辑有相似之处,但也容易简单地将其湮没于西方的窠臼之中,这一点也可通过两者在逻辑上的不同予以说明。亚氏的逻辑之第一格、第二格和第三格可以如是表达:
如果A表述每个B并且B表述每个C,那么A也必然表述每个C;
如果D不属于任何E而表述每个F,那么E必然不属于任何F;
如果G和H都属于每个I,那么G必然属于某个I。
与“理与气”之逻辑相互比照,可以发现:其一,在理、气、与人物之生的关系中,朱子不但强调理与气分别通过“性”与“形”表达与人物之生的表述关系,更强调两者之共生和相互作用,故A在必然表述C的同时,可能也表述D;其二,如性为D,气为E,理为F,则朱子的“性”属于理之表达,不从属于气,可大约等同于亚氏逻辑之第二格,但结论是“理与气”即“E与F”之间并非决然的毫无关联,而总是存在某种相互缠绕之关系,即朱子所说的,形气不同则性不同的关联;其三,在以“理与气”表达“人物之生”的关系的同时,朱子不但强调两者对人物之生的分别作用,更强调两者之交互作用。即可以表达为:
如果G和H都属于每个I,那么G必然属于某个I;
那么每个H必然属于某个I
那么H和G必然在I当中发生某种关联。
相较之于西方逻辑,以朱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关系,这一关系并非西方意义上的“非此即彼”,更强调关系、精神、取向,不是排除异己,而是将异己融汇于更高的统一之中。这就类似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如黑格尔所说:“正像整个亚里士多德哲学一样,他的逻辑学……也需要一种改造,以便把他所有的规定纳入一个有必然性的系统的整体;——不是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分类正确、没有一部分被遗忘,并且依正确秩序表达出来的一个系统的整体,而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在其中每个部分被视为部分,而只有整体作为整体才具有真理。”[1]正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逻辑本身之辩证性和统一性,才使其既包含着价值概念的形象表达,又包含统一性的、关系性的思维——既包含宇宙论上的整体与交融,更包含道德上的精神和气象,呈现出中国哲学之博大宏广的精髓。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