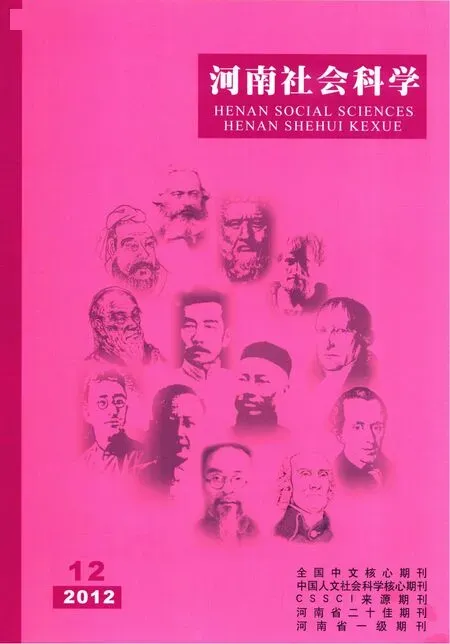道、理、器的形上形下之辨——谈程颢哲学
2012-04-12步蓬勃
步蓬勃,枫 叶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程颢哲学主要围绕道、理、器三个核心概念展开,承继中国传统哲学对“道、形、器”的话题探讨,铺展开以“道、理、气”为转换模式的新式方法,兼以各家学说独特气质,程氏哲学显现出生生不息的大道之行。理与形名虽不同,但实相符,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明道先生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本文围绕道、理、器三者的逻辑关系及逻辑理路并结合史宁中先生“自家体贴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方法谈程颢哲学,试图对程颢哲学有一个清楚明白的把握。
一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最有别于西方本体论之处就在于从生成关系上去探讨。道、理、器作为程颢哲学的核心概念,首先由生之大德的道引出何以生之本体。
天地之大德曰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以下简称《遗书》)
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遗书》卷二上)
程颢用“生”把握道,“生”是最高善之本体。以一个“生”字描绘出一个富有春意活泼盎然的世界,问题的关键也突显出来。什么在生,是道还是器,是理还是气?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每位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
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易传序》)
道、理、器核心概念的提出,具有生成与逻辑的双重维度。在生成维度上,作为最高本体的“道”在生成“物”的同时又给具体物作了一个之所以为区别于他物的理的依据性预设,或者说物直接对本体的呈现是本体散之在物的理。三者的关系用西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加以表述与比对,其关系会很清晰。亚氏三段论一般的表述形式如下:
如果A表述所有的B
并且B表述所有的C,
那么A必定表述所有的C。
道、理、器作为具体的哲学概念,我们可以这样加以转换:
A代表道;B代表理;C代表器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表述道、理、器三大核心概念的生成关系:
如果道生成所有的理(散之在理)
并且理是生成所有器的依据(则有万殊),
那么道必定生成所有的器(统之在道)。
道生阴阳而成器,道即器便是理,有道有理有器,则万物备矣。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间无适而非道也。(《二程粹言》)
道生万物,但道又是不可见无法触及不可捉摸的无声无臭、非有非无的神秘世界:
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如此,则亦无始,亦无终,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处有,亦无无处无。(《遗书》卷十二)
程颢与其他道学家的区别就在于用“无”形容道体,文中亦可以看出其老庄之学的痕迹。道无始无终、自有永有,不因为有,也不因为无,是自因,而非他因,也无法语言表达,“道可道,非常道”,正因无法言说“玄之又玄”,才能成为“众妙之门”。
程颢用“无”形容道体,与其他理学家承认“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形上本体与形下之器的理解上也有所不同: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遗书》卷十一)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形而下的器,道是形而上,器是形而下因道而立。道无形,不能脱离器而谈道,所以“器亦道,道亦器”,道器不能分离,“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矣”(《二程粹言》)。“有形皆器也,无形惟道”(《二程粹言》)。道与器的关系已经说得很分明,一阴一阳的运动、变化、发展即是道之本体的大化流行,离开形而下的阴阳之气便无法体现道。对道之本体只有透过外在有形质的阴阳变化在意识中加以体认,道,实实在在却无法言说,只能“默而识之”。只要言说,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体,可道之道非常道,非常道之道便是史宁中先生所说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形”[1]。虽非常道却是道的分有,因为道体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要说,便在时空中,所言离不开具体的器,或者说我们的思维只能对器背后的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所以然”加以抽象把握。这个“所以然”的抽象便是程颢自家体贴出来的“理”。冯友兰先生说:“明道所谓之天理或理,则即具体的事物之自然趋势,非离事物而有者。以后道学中之心学一派,皆不以为理乃离物而有者。故……谓明道乃以后心学之先驱,而伊川乃以后理学之先驱也。”[2]可见明道先生思想之最根本处不在理,而在道。
道之本体生生不息,永恒不已,生化之妙。人,不但要体贴更要常存此理,不断向上超拔与道合一,以此道此理教化他人,这就是明道先生立学的真正所在。
二
明道先生道、理、器核心概念,完全是按照有道→有理→有器这样的逻辑理路提出的。道、理、器三者在生成维度层面的关系我们在上一部分已讲得很分明:
如果道生成所有的理(散之在理)
并且理是所有器的依据(则有万殊),
那么道必定生成所有的器(统之在道)。
那么三者在逻辑维度层面,依然可以依据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加以表述:
如果道是所有理的依据
就在这时,砖子和赵仙童的手机几乎同声响起,一个是小鸟叫,一个轻音乐,两人查看信息时,头颅同时伸向对方的手机,同声说,女儿发来的,老爸,你和老妈没什么问题吧?老妈,你和老爸没什么问题吧?
并且所有理是所有器的依据,
那么道必定是所有器的依据。
道、理、器三者的逻辑关系特别明晰,道统理、器,而理又是具体的器之所以为具体而区别于其他具体的具体依据,显然道是最高之本体依据。在表述三者的逻辑内涵上,程颢说得也非常清楚。
“道”是程颢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充塞宇宙的最高实体,也是万物化生的本源,自有永有,恒常不易,“亦无始,亦无终”(《遗书》卷二上)。道化生万物,开启了整个现象界(器)的运动序列,虽然人们无法用语言加以概念性的表述,只能“默而识之”。器的运动来源于一阴一阳之气,一阴一阳之气也是形而下的器,虽然阴阳二气在运动序列中推动具体的器,但器不能构成自身动力因,由此上溯,必然有一个终极的动力因。因为一个序列如果没有开端,就不会有中间和终端,因此道是器之动终极的动力因。器都向着一个目的活动,其活动的有规律性与秩序性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有安排的。“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间无适而非道也”(《二程粹言》),透过宇宙的万事万物有秩序有规律的运行、变化、发展完全可以相信其背后必然有一最高主宰。人类思维的意向性无法把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道收摄其内,只能经由思维的后天逻辑证明,承认这一无限者的存在。“道”在这里相似于康德的“物自体”,人的思维属性无法证明道的全部属性,是不可知。虽然不可知,但我们可以去相信去行动,这就为实践理性把握这一实体提供了可能。明道先生的道就是这种可能性。
道是善的,“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以生为道。继些生理者,只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长也。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遗书》卷二上)。而且道的完善性在整个善的序列中等级最高,是完全的善,器相对于完善的道而言是有条件的完善、或多或少的完善性,“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而阴消,善增而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遗书》卷十一)“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遗书》卷二上)。有条件的完善性都是相对于一个最高的完善性才有意义。
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遗书》卷十一)
物物皆有自己的理,即物之“所以然”或当然之则,或称之为规律。各个具体的事物都依此运行发展,它是具体事物具有独特性的依据。同时物与物之间又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感通、相互联系的,“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3]。天地万物的有秩运行发展又相互感通全依一天理。“万物皆有一个天理”,虽言“天理”,但仍未离物而言理,所以程颢说:“天者,理也;神也,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遗书》卷十一)这种奇妙性由心可以体贴出来,“理与心一”(《遗书》卷五),“心是理,理是心”(《遗书》卷十三)。心在这里可以作为理性讲,道虽不能言说,却可以用理性思维通过器来把握。心是理的物质承担者,与理共生于道,“有道有理,天人一也”(《遗书》卷二上)。有道才有理与器,人依器循理而知道,天人浑然于一本之道。道、理、器的如此抽象的概念在程颢哲学中以生生运行的动势体现出来,形上之道的本体世界与形下之器的自然世界浑然一体,活泼而又生机盎然。
在谈道器关系时,程颢说:“有形皆器也,无形惟道。”(《二程粹言》)“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道。”(《遗书》卷六)“以气明道,气亦形而下者耳。”(《二程粹言》)阴阳二气是有形质的东西,故称器,曰形而下。道因无形质,曰形而上。“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今与后,已与人”(《遗书》卷一),虽然道是形而上,器是形而下,但道与器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器由道生,道由器现,器以必然的存在——道——而存在,否则的话,则无器可能存在。器由道获得自身的必然性,所以说“器亦道,道亦器”。虽然在实体意义上道器不可分,但在生成意义上,两者却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而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东西,“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遗书》卷十一)。器是有,道是不固于有也不固于无,“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器由道生,器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但道却永远存在,“亦无始,亦无终”。
基于程颢形上与形下的区分,依据中国传统哲学术语道、形、器的逻辑关系,我们对程颢哲学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凡是有形质、具体的东西都属于形下的“器”;感性存在的形下之器,理性皆可以抽象地把握其背后的“所以然”,即“形”或“理”;然而形而上的“所以然之然”的本源之道,却不是理性把握的对象,无法言说,只能“默而识之”。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把握程颢哲学中道、理、器的辩证关系:
第一,在生成性关系上,道是本源,道生阴阳而成器,道即器便是理。有道有理有器,万物备矣。理与器不可分离,更无先后,不具有谁产生谁的问题。明道先生所言之“理”在韩秋红教授研究所得来说就是具体事物的“抽象”[4],是具体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道则是“共相”,是“抽象了的存在之上的存在”,即本源性的存在,是一种普通的认知意义上的实在性。理是具有单一性事物的根据,并非具有普通意义,必须在“理”或“形”之上支撑起一普通原因,即道,这样才能解决物(器)普通性认识问题。
第二,在实体性关系上,道、理、器的逻辑关系也很分明。理是器的原因,道是理的原因;理是具体的因,道是普遍的因;理是抽象,保证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道是共相,提供事物多样与差异的可能性。道是一,是绝对,是原因的因;理是多,是相对,是具体的因;器是杂,是具体,是现象。“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可以表述为“理而上者谓之道,理而下者谓之器”。理是连接有形与无形的中间环节,通过这个中间环节可以在杂多的现象背后找出个体原因进而形成普通性的认识。道非可道,虽无法言说,但物(器)可以体现道,透过物(器)可以承认道的存在,虽然无法认知,勉强把握为“无”。“一阴一阳之谓道……则亦无始,亦无终,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处有,亦无无处无”(《遗书》卷十二)。
三
正如史宁中先生所言,中西结合的探讨方式是有意义的,运用这种探讨方式,不但可以清晰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处,又可把这种特质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在中西方文化的根基处把握两者的共通之处。中西方的本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就是实体;中国哲学所说的本体,不但具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实体之意,还有多重含义:有神性意义,即作为具有情感意志主宰万物的至上神;也有自然意义,即作为自然现象运行生化的必然性;又有德性意义,即作为道德的化身,具有与人同样的德性,甚至是人的德性的根据、本源。这些含义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融的。概括来说即潜在性存在,是一种创造与发展的可能性,其实现需要作用、功能,或者说通过作用、功能体现。
通过道、理、器逻辑关系的探讨,我们在感叹中西方哲学共通之处的同时,又不得不敬佩中国先哲思想的深刻与独特。程颢出入释老多年,自家建构的哲学体系极具思辨色彩,程颢哲学的本体论是“体用一源”的本体论,本体之道直接承继老子,道“玄之又玄”,宗教神秘色彩十分浓厚。其形上道之本体,必须由形下器之用来体现。器由道生,道是形而上,器是形而下,道与器虽是不同的两个东西,但却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器以必然的存在——道——而存在,否则无器可能存在。器的运动由阴阳二气推动,而阴阳二气又由道这一终极动力所推动。器的运动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有秩序的,其活动的有规律性与秩序性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有安排的,都向着一个目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体现完善的道。因而程颢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间无适而非道也”(《二程粹言》)。器之所以多样复杂的可能性又由道提供保障。器之所以复杂多样的直接规定性为“理”,即器之“所以然”。而理之“所以然”即器之“所以然之然”就是道,道即理器不分之必然性,所以程颢说“器亦道,道亦器”。我们作为形下之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心体贴道,虽然不能更好言说,但可以通过道德行为来体现道,无限接近具有完善性的道之本体,所以修养论对程颢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这可以说是程颢哲学或者说宋明理学家重建儒学新体系的根本宗旨所在。
明道先生的修养方法首先要识仁,“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智信皆仁也”(《遗书》卷二上)。“天地万物化醇。……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遗书》卷十一)。“人与天地一物也”(《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遗书》卷十一)。道之生谓仁,仁者只有与生生不易之道合一,与万物一体共生共荣,或者说认识了生生不易之道,与万物一体共生共荣,才能被称为仁。天地充满生意,人活天地间如沐春风,人的风格也应当如天地一样豁达从容,优游自得。“……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明道文集》卷三)内外两忘不累于物则心定,体现了道家人生境界。但程颢又与玄学家不同,没有流于颓废。他的自得是通过自家体贴,与生生不易之道合一,与万物共生共荣,过有规矩的生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情怀。那么如何自得与道合一呢?“学者须先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遗书》卷二上)。“以诚敬存之”,存什么?方法论与本体是分不开的,存即存生生不易之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斯所谓仁也”(《遗书》卷十一)。道化生天地万物即为仁,人“继之者善也”。道之本体以生为善,以生为仁,人是有限不完美的存在,只有不断地体道,以诚敬存之,才能去恶存善,人生的意义只有在向着道之本体无限超越和对完善的道无限追求中才能得以彰显。程颢哲学的伦理诉求及道德修养方法是在完善的道之本体追求及实践中实现的,这也体现了程颢哲学目的论的特征。
程颢泛滥诸家,出入释老,后返求六经为往圣继绝学而宗儒,以儒家经学为基础,融合释、老,使自家建构的哲学体系更加具有思辨性,这一点透过道、理、器的逻辑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传统本体论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观点或者说前提,就是把世界二重化:可感的世界与超感的世界。前者是生灭变化的现象世界,后者则是真实永恒的本质世界。中国哲学虽无明确的二重世界划分的观念,却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论证方式,即形上与形下之别范畴体系,通过道、形、器三个核心术语,以形连接现象界与超越界,有形与无形、形上与形下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彼此不可分离,体现了中国哲学圆融一体的特点。故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以“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表达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内在超越的冲动”[5],那么中国哲学则是以圆融的方式表达一种和谐与一体的共生。
程颢通过道、理、器哲学术语的形上与形下之别,严格区分出普通与特殊、具体与抽象、共相与殊相、道与器、理与气等哲学范畴体系。形上与形下的证明贯通整个哲学体系,与其说这是程颢哲学的重要方法,不如说这正充分体现出了其哲学最精微最独到之处:人在体贴理的同时,通过道德实践与道合一进而与万物浑然一体,进入万物齐一的优游境界,另外又不失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入世与出世的完美结合也许就是明道先生所要表达的人生真正智慧!
[1]史宁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评析[J].古代文明,2010,(3):37—4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47.
[3]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三·明道学案(上)[A].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3册)[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4]韩秋红.道、形、器的术语及逻辑——以庄子《知北游》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1,(1):53—57.
[5]韩秋红.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J].江苏社会科学,2010,(1):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