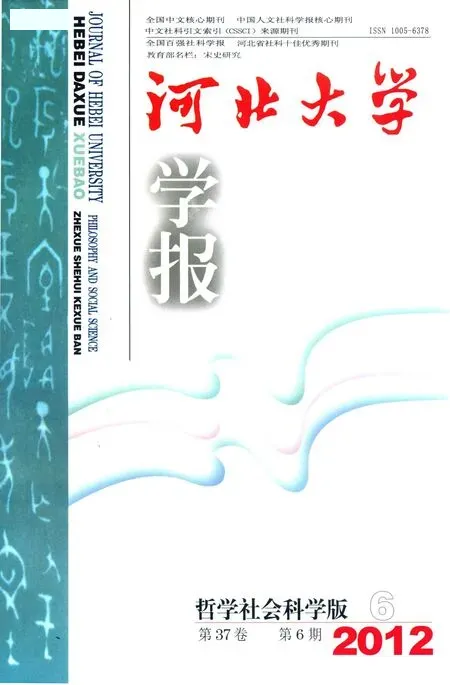英美战争题材诗歌的政治审美维度
2012-04-11王艳文周忠新
王艳文,周忠新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性的文学体式,记录着诗人心灵中的喜怒哀乐,英美诗歌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教授胡家峦在谈及英国诗歌史时指出:“在英国文学史上,自民族史诗《贝尔武甫》直到18世纪现代小说兴起之前,‘诗’几乎是‘文学’的代名词。”[1]1而英美战争题材诗歌在英美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诗歌展示出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和灾难。通过这些作品,诗人描绘出战争狂人们的偏执、野蛮以及给现实世界造成的创痛。战争的暴力野蛮折射出人性丑的一面,诗人从文学文本的角度呈现出战争非人性的本质以及诗人的忧怨情怀。
这些战争题材的诗歌记录着不堪回首的人类历史瞬间,唤醒人们的记忆,在今天我们这个充满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时代,英美战争题材诗歌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战争的本质,传递出人们的共同愿望——远离战争。本文从诗意化的政治隐喻、人性恶的反思、战争的血腥、野蛮性及折射出的诗人的政治审美情怀几个方面探究英美战争题材诗歌的政治审美维度。
一、诗意化的政治隐喻
“何种政治、谁之文学,如何审美等是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三大核心问题”[2]181。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政策、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可以归结于政治的审美层面。由于文学作品在当时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政治意识、社会思想和文化潮流。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政治与文学不可脱离。在战争期间,诗人们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文艺创作或者再创作作为手段,参与战争活动。德国犹太文学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说:“将政治美学化的一切努力都会达到一个顶点,这一顶点就是战争。”[3]121
诗歌是人类思想文化、语言文字高度发展的体现。“诗歌犹如一盏盏古典的烛火,在苍凉的角落闪着温暖的光芒。这些光芒如一枚枚箭,刺痛着黑夜里跋涉着的眼睛,让身虽疲惫的人不至于累倒”[4]5。战争题材的诗歌作为战争生活的反映,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者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5]28。隐喻代表的不是一样东西或者一个观点,而是一种关系,隐喻“除了具有修辞功能、语言功能和认知功能等一般功能外,还具有文学和审美功能”[6]65。战争题材的诗歌隐喻出的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和价值观。如在欧文的著名战争诗歌Dulce at Decorum Est中有这样的描述:
腰弓着,就像压在麻包下的老乞丐,
双膝外翻,象丑陋的老妇在咳嗽,我们用泥巴诅咒,
直到闪耀的火光叠现,我们才背转身,
向着我们遥远的憩息处开始踯躅。
男人们在昏昏欲睡中行进。许多人丢掉了烂靴,
但却瘸行,浸着血污。跛着,麻木了;
疲惫到听不见耳边咆哮落下的炮弹。[7]527
诗人以第一人称描绘出战争中士兵们满身血污,跛着脚,在炮弹的轰鸣中如惊弓之鸟,口吐白沫,躲避着袭来的炮弹,揭示出战争狂人灌输给人们的谎言“Dulce at Decorum Est”(“为国家牺牲是甜美的”)。
同样在哈代《战后的平静》一诗中,诗人通过对战争的反思,展示出了战争的疯狂、邪恶和荒诞,揭示出战争对真善美的摧残。哈代一生中创作出了40多首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美好憧憬。美国诗人惠特曼《百岁老人的故事》一诗,描写了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场战役,许多士兵壮烈牺牲,战斗场面惊心动魄。在惠特曼的全部诗作中,记录南北战争的诗篇在美国诗歌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诗歌以诗意化的语言记录了南北战争期间广大士兵和民众的精神面貌,展现出联邦将士浴血奋战的激情和血染的风采。
“政治首先是权力机构,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政治运作等等。同时。它还是‘情感机构’,因为权利必须通过人来掌握,必须代表某些人的利益,必须追求某种社会理想”[8]112。政治特别注重社会理想的张扬,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把自己的理想蓝图投射到民众的心灵中去,让他们景仰蓝图、歌颂蓝图,自发地萌生出为“美”而奋斗、现身的情感驱动力。政治现实经过作家的内化,诗一般地转化为“政治审美因素”,有深刻的美学意蕴。政治在人们的心中掀起了宛如山崩、烈火、海啸、怒潮的激情。比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动员文艺资源参加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具有互文性效果的是在二战期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欧洲战场上,英国政府着意将莎士比亚描写战争的作品《亨利五世》拍摄成电影以鼓舞士气。
中国文学史上自先秦开始就有“诗言志”的理论观念,记载在《今文尚书·尧典》之中,孔子在《论语》中更加明确地阐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9]169,强调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念。现代学者骆冬青、台湾学者林锡铨等也都提出了“政治美学”的概念。文艺最重要的属性是审美,而进步政治本身可以经由审美主题化为政治审美因素,“文艺应当表现和反映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之美”[9]168。战争题材诗人们如沙松、欧文等等把政治现实经过内化,用诗言志,隐喻出了当时的政治,是诗意化的政治隐喻。
二、人性恶的反思
英美战争题材诗歌很多是诗人饱含深情,以凝练的笔墨,揭示出人性恶的一面,是一首首反思战争的檄文,呈现给世人的是人类战争的“恶之花”。《恶之花》是法国现代主义代表作家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他描写了大城市巴黎的丑恶现象,诗人笔下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以及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认为丑中有美,因而描写丑和丑恶的事物,在写丑中挖掘恶中之美。著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朱光潜认为“丑,也属于审美范畴”[10]12“作为审美范畴的丑是以现实为基础的”[11]128。这些战争题材的诗人们呈现出来的战争之丑无不折射出对人性的反思。如沙松的战争诗歌《基地》(Base Details):
假如我凶悍、谢顶、气喘吁吁,
我也会在基地升为少校,
并且边嚼口香糖边快速地念出阵亡将士名单。
你会看到我浮肿的肥胖的脸,
在最好的旅馆狼吞虎咽,
读着阵亡录时,还会嘟囔着“可怜的家伙,我还认识他老爹呢,
是啊,我们这次战斗损失惨重啊。”
当战争结束后无数青年成为亡灵,
我会信步回家沉沉睡去。[7]568
在这首诗中,诗人沙松描绘出了官僚的腐败,他们吃得肥头大耳,走起路来都气喘吁吁,前线战士们浴血奋战的时候,他们却在最好的酒馆里吃喝玩乐。而面对呈上来的阵亡将士名单的时候,他们冠冕堂皇、漠然地说:“哦,这个战士阵亡了,我还认识他老爹呢,这次战斗损失惨重啊。”诗人以一个阵亡士兵的视角,揭示出战争的黑暗、官僚的腐败。
在哈代的战争诗歌 《敌人》(The Man He Killed)中,描写的是两个互不相识的战士,只是因为战争偶然地被安排在了敌对的战壕,而向对方射击,最后造成互相残杀。如果不是战争,很可能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会在一家小酒馆对酌一番。在另一首战争诗歌Naming of Parts中,诗人瑞德(Henry Reed)把新兵们的武器常识课与花园的美进行了对比。在美的杏花、早起的蜜蜂戏弄花枝、采花蜜的美好意象衬托下,揭示出战争的丑与恶。在美的映衬下,丑的试武器动作如怎么拉枪栓、怎么推子弹等显得更加丑陋不堪。“我们快速地滑动枪栓,即让弹簧松紧自如。早起的蜜蜂来来回回地戏弄着花朵:他们说它在戏弄春天”[7]564。同样的忙忙碌碌,同样的前前后后,同样的词汇spring,一个是枪上的弹簧,一个是美好的春天,可以杀人的滑动的枪栓和戏弄花朵的蜜蜂的意象并置,带给人的是不寒而栗。诗人在诗中用的是零度抒情,注重的是客观化的描述,没有掺杂主观色彩,以一种冷静的白描手法表达感情。这些意象通过审美移情想象的作用达到道德审美的效果。尽管人们常常忽视审丑获得的审美享受,在战争诗人笔下,一幅幅战争的凄惨景象用诸多意象呈现出来。别林斯基说:“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12]57-58
哈罗德·奥尔(Harold Orel)认为”诗歌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诗人们记录下战争的丑,通过审丑,使其作品更加富有生动性、丰富性的生命活力。英国作家赫兹利特说“恐怖是诗,希望是诗,爱是诗,恨是诗;轻视、忌妒、懊悔、爱慕、奇迹、怜悯、绝望或疯狂全是诗”。童庆炳指出“丑的事物之所以产生美感,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学的形式对于内容而言不是被动的,它具有征服内容的作用”[13]24。战争诗人笔下,一幅幅战争的凄惨景象用诸多意象呈现出来,诗人捕捉和提炼自己的情感经验,以富有感染力的形象来表现、创造出饱含意蕴的意象和意境,是一个个瞬息间呈现出来的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比如英国著名战争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在《战争诗抄》中描绘出的凄惨景象。在诗人笔下,战争使人异化,使人沦落到连“猫狗鼠蚤”都不如的境地,人死了,只能“天当棺盖,横尸战壕”“泥灰裹尸,虫蚁食之……”。哈代的另一首战争题材诗歌《奔赴炮兵连》(The Going of the Battery),以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前线士兵的妻子的角度来呈现出战争之丑,泥泞的小路、肝胆欲裂的分离、泣不成声的挥手都表现出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
“丑”刺痛感官,引起思考,在痛苦与厌恶的交织中,引起理智的介入。战争题材的诗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描述和评论战争以及战争的“丑”,描绘出战争的“恶之花”,引起读者对人性恶的反思。战争诗人们“对战争的丑恶面目的再现,给那些想从战争中实现英雄情结的人们一记重拳”[14]139,表达了人们渴望和平、远离战争、痛恨死亡和毁灭的美好诉求。
三、诗人的政治审美情怀
“政治不仅关乎利益而且关乎审美,因为人的主体性是物质和精神的有机统一,人的一切活动规律中内在地渗透着人的审美需要”[15]18。政治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学研究生态的重要维度之一。“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16]70。在英美战争题材诗歌中,透射出的是诗人们的政治审美情怀。一首首令人深思、饱含热泪的诗篇都是一片心灵的世界,展现出的是一幅幅的心灵境界图。黑格尔说“诗歌只为提供内心关照而写作”[17]19。虽然战争诗人们的写作风格不同,对战争的描写由于自身的经历各不相同,如沙松和欧文的战争诗作在直接描写战争残酷的同时,也对战争对战场上作战的士兵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进行描写。但是以战争为题材的诗人们都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战争进行了历史透视,对人类生存状况给予高度关注,因而折射出诗人们的政治审美情怀。
哈代的战争题材诗歌,由于诗人本人没有亲临战场的经历,所以他的战争题材的诗歌没有血雨腥风的战争场面描写。但是诗人用冷峻的视角审视人生,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描绘出了战争对人们身心的摧残以及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和毁灭。哈代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曾经说到:“战争注定会结束的,不是今天或者明天,而是在时机到的时候,是在人类经过内省意识到战争的荒诞以后。”[18]44在《鼓手霍吉》中诗人客观地描述了霍吉在死后“不加装殓,扔进了坑”以及霍吉“化作陌生平原的一抔土”。在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哈代对客死他乡的士兵的深深的同情:
这灌木丛、这粉状的土壤、
这广阔的台地有何意义;
不懂为何每当夜色苍茫,
升起的星星这样奇异。[19]45
而目睹了美国内战的惠特曼,亲身经历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他在组诗《鼓声哒哒》中大声疾呼,号召民众不要犹豫,坚决地投身到反对分裂、反对蓄奴制的战斗中去:“敲吧!敲吧!鼓啊!吹吧!军号!吹吧!”诗人用富有战斗性的笔触,满怀豪情地为南北战争呐喊助威并与北方军民并肩战斗,表现了诗人的政治审美情怀。
鲁迅的“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文学主张其实倡导的就是文学家应该投身到政治中去的情怀。诗人们把政治因素巧妙地转化为审美因素,并物化为“美”的诗章,实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审美意识形态。在英美战争题材诗歌中,一切政治事实折射在诗人们的心灵后,进入到审美的、或者说是审丑的哲理高度,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不朽诗篇。沙松对战争深恶痛绝,他的战争题材的诗篇是声讨战争恶魔的铮铮有声的檄文,是强有力的号召停止战争的声声呼唤。比如在《战壕里的自杀》(Suicide in the Trenches》中:诗人沙松不仅目睹了战争的野蛮、荒诞,而且还亲自奔赴了战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示出诗人也可以是一名战士,也可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Dulce et Decorum Est全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都是平实的词语,但是通篇都充满刺目的意象和刺耳的愤怒。这首诗是上了子弹的一杆枪,瞄准了那些慷慨激昂的民众,每一诗行都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审丑情怀。
在冬天的战壕里,他瑟缩、阴郁,
伴随着轰鸣的炮火、虫蚁和点滴朗姆酒
对着自己的脑袋扣下了扳机
从此,便再也没有人把他提起。[20]381
黑格尔说:“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因此,使这最崇高的东西更接近自然现象,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18]44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惨无人寰的战争——这种政治现实引起了战争诗人们的审美关注,启动了审美期望,激发了审丑激情;那些反动的、迂腐的政治现实,经由诗人们的真情实感的含茹,以审丑的角度为审美主体所感受,实现政治的审美特征。这些战争诗人们以悲伤的笔触,倾诉着生命是如此脆弱,被死亡夺去生命。躲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们无论生前是多么伟大多么美丽,都将变成灰烬。斯托克(Stryk)说“每一位亲历战争的人都会看到,战争没有赢者!”[19]45战争诗人们以诗意化的篇章引起世人的关注,告知人们战争其实就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赢者会扩大或者护卫了自己的市场、材料、能源以及影响力,那些指挥官们获得升职,但是那些普通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他们充当了炮灰,让妻儿、母亲们或惶惶不可终日,或悲痛欲绝承受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每一首诗都表达了诗人的政治审美情怀。
四、结 语
“‘好的政治’和‘好的文学’有着共同的人学内涵和价值追求”[21]134,都强调对和平、幸福的渴望和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追寻。文艺最重要的属性是审美,文学是文艺的一个重要分支,因而文学应当表现和反映体现价值体系的政治之美。生活在战争年代的有责任感的战争诗人们,不可能远离政治,他们直面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些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打入人们的情感世界,使之产生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激动与共鸣,战争诗人们“以己之情煽大众之情,使之普泛化”。英美战争题材诗歌强调了人对生存情景——战争场景、心灵创伤的感受,表现了诗人对生命意识的反省,对伦理道德的评价、对公平正义以及和平的执着。大多数现代战争诗歌描述的是战争的野蛮和残暴,诗人们通过描述战争中和战后带来的肉体和情感之痛,挖掘战争带给人类的精神地狱。沙松、欧文等亲历了战场的诗人们由于拥有一手的战争经历,他们笔下对战争的恐怖、丑陋和兽性的描写更加逼真。审视英美战争题材诗歌的政治审美维度,探究其政治审美因素恰恰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1]胡家峦.英美诗歌精品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卢衍鹏.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J].社会科学,2011(7):181-186.
[3]BENJAMIN WALTER.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tivity[M].Second version.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Ed.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Jennings.Vol.3.(1935-1938).Cambridge,MA:Harvard UP,2002.
[4]颜学军.百年诗歌赏析 [M].九江: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2002.
[5]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8.
[6]王艳文.《贵妇人画像》中隐喻的叙事功能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9(6):64—66.
[7]LAURNCE PERRINE,THOMAS R.ARP.Literature—Structure,Sound and Sense[M].The United States: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3.
[8]高永年,何永康.百年中国文学与政治审美因素[J].文学评论,2008(4):112-116.
[9]徐曙海.试论文艺与政治的审美和谐[J].江苏社会科学,2008(3):168-172.
[10]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1]王艳文,刘丽霞.英美现代派文学的审丑性评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3):128-131.
[12]胡适.寄沈尹默论诗[C]//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3]孙书敏,刘文斌.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的形成及其演进[J].中国文学研究,2010(2).
[14]AHMAD ABU BAKER.The Theme of‘Futility’in War Poetry[J].Nebula,September 2007.
[15]彭自成.诗意化的政治隐喻[J].理论月刊,2006(10):16-18.
[1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7]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8]LORRIE GOLDENSOHN,Dying in War Poetry[J].The Yale Review,Volume 100,Issue 2,Mar 2012.
[19]飞白.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M].吴迪,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
[20]HERBERT LOMAS,The Critic as Anti-Hero:War Poetry[J]Hudson Review,1985:Autumn.
[21]范永康.当代西方的文学政治学[J].国外社会科学,2011(4):12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