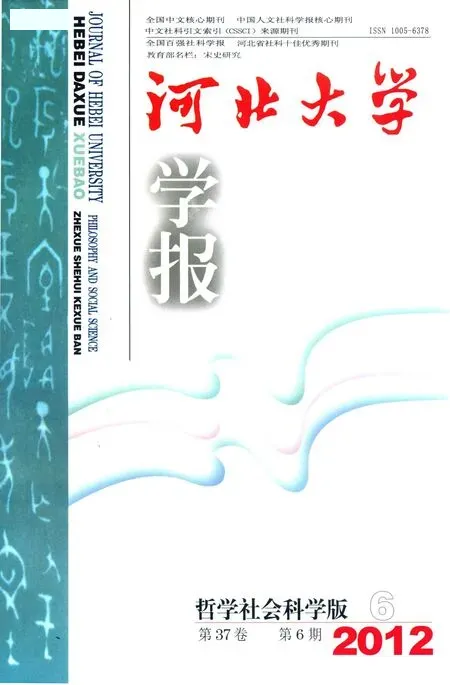北朝鲜作家笔下的朝鲜战争——1950年代中国报刊刊载一瞥
2012-04-11常彬
常 彬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二战结束后,共同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同盟国解体,以苏美为代表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峙,冷战格局形成。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出太平洋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损害中国统一的核心利益。北朝鲜军队一度占尽先机,战线直推韩国南部釜山一带;9月15日美军的仁川登陆,拦腰切断了战线过长的北朝鲜军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火北推,直达中朝界河鸭绿江岸,轰炸了中国的边境城市,严重威胁新中国安全。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朝鲜半岛上由此形成了一场区域性的国际战争,冷战对抗下的三年热战,它就是朝鲜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美国学者、战争亲历者贝文·亚历山大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韩国和一些联合国成员的支持下,赢得了一场针对北韩的战争,输掉了另一场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这两场战争的起因性质完全不同:北韩人公然进行侵略而被挫败;红色中国人努力保护其家园免遭潜在的入侵威胁而获得胜利。”[1]虽然仅是美国学者的一家之言,但确实有其值得深思的地方。
这场战争,催生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朝鲜战争文学”,中国、北朝鲜、美国、韩国均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①笔者曾耗时一年查阅1950年代中国大陆8大报刊和省级以上的出版社刊载出版的朝鲜战争文学作品,篇什达4000篇/部以上。仅1950年代北朝鲜大型文艺刊物《朝鲜文学》《新朝鲜》就刊载此题材作品560余篇;美国朝鲜战争文学,仅长篇小说就有100多部。参见常彬《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政治与人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中国和北朝鲜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化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极其相似,国家关系友好,以兄弟相称[2]。中国的报刊杂志,比较关注朝鲜半岛的文学艺术,介绍其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当代文学作品[3]。尤其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经常刊载北朝鲜作家作品,这些作品多以朝鲜战争、抗日战争为题材或背景,反映朝鲜人民的苦难抗争,阶级斗争的凶险激烈,革命领袖的伟大英明,中朝军民的生死友谊。
本文所涉的北朝鲜作家的朝鲜战争,主要指刊载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报刊杂志、以反映朝鲜战争题材为主的北朝鲜作家的文学作品。笔者以1950年代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8大报刊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文艺报》《新华月报》为研究对象,搜索翻检了北朝鲜作家发表(或转载)于此的朝鲜战争文学作品在130篇/部以上,有小说、诗歌、散文、特写、剧本、歌谣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内容划分,主要有以下三类作品:
一是表现中朝军队和人民战斗友谊的作品。小说:韩雪野《战斗的友谊》[4]、金道荣《阿妈妮的心》[5]、李泰俊《高贵的人们》[6]、金学铁《英雄》[7]和《在严峻的日子里——纪念胡家庄战斗十周年》[8]等。诗歌:洪命熹 《中国人民志愿军来援》[9]、金尚武《一座城市》[10]、林和《哪怕送一碗饭——献给给志愿军弟兄们》和《来吧,亲爱的姊姊!——献给志愿军中的女同志》[11]。散文:崔承喜《友爱的道路》[12]、话剧剧本:洪建《“一二一一”高地——“伤心岭”》[13]等。
二是反映朝鲜军民战斗生活和阶级斗争的作品。小说:权正龙《渡江》[14]、韩雪野《离别》[15]、李北鸣《恶魔》[16]。特写:韩雪野《歼灭——姜泰运代理中队长战斗记》[17]、韩雪野《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18]、金 顺 石 《在 前 线 》[19]、洪 淳 哲 《平 壤 的 一天》[20]、赵基天《朝鲜在战斗着》[21]、黄泰山《游击队生活——朝鲜战斗生活素描》[22]、宋镇银《夜袭美军基地》[23]、佚名《朝鲜女英雄李顺壬》[24]、白应法《女侦察兵》[25]、佚名《光荣的朝鲜女飞行员——泰善姬》[26]等。
三是歌颂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领袖,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仇恨“美帝国主义”及其霸权主义的作品。散文:李阳燮《朝中友谊万古长青》[27]、李 泰 俊 《伟 大 的 新 中 国 》[28]、朴 正 爱 《朝鲜——伟大斗争的旗帜》[29]。诗歌:洪淳哲《献诗二章》[30]、洪哲淳《请接受献给你们的光荣》[31]、洪淳哲《献给伟大的中国弟兄们》[32]、洪淳哲《献给毛泽东主席》[33]、朴八阳《功勋》[34]、闵丙均《我们的友谊》[35]、金常午《不能消 灭的火焰》[36]、朴英东《憎恨》[37]、崔尚恩《美国侵略军的“俘虏收容所”是活地狱》[38]等。其中颂诗写得最多的是洪哲淳,时任朝鲜共和国访华团团长,巴金等资深作家曾经撰文对洪哲淳的颂诗进行了热情洋溢的称赞[39]。
这些刊载于中国报刊杂志的北朝鲜文学作品,除了在翻译上存在语言生涩、汉语表述上欠规范外,相当一部分作品,就内容和情节模式上看,很难将它们与同期中国作家的同类题材作品区别开来,容易在阅读中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新中国文学,注重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和意识形态灌注,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观长期以来左右着文学创作的理念运思,描写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右派等)的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以此表现剑拔弩张的阶级矛盾、泾渭分明的阶级路线,突出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国情相似的北朝鲜,也有这样的文学反映,比如土地改革的欢欣、还乡团的复辟、勾结日本人的朝奸、投向美国军的地主,因政治道路不同的兄弟反目,以及对美军的丑化等等。北朝鲜作家李北鸣《恶魔》里的北朝鲜老人朴佥知,土改中分得了地主的田地,日子开始好过起来。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儿子参加了人民军,在军事失利中(指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朝鲜战局)跟随部队向北边撤退。老人望着“北撤后的公路,光秃秃的,干静得仿佛用扫帚扫过似的。人、汽车、炮车、牛马车都向北撤退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留下的仅是天空、山峦和灰尘扑扑的公路。这几天,这条公路在老人看来,似乎就是走向地狱的路”[16]78。这“地狱”就是还乡团的地主投靠美军势力,卷土重来回到村里,到处清算那些分他们土地的农民。他们杀害了老人的媳妇和刚出生的孙子,还抓住了老人负伤的儿子,将儿子、媳妇和孙子的三颗人头装在麻袋里,送给老人作“礼物”,以报复他对土改成果的分享,悲愤的老人从此拿起武器参加了游击队。小说的立意在于揭示阶级斗争的残酷血腥、敌对力量的“恶魔”本性,表现老人仇恨满胸膛地走向杀敌战场。这个情节处理,与中国作家峻青小说《黎明的河边》很相似:小战士小陈和父亲掩护武工队的同志渡潍坊河,母亲和弟弟被还乡团押到河边作人质,小陈在保护同志的战斗中牺牲,母亲和弟弟也被敌人杀害,从此,游击队中出现了一位身体黑瘦、脸气阴沉、目光炯烁、杀敌英勇的老战士,那就是小陈的父亲。
同时,《恶魔》在人物的塑造上也着力于阶级对立和阶级分层,贫苦农民出身的朴佥知老人一家,代表了革命的力量;美国兵贾克、加入联合国军的日本人吉田①《恶魔》里美国走狗“吉田”,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同名,这也许不是一个意外的巧合,而是一个指向十分明显的寓意象征,寓指战败国日本二战后完全倒向美国。战后日本,惟美国马首是瞻,充当冷战格局下美国的亚洲走卒。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天皇制度保全,军国主义及右翼势力并未根除,为日本右翼势力日后否认战争罪行、颠覆二战反法西斯成果埋下了祸根,中日钓鱼岛之争即是战败国日本对战胜国中国领土的公然侵占,源于美日对钓鱼岛的私相授受。、朝鲜地主金炳全和黄主事,代表了反革命的力量。在这个反革命阵营中,曾经奴役过朝鲜民族的日本人,成为了朝鲜地主的政治同谋者,一起投向美国势力。而且敌对力量中也存在阶级分层,美国兵、日本人、朝鲜地主、地主狗腿子,地位尊卑依次递减。日本人吉田对美国兵点头哈腰奴才相十足,他“为了掩饰自己是日本人,在朝鲜人面前——尤其是在不熟识的人面前,总是紧紧的闭着嘴装着哑巴,这条狗非常会看主子的眼色;他毫无差错地领略了美国兵贾克的口哨和他用下巴指示的命令”,尽管如此,因为私藏了从朴佥知家里搜刮出来的金戒指被美国主子发现,美国兵当胸给他一记老拳并抢走了戒指,还用日本话对他劈头盖脸地恶骂臭打。地主狗腿子许万世更是奴才的奴才,他用“被烧酒烧坏了的喉咙”发布告示、威胁农民:“对大韩民国和大总统李承晚博士要忠诚,对美国也要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后不管什么税,应该在期限内缴纳,同时地主黄主事三天之后就要回来,种他地的人,如果不准备租子的话,那么一定要吃苦头……”[16]79、81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斗争,摆在刚刚获得土地、但又得而复失的朝鲜农民面前。其场景的描写和情节的展开,以及地主与农民的斗争,颇有几分像《闪闪的红星》里地主胡汉山回到村子里对农民进行的反攻倒算:“我胡汉山又回来了,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在阶级分析思路下,普天之下地主阶级的反动凶残,不仅是中国的胡汉山、南霸天、黄世仁,朝鲜地主们也概莫能外。中国和北朝作家笔下地主阶级的作恶和还乡团的残暴也极其相似。中国作家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采取了将朝鲜战争的进程和中国农村土改、合作化发展“双轨同时推进”的写法,力图描摹朝鲜战争风云和国内建设斗争形势既双轨推进又互为交叉的全景画面。将中国农村和朝鲜农村的两个自然时空作为同一政治理念叙事的不同空间对接,表现农村的阶级斗争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局部现象,它直接和国内乃至国际大格局中更为复杂严峻的敌对斗争密切呼应:在冀中农村,地主谢清哉们仇恨土改,做复辟梦,听说美军打到朝鲜了,气焰立刻嚣张起来,“朝鲜一起战事,他们那气儿就更粗了。以前是小声地说,现在是大声地骂(农民)”;到处张扬“现在形势不同了,美国有好几百万大军开到了朝鲜,说话就进来了。今天盼,明天盼,这一天总算盼到了”,威胁分到他们土地财产的农民:“我那桌椅板凳,犁耢锄耙,就是粪叉子在谁家,我都知道。你现在不给我,你以后得敲锣打鼓给我送回来,我还不定要不要哩!”[40]59-60在朝鲜某村庄,还乡团洗劫了在土改中分到田地的农民,并将他们杀害,村口的一株高大的白杨树上,“用铁丝捆绑着一个赤身裸体的老人,面前是一大堆柴火的灰烬。他的全身都成了赤红色,上身前倾,早被烧成弓形。在他的小腹上,还用长钉子钉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印刷品,上面盖着朱红色的大印。凑近一看,原来是一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土地证。……郭祥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猛可地想起自己的父亲被‘还乡团’开肠破肚,把血淋淋的心肝挂在树上的情景,心里一阵剧痛,就好像那根钉子是钉在自己身上似的”[40]389。地主还乡团的猖狂反扑,朝鲜老人被“烧成弓形”,中国老人被“开肠破肚”,中朝地主们反攻倒算的反动性、残忍性、血腥性是那么地惊人一致,其间看不到因国情、民情、习俗、文化、个性等诸多差异而呈现出的“这一个”地主和这一方水土的不同。说明了处于同一意识形态框架的中朝两国,文学认知上也体现着很多的相似和雷同。
中国文学对美军形象的鬼化、漫画化、“纸老虎”化,不仅在其精神层面,也在其外貌上的“画鬼”摹写。而且这些形象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差别的“鬼也似”的人物,从审美心态上对美军形象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图释。他们如“罪恶的毒蛇”“凶鬼一样”“恶狼一般”,有“凶恶的眼光”“长毛的手”“紫红的嘴唇”“鬼魂似的”“魔鬼面孔”,没有战争个体的独特性表现,而是政治理念化的贴标签、概念化的“画鬼”模式[41]。
北朝鲜文学对美军也进行了极度的丑化,但在具体意象的表达上与中国作家的“鬼化”描写有所不同,多用“狗化”的比喻来描写美军和表达仇恨与蔑视的情绪:美军是“长着狗牙的杀人鬼子”,北朝鲜的“战士们都自信着美帝侵略军与我军同志的分别,一看就如同狗屎和人一样地很清楚地被判别出来”[17];当美国“强盗们正在像狗争粪一样喧闹着的时候,冲击来的游击队员射出了复仇的子弹”[16];吉田“这条狗非常会看主子的眼色;他毫无差错地领略了美国兵贾克的口哨和他用下巴指示的命令”[16]。表现美军道德的沦丧是“哼着卑鄙的歌曲”、喝酒、活命、女人、不要祖国;毫无人性,“对活出来的自己与同伴死者对照,有幸灾乐祸的表情”;贪生怕死,战斗还没开始,就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17]。中国文学的同类题材,与此有着惊人的相似:“一群美国兵在那里吸烟、喝酒,有的在耸着肩膀哼着淫荡的歌曲,有的嚎叫,有的喧笑。”一辆燃烧的美国吉普车里还传出“那种淫荡的美国音乐”[42];从美军飞行员身上搜出的照片,“这个瘦脸的胡子刮得光光的流氓,搂着一个裸体的日本女人,坐在自己的膝盖上”[40]283。中国和北朝鲜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对资本主义文化“贪图”个人享乐、“贪恋”一己生命的“颓废性、腐朽性、反动性”上的理解与诠释上,都凸显着那个时代的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模式。
我们发现,中国报刊杂志上刊载的北朝鲜文学,表现中朝军队“战斗友谊”的作品很多。应该说,这样的主题表现,是彼时北朝鲜政治和战争现实的文学反映,也符合当时中国和北朝鲜主流意识形态诉求,中国文学也有很多诸如“老战友”叙事、歌颂中朝友谊的同类题材表现。
北朝鲜作家李泰俊《高贵的人们》[6]里的北朝鲜军医院看护长金玉实,曾在中国的解放军部队里做护士,回到祖国后她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她照顾中国伤病员不怕脏累,力单体弱的她多次为他们输血,一次次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安全转移中国伤员,直至最后牺牲。小说以看护长温柔亲切的声音为伏笔和线索,在神志不清的中国重伤员陈平秀的模糊听觉中,这个熟悉的声音唤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位朝鲜护士输血给他,救了他的性命,他亲切地称她为“姊姊”;如今“姊姊”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回响——看护长日夜守候在他的床前,为他输血、擦洗、唱歌,温柔的声音就像当年的“姊姊”。美军飞机轰炸,看护长背着他冲出燃烧的房屋,她被机枪射中,弥留前的她突然被他“听”了出来,就是当年救过他命、现在又为他受伤牺牲的那位“姊姊”。伏笔的“扣”结在伤员陈平秀初次听到看护长声音引起的回忆,“解”在看护长牺牲前为保护他在奔跑中的呼喊。在这里,“姊姊”的含义具有了双重含义:志愿军伤员的血管中流淌着朝鲜民族姐妹的血液,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有着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情;“姊姊”到中国支援中国革命,志愿军到朝鲜半岛打击美国军,志愿军为了“姊姊”的祖国而负伤,“姊姊”为了志愿军而牺牲,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患难朋友、是坚贞的战友。
在北朝鲜文学的作家队伍中,金学铁是应该被关注并重点提及的作家。他1916年出生,朝鲜元山人。1936年毕业于汉城高等学校,1938年毕业于中国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同年在武汉参与组建朝鲜抗日义勇军,任义勇军分队长、八路军宣传干事。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太行山对日作战中腿部受重伤被俘,送日本长崎服苦役,以政治犯被判10年徒刑。由于在监狱里拒绝写悔改书,腿伤3年多未予治疗,导致腿部左下肢截肢。1945年日本投降,金学铁获释,在汉城开始文学创作。1947年任北朝鲜《劳动新闻》记者、《人民军报》总编辑。因性格耿直、政见不合,1949年后定居中国,但仍保留朝鲜国籍,为中国文联和延边文联的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2001年去世。著有长篇小说《说吧,海兰江!》《激情时代》《二十世纪神话》,中篇小说《泛滥》《繁荣》,短篇小说集《军功章》《乔迁》《苦闷》《无名小卒》,散文集《我的路》,传记文学《抗战别曲》,报告文学《高峰起遗书》,自传《最后的分队长》,以及《金学铁作品集》《金学铁短篇小说选》等。他的作品与同期北朝鲜作家创作相比,艺术性和思想性显胜一筹,有较为独特的内涵和令人咀嚼的意味。
金学铁的《英雄》[7]刻画了志愿军和北朝鲜军的两位英雄,歌颂他们在战斗中互相支持、在功劳面前互相谦让的美好品质。朝鲜士兵杨云峰炸美军坦克,快接近坦克的时候,坦克里的美国兵探出头来向他射击。危急时刻中国士兵胡文平跃出战壕,一枪射中了敌人,掷出了手榴弹,炸毁了坦克,自己也身负重伤。杨云峰把胡文平背下火线,送进部队医院。北朝鲜军方表彰杨云峰勇炸坦克的勇敢行为,杨云峰没有在荣誉面前贪功隐瞒,坦诚地说出炸掉坦克的人不是他,而是中国军人胡文平,并把胡的番号告诉了上级。后来杨云峰也在战斗中负伤,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因伤势过重而去世。苏醒过来的胡文平面对朝鲜军方送来的锦旗和军功章,坚持说炸坦克的人是杨云峰而不是自己。在巨大的荣誉和战功面前,两位军人“死无对证”地将功劳归之于对方,将平凡化之于自己。到底谁是炸坦克的英雄此刻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美好品质和高尚人格,超越了炸坦克这一行为本身,绽放出意义远不止于此的人格光芒,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真正英雄。
《在严峻的日子里——纪念胡家庄战斗十周年》,是金学铁以自己在中国抗战的一段经历为蓝本而创作的一篇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而他自己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因负重伤而被日军俘获,押解到日本监狱。小说反映抗日战争期间,一支“朝鲜义勇军”帮助中国人民抗战,他们在中国太行山下的胡家庄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因寡不敌众而被俘或牺牲。日军惊诧于这些穿着八路军制服的朝鲜人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一位俘虏“自豪地笑着回答:‘我们是为了打倒日本鬼子,和八路军一起合力作战的朝鲜人!’正如同在中国有汉奸,也有爱国者是一样的,朝鲜也有不是‘高丽棒子’的人”。日军劝降他们,说“你们虽然犯了一时的错误,可是仍然还是回到祖国大日本帝国的怀抱里”①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亡国。日本占领者在朝鲜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灌输朝日一家,同文同种,以此规训朝鲜人的大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这些被俘的朝鲜人毅然地回答:“我们不是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我们是被你们抓来的俘虏!”[8]57、55小说意在表达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都共同遭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都有国破家亡的民族伤痛,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朝中人民是坚强的战友、日本军国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作品在表现朝鲜军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时,有一个意味深长、值得重视的细节——被俘的朝鲜义勇军人“我”临刑前的一段心理活动:
我想我应当取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行动,随着先烈们的榜样,我也要宏壮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朝鲜人民万岁!可是——用哪一国话来叫呢?用中国话吧,那么鬼子们又听不懂,用日本话吧,又不能教育伪军们……嗳,算了,还不如就用朝鲜话叫吧!好,那样倒好得多。[8]56
作为“朝鲜人”的义勇军战士,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日寇的临刑,“用哪一国话”来喊出最后的心声——用中国话,鬼子听不懂;用日本话,伪军听不懂;用“朝鲜话”,鬼子和伪军都听不懂。就义者最后选择了用本民族语言——鬼子和伪军都听不懂的“朝鲜话”,发出临刑前的慷慨激昂之声。这段心理描写,看似矛盾,实则反映的不仅仅是个语言的选择问题,更是朝鲜人的民族尊严、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问题。他们的祖国虽然被日本强制性占领而亡国,他们是“失去祖国的孩子”②舒群小说《失去祖国的孩子》(短篇,1936年),反映日据时代,一位失去祖国、无家可归的朝鲜孩子的亡国之痛,被苏联学生奚落为“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高丽这国家了”。,但他们依然坚持民族抗争、民族不亡的信念,即便在人之将死、英勇就义的最后时刻,血脉中涌动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他以自己的母语“朝鲜话”喊出了“朝鲜人民万岁”的心灵呼唤,选择了伪军和日军都无法听懂的朝鲜语。这是一种值得玩味的心理真实和潜意识本能,犹如人在大祸惊惧或死亡恐怖中冲口而出的“我的妈呀!”,一定是毫无思虑脱口而出的母语表达,那是他/她最深的根的情结和血脉认同,是本能的体现。
在艺术表现力上,这篇小说与同期的北朝鲜作品相比,显见成熟,尤其是对中国民众麻木不仁、争看杀人场面的描写,很有鲁迅笔下鞭挞“看客”的风格。受伤被俘的朝鲜义勇军人“我”因拒绝投降而被日本人送上刑场: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是躺在一辆停住不动的马车上了这是街道的当中。许多的居民把我包围起来,并且在叽叽咕咕地议论着。好奇的眼睛、同情的眼睛、侥幸于“不幸”并没有落在自己头上的安心的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人们都成群成群地跟着,为了赶来看枪毙人的热闹、不懂事的孩子们兴奋地到处钻着。一个押送兵用枪柄驱散着看热闹的人们、另一个日本军就趁火打劫地把街旁一个小摊上的花生结结实实地装满了两口袋,那被抢的小贩只是哭笑皆非地瞪着那个满载而去的日本兵。[8]55、56
看客们“好奇的眼睛、同情的眼睛、侥幸于‘不幸’并没有落在自己头上的安心的眼睛……”,观赏他人灾难而自己幸免的噬血兴趣,犹如鲁迅笔下拼命拉长脖子看杀夏瑜的眼睛、欣赏祥林嫂讲述阿毛故事的眼睛、闪着“两颗鬼火”看阿Q游街杀头的眼睛、北京的羊肉铺前张着嘴看剥活羊的眼睛、荒野中四面奔来“要鉴赏这拥抱或杀戮”的眼睛,欣欣然地“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43]11的无数看客们眼睛: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们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了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44]156-157
鲁迅对中国庸众冷漠麻木、噬血残忍的国民性的深刻揭示,在北朝鲜作家金学铁那里我们也获得了一分精神上的共鸣。
北朝鲜的文学创作,有不乏如金学铁《在严峻的日子里》之类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两相兼顾的佳作,但仅就刊载于中国报刊杂志上的作品而言,它们与同期的中国文学在相关题材的表现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阶级斗争的理念运思、二元对立的人物描写,雷同化的情节模式,注重战事过程而少心灵刻画,更缺乏对人与战争的深度思考。但北朝鲜文学也有一些异质于我们的如民族心理、意象运用和叙述方式,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既像我们又不是我们的另一国度的文学表达。
[1]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前言[M].郭维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常彬,杨义.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3]陶冰蔚.朝鲜文学作品在中国[N].人民日报,1960-08-14.
[4]韩雪野.战斗的友谊[J].文艺报,1951,2(11、12).
[5]金道荣.阿妈妮的心[J].解放军文艺,1956(1).
[6]李泰俊.高贵的人们[J].人民文学,1951,4(5).
[7]金学铁.英雄[N].光明日报,1952-03-22.
[8]金学铁.在严峻的日子里——纪念胡家庄战斗十周年[J].人民文学,1951,5(2).
[9]洪命熹.中国人民志愿军来援[J].解放军文艺,1956(6).
[10]金尚武.一座城市[N].光明日报,1951-04-24.
[11]林和.哪怕送一碗饭——给志愿军弟兄们、来吧,亲爱的姊姊——献给志愿军中的女同志[N].光明日报,1951-01-23.
[12]崔承喜.友爱的道路[N].文汇报,1951-12-25.
[13]洪建.“一二一一”高地——“伤心岭”[J].解放军文艺,1954(5).
[14]权正龙.渡江[J].解放军文艺,1954(10).
[15]韩雪野.离别[J].人民文学,1952(10).
[16]李北鸣.恶魔[J].人民文学,1951,5(1).
[17]韩雪野.歼灭——姜泰运代理中队长战斗记[J].人民文学,1951,3(4).
[18]韩雪野.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N].人民日报,1953-06-26.
[19]金顺石.在前线[J].人民文学,1950,2(4).
[20]洪淳哲.平壤的一天[N].文艺报,1954(15).
[21]赵基天.朝鲜在战斗着》[J].人民文学,1951,4(4).
[22]黄泰山.游击队生活——朝鲜战斗生活素描[J].人民文学,1951,3(4).
[23]宋镇银.夜袭美军基地[N].文汇报,1951-07-17.
[24]朝鲜女英雄李顺壬[N].文汇报,1951-09-07.
[25]白应法.女侦察兵[N].光明日报,1951-01-30.
[26]光荣的朝鲜女飞行员——泰善姬[N].光明日报,1951-10-16.
[27]李阳燮.朝中友谊万古长青[N].人民日报,1960-08-10.
[28]李泰俊.伟大的新中国[J].人民文学,1952(6).
[29]朴正爱.朝鲜——伟大斗争的旗帜[N].文汇报,1951-01-18.
[30]洪淳哲.献诗二章[N].光明日报,1952-05-07.
[31]洪淳哲.请接受献给你们的光荣[N].人民日报,1952-03-18.
[32]洪淳哲.献给伟大的中国弟兄们[N].人民日报,1952-01-26.
[33]洪淳哲.献给毛泽东主席[N].人民日报,1952-05-06.
[34]朴八阳.功勋[N].人民日报,1958-10-31.
[35]闵丙均.我们的友谊[J].人民文学,1954(10).
[36]金常午.不能消灭的火焰[N].文汇报,1950-12-07.
[37]朴英东.憎恨[N].文汇报,1950-12-07.
[38]崔尚恩.美国侵略军的“俘虏收容所”是活地狱[N].光明日报,1951-11-29.
[39]巴金.充满热情的诗篇[N].人民日报,1952-07-21.
[40]魏巍.东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1]常彬.抗美援朝叙事中的政治与人性[J].文学评论,2007(2).
[42]刘白羽.安玉姬[M]//刘白羽.刘白羽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3]鲁迅.复仇[M]//鲁迅.野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C]// 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