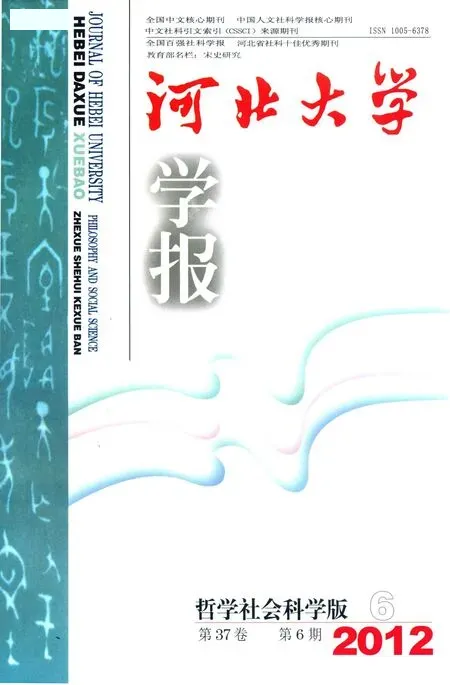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
2012-04-11赖彩慧
黄 健,赖彩慧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晚清以降,中国传统以“九州方圆”为中心的国家认知及其形象塑造,遭遇了来自西方以科学测绘、计算为特点的天文地理学的巨大挑战,随着新知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在“学习西方”的浪潮中,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索重塑新的中国民族国家形象问题,无论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的《四洲志》,还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所展现出来的都是一种对未来中国的新的想象。民国建立后,第二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民主”“科学”“自由”价值影响当中,则是更多地展现出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批判,从中寻找重塑现代文明中国形象的意义建构。在这当中,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和批判最为突出。他曾勾勒出“四千年文明”中国的“吃人”形象,成为迄今为止,现代中国对“老中国”形象解构和批判最为深刻的一种比喻性展示。纵观鲁迅对“老中国”形象解构与批判的特点,不难发现,鲁迅分别是从纵、横和纵横交互的三个维度对来进行的。纵的维度是通过对传统文明的反省,展现出对对“老中国”历史的深刻剖析;横的维度是通过对现代文明的建构,表现出对“老中国”现实境况的执着批判;而纵横交互的维度,则主要是通过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联和交互,三位一体地展现出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深度思考。
一
与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不同,鲁迅自从在南京求学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之后,就开始注重用“物竞”“天择”一类的新观念来观察古老的中国,如同他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的现状[1]。东渡日本求学后,在广泛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当中,他对处于新旧转型时期中国的思考又有了新的发现,认识到所谓民国虽然已是“共和”,“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本质[2]。正是用这种用现代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思维,鲁迅在考量重塑“中国形象”当中,首先是要展开对“老中国”形象的“破”,也就是要对“老中国”形象进行整体的解构和批判。他多次指出“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并同时又坚信“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3]①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鲁迅也这样感叹道:“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于是,他坚持选择“抗战”“反抗”的方式来解构“老中国”形象,如同他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4]
依据这种思路,鲁迅首先是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中国的历史,认为中国历史始终未能走出“一乱一治”的“怪圈”,指出:“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5]这种“破坏”又“修补”的循环,使中国一直未能走出做“奴隶”的时代,只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里周而复始地循环,形成所谓中国历史“超稳定”的状态,而这样,“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6]212。奴隶的历史,造就的是奴隶的性格,从来就不曾有过“人”的意识,更谈不上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和人的地位。鲁迅就是这样深刻地发现了中国历史的“吃人”现象。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他说:“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7]在鲁迅看来,“吃人”就是“老中国”历史形象的本质特征,在《狂人日记》中,他对此进行了最具颠覆性的解构: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吃人”是奴隶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由于未曾有过“人”的意识,“吃人”使得做奴隶也是心甘情愿的。鲁迅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6]211通过对传统的反省,剖析摧残人的历史罪恶,鲁迅认为,奴隶、奴性是“老中国”给予人们最直接的形象展示,表明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但仍然是静态的停滞不前,老气横秋,暮气沉沉,毫无活力。为此,他多次强调要以史为鉴,强调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8]16
对于“老中国”的这种历史形象,鲁迅在小说创作中予以了最生动的艺术展示,“未庄”“鲁镇”“S城”,都是他展示的“老中国”的系列形象景观。
“未庄”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虚构的中国南方的一个村庄,也是小说主人公阿Q活动的主要场所。鲁迅在小说中对“未庄”是这样描写的:“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
表面看上去是南方水乡的秀丽景色,但“内骨子”里却处处透露出旧中国乡村的闭塞、衰败和凋零,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未庄似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革命党”已经进了县城,而未庄却并“没有什么大异样”,更何况县政权改头换面为“革命”新政府,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不过改称了什么”。在未庄,无论是有权势的乡绅赵太爷、赵秀才父子,还是普通的百姓,都是依然如旧地生活着,不是对外部的“革命”茫然无知,就是另作图解。如未庄的几个“盘辫家”,与假洋鬼子有交往,听他吹嘘“革命”而将信将疑,故采取盘辫子这种依违于清政府和革命党之间的“骑墙”做法,足见“看风使舵”的投机性格。还有阿Q、王胡、小D一类游民,靠着“精神胜利”法,过着“倚强凌弱”的生活,嗜酒、赌博、打架、偷盗、调戏妇女,作奸犯科,乘势作乱,为己谋利。在未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内心深处的隔膜,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上的愚昧落后,都呈现出“老中国”社会的形象老态。
与“未庄”不同,虚构的“鲁镇”是中国南方一个小镇,有着像“酒店”一类的公共场所,如在《孔乙己》中,鲁迅就特意提到“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如咸亨酒店那“当街的曲尺形大柜台”,孔乙己就是经常在这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然而,他依然是迂腐和麻木愚忠的。他无视时代的变动,也不知镇外的变化,而是依旧依照自己的方式“过着日子”。尴尬的身份,迂腐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背时者”“落伍者”。在鲁镇,咸亨酒店一类的公共场所,无论是掌柜、小伙计,还是那短帮长衫的平民百姓,无一例外地都显示出一种“不合时宜”的老态。他们聚集在酒店这样的公共场所,嘲笑、捉弄他人,由此获得某种快感。如他们嘲笑孔乙己,从中寻找乐趣。其实,这个没有人情的小镇,彼此都处在“看”与“被看”“示众”与“被示众”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与爱。”《祝福》所展示的“鲁镇”,与《孔乙己》不同,它是构成“杀死”祥林嫂的特定空间。小说虽然没有指控究竟谁是迫害祥林嫂之死的“凶手”,但实际上指的是生活在“鲁镇”的所有的人。鲁四老爷、四太太、祥林嫂的婆婆、以及后来的大伯、柳妈、鲁镇的男女老少们,共同组成了以“鲁镇”为代表的中国旧文化、旧传统的罗网,用不同的方式对祥林嫂进行了肉体、精神的摧残、迫害,使祥林嫂始终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时代里苦苦挣扎,最后只能是孤寂与冷寞地死去。
“S城”似乎是指鲁迅的故乡绍兴,但又不完全是。不论是《朝花夕拾》所指的现实的“S城”,还是小说虚构的“S城”,展示的也都依然是“老中国”的形象。现实的“S城”,是鲁迅成长的空间,反映出他真实的生存境况。对于这座“S城”,鲁迅感到的是难以忍受的冷酷、冷漠和压抑,他说:“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9]小说虚构的“S城”,也不仅仅只是故乡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使人感到空前的无奈、孤独和使人愚昧的“城”,如《在酒楼上》提到的又“飞回原地点”,即又回到“S城”的无奈,《孤独者》中所描写的在“S城”“我”则是处处感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的孤独,《故乡》中回到故乡“S城”遇到儿时伙伴闰土那一声“老爷”声中透露出来的愚昧,都是“老中国”这座“城”的真实形象境况:沉重、麻木、压抑、僵化。
“老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乡土社会,恪守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训,如同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10]通过对“未庄”“鲁镇”“S城”为代表的“老中国”历史形象的展示,以及对生活其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如“孔乙己”“华老栓”“闰土”“阿 Q”“祥林嫂”等,鲁迅就将“老中国”在“一乱一治”的奴隶时代中循环,在无形中“吃人”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形象认识和深邃的历史思考。
二
与解构“老中国”的历史形象不同,用现代文明标准批判现实,是鲁迅解构“老中国”现实形象的一个显著特点。鲁迅曾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11]通过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从社会横断面上来展现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剖析和批判,是鲁迅批判“老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认为,现实就是历史的自然延伸,“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12]。虽然已经是民国时代,但“老中国”形象阴魂仍然无处不在。鲁迅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8]17以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社会,以现代文明标准批判现实社会,是鲁迅对“老中国”现实社会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13],解构“老中国”现实形象的价值尺度。
如果说对“老中国”历史形象的解构,鲁迅主要侧重于对“吃人”本质的批判,对历史“一乱一治”循环的“静态”“老态”的揭示,那么,对“老中国”现实形象的解构,则主要侧重于对时弊的揭露,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与批判,旨在深化对“老中国”历史形象的批判,将现实看作是历史延伸的一部分,从而达到整体解构“老中国”形象的目的,促使现代中国加快文明的步伐,树立起现代文明中国的形象。
基于这种对现实的审视理念和态度,鲁迅选择了杂文这种方式,展开了对“老中国”现实形象的批判。在鲁迅看来,杂文是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它的特点是以短小精悍的形式,针砭时弊,批判现实丑恶,揭露社会黑暗面,是现实的“匕首”和“投枪”,是时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14]。因此,以“杂文”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对“老中国”的现实形象进行解构,显示出鲁迅对“老中国”历史与现实认识的老练、深邃和自觉。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15]。从形象解构上来说,采用杂文的方式,其特点就是以横断面的剖析方式来展现“老中国”形象的现实丑态。鲁迅说杂文的特点是:“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 ’。”[16]抓住“杂感”来做文章,鲁迅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对“老中国”现实形象作出最直接的观感评判,对不适合现代文明的现实丑态进行直接的揭露。
依据“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价值尺度和审视思路,鲁迅通过杂文方式解构“老中国”现实形象,主要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全方位地展现现实社会对于现代文明的严重不适应性和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二是整体地反思中国国民劣根性,力图找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滞后的症结所在。
鲁迅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17]现代中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水准,都还远离现代文明,给予人们的形象观感,仍然是落后、愚昧、麻木、无序和混乱的。鲁迅在《热风·四十二》中这样描绘“老中国”延续的现实形象:“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有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
在《华盖集·“碰壁”之后》中,鲁迅再将这种“老中国”的现实形象作了更直观的展示,他说:“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接着,他又以幻感的形式再将现实丑态进一步具象化:“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鲁迅指出,来自“老中国”的“这蛮风,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假如此前者为白纸,将由此开始写字,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18]332-333不同于一般的时评文章,鲁迅对时弊的针砭和批评,旨在整体解构“老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颠覆其一以贯之的传统形象。他始终认为,以“民主”“自由”“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已是“洪流所向,则浩荡而未有止也”[19]。现代中国要重塑自身新形象,就必须打破历史“超稳定”的循环,走出历史的“怪圈”,创造出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6]213整个中国社会才能迈入“沉邃庄严”的“二十世纪之文明”世界[20],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一员,“在当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所以,鲁迅反复强调:“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21]
从现代文明的世界洪流中审视“老中国”的现实形象,剖析中国现实社会,离不开对国民性、国民精神的反思。鲁迅说:“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18]334这种善于用精神虚幻的方式来满足对世界的认识,显然与现代文明的价值原则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结果只能是加速国民性的堕落。鲁迅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22]为此,他重点考察了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并将其提升到国民性格心理的层面予以认真的考量和剖析。他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就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23]在他看来,“内骨子是依旧”的现代中国依然没有植入任何现代文明的种籽,黑暗的现实社会依然是“暴君”统治着的“专制社会”,造就的是“奴性”国民性格和心理。他认为,“奴性”性格心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奴隶性”,二是“奴才性”。前者给予人的是“逆来顺受”的“臣民”形象,其特点是“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24],而后者给予人的则是“中山狼”“变色龙”一类的“小人”形象,其特点如同“叭儿狗”“山羊”和“猫”一样善于“献媚态”。他称奴才为“万劫不复”,并指出:“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25]又说,往往“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26]。对国民性的反思,特别是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鲁迅将“老中国”历史的“吃人”形象,再次在现实的层面上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反省和批判,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他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
通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剖析“老中国”的现实形象,使鲁迅对时弊的批评,上升到了对整个国民性进行改造、重铸民族魂灵的高度,从中展示了他深邃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反思精神,展现出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现代性思想,如同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27]
三
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价值指向则是未来的中国。在他的历史观中,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三位一体的。他指出:“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28]又指出:“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29]因此,通过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联和交互,三位一体地展现出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深度思考,是他解构“老中国”形象,以及重塑现代文明中国形象的思想基点。
尽管鲁迅内心对未来总有些犹豫、疑惑和彷徨,但对于未来中国的形象重塑,他还是一直在寻求肯定性的价值建构。在他看来,真正的解构并不是简单的颠覆和否定,深层次的企盼仍然是希望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新的蓝图。在完成小说《非攻》创作不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他就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不是通过一般的逻辑推理,而是借助被解构对象的固有资源,由表及里,深入其中,打破其“固态”结构,以达到颠覆、解构的目的。通过对“老中国”历史和现实形象的双重审视、剖析和批判,鲁迅不仅表现出一种认识“老中国”形象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而且展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思想和新思维。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一改原先创作中多取材于“病态社会”“病态人生”的方法,转而从历史的“神话、传说、史实”中寻找重塑中国形象的资源。1935年1月4日在致萧军、萧红信中,他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用中国人最忌讳的“刨祖坟”方式来重塑中国形象,依然延续了他解构“老中国”形象的思路,但重点却是展现超越一般性形象重塑的新思维、新理念。虽然解构本身是破坏式的,然而,这并不是终极目的,而是在其中蕴含着更高的价值建构性指向与目的。换言之,鲁迅解构“老中国”形象是以现代性价值建构为指向的,他把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来审视的,并纳入一个更大的框架之内来把握,如同茅盾所说那样是“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世界[30],从中展现他重塑未来中国形象的价值考量。为此,鲁迅抛弃了以往历史小说创作纠缠于“史实与虚构”的写法,而是采取“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方式,激活历史,穿越历史,重构历史,凸显出创作主体对于历史、现实和未来认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中表达他对中国历史命运和未来前景的高度关切。像《补天》,就借弗洛伊德学说解释创造的缘起,表现创造者的心理苦闷,《奔月》写神话中射日英雄的困境和孤寂,《铸剑》通过荒诞情节的刻画,突出义士与暴君誓不两立的复仇精神,而在《理水》《非攻》等小说里,则正面塑造大禹、墨子等信念坚定、埋头苦干的“中国脊梁”形象,《采薇》《出关》《起死》等寓意历史,古今杂糅,从历史透视现实和未来,从中探寻未来中国如何展现文明形象的可能性。在鲁迅看来,解构“老中国”形象,展开对未来中国形象重塑的思考,不是简单地重塑一个新形象来代替旧形象,表现一种廉价的乐观,而是要释放出更多形象展示的可能性,并将其留给未来,让人们能够在未来的时空中,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展开对文明中国多样性、多元化的理想企盼和想象。如果说历史的真相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永远是无法弄清楚,但人们依然能够在解构历史当中,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如同波普尔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它一种意义。”[31]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从中贯穿着他对未来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合理想象,赋予了一种对未来文明中国价值建构的意义内涵。
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站在时代思想发展的高度,描绘出了一个步履艰难地跨入20世纪现代文明的“老中国”形象,从中也寄寓了他对未来中国命运和前景的深切企盼与充分想象。在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位一体的整体中国形象当中,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真正的用意也是在提示人们: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中国,其实还并没有为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作好充分的准备,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依然是“老中国”及其子民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依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在近代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冲击之中,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整个中国却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它的无奈、惶惑、颓唐,尽显愚昧、无知、麻木之态。在鲁迅的笔下,这是人与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与现代,通过国民劣根性所展示出来的“老中国”永恒的矛盾及其形象观感。鲁迅当然不希望这种情景永久留存下去,他要通过对历史、现实、未来、国民性等一系列问题的剖析,开启思想启蒙之路,完整地传达出他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并以超越于有限历史之上的心理透视,在最广泛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探寻上,引发出关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命运的诸多精神命题,以此来表达他对民族生存状况和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和深邃思考。他始终是把重建新的民族国家的火一样的激情、热忱,裹夹在冰一样的冷静观察和考量当中,描绘出了一个民族、一块大陆的整体惶惑,整体徘徊,整体的对现代文明的严重不适应性,深刻地阐释出有关民族生存、性格、心理及其命运的历史寓言意义,面对“万难破毁”而“绝无窗户”的“铁屋子”,发出他的呐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这呐喊声,在时代的幽谷中长久的回荡,震撼着每一个国人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关联着现代中国文化泛文本中最基本的语义内容,构筑了一个极具启蒙意义的象征世界,使所展示的“老中国”形象,一开始就超出了有限的表征意义范畴,传导出整个民族在转型时期的内在苦痛和心灵律动,包孕着对千百年历史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在民族心理中积淀的深度反省。
显然,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也成为鲁迅借以探寻和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意识和心理性格的一种独特方式。民族生存境况、国民的愚昧精神状态,国民奴性心理性格,乃至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蕴含在这种解构之中。如同沈雁冰所说的那样,读鲁迅的作品“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绝的阳光。”又说:“在他(指鲁迅)的著作里,也没有‘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歆羡与自慰(像许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32]沈雁冰的见地是十分深刻的、独到的。应该承认,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在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也是革命性的。
[1]鲁迅.两地书·四[M]//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
[2]鲁迅.朝花夕拾·范爱龙[M]//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3.
[3]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4.
[4]鲁迅.两地书[M]//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
[5]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M]//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7-358.
[6]鲁迅.坟·灯下漫笔[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书信集·180820·致许寿裳[M]//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3.
[8]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M]//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鲁迅.朝花夕拾·琐记[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3.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68.
[11]鲁迅.华盖集·题记[M]//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
[12]鲁迅.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M]//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1.
[13]鲁迅.两地书·十七[M]//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3.
[14]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M]//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
[15]鲁迅.准风月谈·后记[M]//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
[16]鲁迅.三闲集·序[M]//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
[17]鲁迅.伪自由书·序言[M]//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
[18]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M]//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鲁迅.坟·科学史教篇[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
[20]鲁迅.坟·文化偏至论[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
[21]鲁迅.热风·三十六[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7.
[22]鲁迅.坟·论睁了眼看[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0.
[23]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M]//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2.
[24]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M]//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2.
[25]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M]//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2.
[26]鲁迅.准风月谈·我谈“堕民”[M]//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7.
[27]鲁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M]//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5.
[28]鲁迅.华盖集·答KS君[M]//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1.
[29]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M]//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25.
[30]茅盾.玄武门之变·序[C]//故事新编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137.
[31]波普尔.开放社会的敌人[C]//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66.
[32]沈雁冰.鲁迅论[J].小说月报,1928,19(1):2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