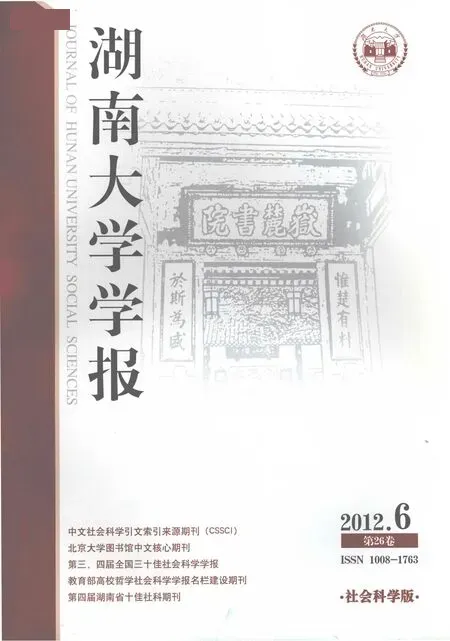仁心、觉心与本心——朱熹心论三议*
2012-04-08向世陵
向世陵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朱熹将“心统性情”解释为由性而情的发用流行,也就同时承认了以仁义礼智为内涵的心之本体的发用,实际会产生不同的路向,即或者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善,或者走向情迁于物的不善,从而导致了心仁关系的多样化和本心是否有失的问题。
一 心有不仁
心之本体为善,是朱熹心论坚守的基点,也是性善论的基本前提。所谓“却是心之本体本无不善,其流为不善者,情之迁于物而然也”①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92页。。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心既流于恶,便不能谓之“统”性情,因为它在发用中已经失去了自身的主宰地位和主导作用。“仁者,本心之全德”②朱熹:《论语集注·颜渊》,《四书章句集注》第13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仁也必然是不善:“心失其主,却有时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③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92页。由仁德构成的本心是纯善的概念,集中体现了心之本体的价值。但是,朱熹虽然始终坚守本心之善,却又不得不解释恶、即需要面对发用的问题。心与仁德在现实中是否统一,需要考量双方在后天的具体关联和实际善恶状态。一句话,一心之中有善有不善也。
就是说,一旦采用“心统性情”的构架而将本体与发用放在一心的发用流行之中,心、善、仁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出现变数,多样化的走向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在理学史上,对于一心之中有善有不善的问题,理学各派都有自己的回答,并因之牵涉到如何考量心与仁的关系。这里可以参看从程颐到湖湘学与到朱学的两系对此问题的看法:
问:“‘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体有善而无恶,及其发处,则不能无善恶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先生以为下句有病。如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岂可直以为心无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别得体与发处言之否?”曰:“只为他说得不备。若云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体无不仁,则意方足耳。”④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第2439页。
程颐对于“心有善恶否”的问题,虽然给予了“心本善”的肯定性回答,但他的回答本身是有层次的,即随后所说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并以为这就像“水”本来只叫水,但随着东西不同的支脉分派又叫做“流”一样⑤程颐:《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4页。。水体与脉流的关系,即是本善之心本体与其发用的有善有恶之情的关系,程端蒙的解释大意不差。但将此联系到胡宏的“人有不仁,心无不仁”,便明显发生了龃龉。朱熹认为其下句有毛病,在心是可以出现不仁(不善)的。因为在孔门,即便是颜子也难免三月之外心有不仁,其他诸生就可想而知,所以不能一般地说心无不仁。
这一问题从来源来说,无疑为孟子所引发。孟子提出了“仁,人心也”⑥《孟子·告子上》。的仁与心同一的命题,但也看到了有放其心而不知求的现实,实际认可仁与心的同一不是绝对的。比起孔子来说,孟子的立足点已有不同。孔子讲“不违仁”是就人的操存践履而
言,孟子的仁—— 人心却是基于其先天的本性,故前者要求至而不违,后者则主张养而不放。
朱熹对二说进行了调和,并将关注点移到了心理合一的本体论基础上:“如‘心’字,各有地头说。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这是心合理说。如说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是心为主而不违乎理。就地头看,始得。”⑦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84页。所谓心字的“地头”,明里是孔孟自己的观点,实则即朱熹的本体论基础。从朱熹的理本论出发,孟子的仁即人心,是在仁理合一的基础上发论;孔子的心不违仁,则是指心作为主体的意志努力,是心依从理。由此,“合”与“不违”不同,“合”是就仁心的先天来源说,“不违”则依赖于人心的自觉状态。在后者,心违仁乃至不仁的情况便是可能的。不过,对于“心与理合”方面的问题,朱熹还有另外的讲法:
问:“莫是心与理合而为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动,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学,理会甚么事?只是理会这些子。”⑧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一,第785页。
就本来天性说,心就是仁,在本体层面不存在合不合的问题;但就现实来说,受私欲扰动的发用之心又离开了仁,心与理便有违了。在此意义上,讲“仁,人心也”就具有更深一层的寓意,即儒者的学习进步,说到底在于领会内在的仁德或天理,此乃人心之根基,即孟子之语在这里已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回到朱门师徒围绕胡宏“人有不仁,心无不仁”观点进行的讨论,朱熹的归结,是认为不应简单地说胡宏未能区分开心之本体与发用。胡宏的问题主要在于不完备,即相对于人的不仁,可谓心无不仁;但就心之自身来说,又要知晓心无不仁是专指本心即心之本体的方面,而不包括其流行发用在内。
二 诚意有觉
要保证心之本体的发用端正不偏,“诚意”的涵养功夫就必不可少,所谓“意诚而后心正”也。至于意诚何以能保证心正,朱熹的解答是:
问:“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意发于心,则意当听命于心。今曰‘意诚而后心正’,则是意反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体何尝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盖由邪恶之念勃勃而兴,有以动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莹净宁息,盖因波涛汹涌,水遂为其所激而动也。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学者苟于此一节分别得善恶、取舍、是非分明,则自此以后,凡有忿懥、好乐、亲爱、畏敬等类,皆是好事。大学之道,始不可胜用矣。”①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6页。
意念既为心之所发,按理当以心去定意,但朱熹的要求正好相反,是通过诚意去安心。心体由性到情的发用与由心到意的发动,在心理过程上不完全一致,前者之不善在受形气的影响而偏于贪欲,后者之不正在受情绪干扰而产生邪念。虽然意念的邪恶有别于物欲的贪求,但在心体发用的偏邪不正上实际又统一了起来,结果便是以情欲、邪念而扰乱了心本体,这就如同波涛汹涌而搅乱了水体本身一样。所以,“大学之道”的下手处就不应是本体之心,而是躁动之意,这就需要通过慎独等工夫使意念诚实,去其躁动和污秽,“然后水之体得静”②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6页。,使心体恢复纯正。如能做到意诚心正,则人之一切喜怒好恶的情感发动无不中节,止于至善的最终目标也就可以实现了。
当然,先后的意义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心与意双方都需要做功夫。按《中庸》的理路,“意是指已发处看,心是指体看。意是动,心又是该动静。……若不各自做一个功夫,不成说我意已诚矣,心将自正;则恐惧、好乐、忿懥引将去,又却邪了”③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6页。。从体用关系的角度考察心与意关系,一方面是用根源于体,但另一方面未发之体又是通过发动之用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双方构成的是一个整体。不是先已意诚了而后自然会心正,而是诚意又需要正心的功夫。从而,恐惧、好乐、忿懥等情绪活动的发用才能不再受外物左右,一切恰到好处。所以,朱熹既要在下手处意义上讲“先诚其意”,又要从体用关系上补以正心之功④诚意与正心的关系在朱熹,实际上也是一个反复纠结他的问题。双方既可以是一个功夫,也可以是两个功夫:“‘诚意正心’章,一说能诚其意,而心自正;一说意诚矣,而心不可不正。”又云:“若论浅深意思,则诚意工夫较深,正心工夫较浅;若以小大看,则诚意较紧细,而正心、修身地位又较大,又较施展。”见 《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7、306页。。
但是,由于心该动静而分体用,一切问题说到底都纠缠于心,所以朱熹感慨“‘心’字卒难摸索”⑤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6页。。人在昏昧蒙蔽之中而能悟得本体,所依赖的,一是依凭于天的本体光明,一是人心终有觉醒的空隙。“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⑥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第4页。源于天的本明之体作为心之本体,也就是天性,它最终不会被污染昏昧。心一旦有觉,光明的天性便能乘此“空隙”闪现出来,由体到用而通达明了。在朱熹,“一有觉焉”的本体“洞然”,不是禅宗的顿悟,但也不是“磨镜”似的逐渐复明,是“忽然闪出这光明来,不待磨而后现,但人不自察耳”。再恶之人,昏蔽之极,也有显露真心、良心的“空隙”,问题只在主体放过不放过而已⑦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七,第377页。。
朱熹在这里不赞同消磨之法,因为这影响到本体的光明常在,他需要维护本体存在的绝对性和发用的当然性;但不少时候他又是认同消磨之法的。对于人生修养来说,善恶乃是相对之词,消恶即是向善,突出的是成就圣贤的现实可能性。天命本体常在,人只在觉与不觉,使善的心之本体与善恶间杂的人心众相能够融通起来。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平时缺乏格物致知的工夫。按他所说:“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⑧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第4页。人在格物致知的践履中,能够随其心之所发而觉察认识,由此端绪入手,而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便能由发于外之恻隐羞恶现象反求于心本体自身,从而得以“觉悟”光明本体的究竟。
从朱熹的“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来说,持续的致知和操存功夫,是觉察本体于一念之微并发扬光大的必要条件。因为“介然之觉,一日之间,其发也无时无数”,譬如《孟子》书中之例,见孺子将入于井而有恻隐,齐宣王不忍牛之觳觫而以羊易牛,都可以说是良心的发现,但前者表现的是普遍性,贴切现实而人容易明白;后者则是说特殊性,故需要孟子的专门引导。即尽管良心或本心无时不在发现,但若平常失却穷理致知之功则不可能识得。如果坐等良心“等大觉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这般时节”?因为“大觉”在朱熹,只是在格物致知的践履中养成,不可能先已大觉了,再去等待和察知良心或本心的发现。即“觉”在致知涵养之中而不是之前。所以,朱熹不认可湖湘学派先觉良心苗裔而再加存养的“以放心求心”之方。
同时,胡宏答“以放心求心”应对齐王见牛之事不妥,还在于“只觉道我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见牛时方求得”①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第1401页。!暂且不论湖湘学派的本来意图,朱熹在此观点上的见解,是觉“放心”正是心体自身的觉醒显现,而胡宏之言则是以一心求另一心了。当然,朱熹自己也有以“是底心”知得和治理那“不是底心”的两个心,前者为主而后者为客。但所谓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就是人知觉善恶的是非心。按朱熹的解释,这不是并列的二心,而是一当你觉知到这个不是底心,你就是是底心(治理了不是底心);如同你觉知到这个非礼底心,你就是礼底心(不再非礼)一样,他以为这便是从程子哪里来的“以心使心”说,二心实质上仍是一心。②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七,第376~377页。
三 不失本心
在朱熹,本心与心之本体都是常用的概念,二者本质上同一,但也有一定的差别:心之本体的概念主要使用于体用关系的架构,说明的是客观层面的先天实体存在和后天流行发用的关系;本心一词亦指道德实体,但重点在引出主体自身的存养状态和如何保持仁德的不失,以便从实践中解决从孔孟以来直到湖湘学和闽学都在考虑的心与仁的一致性问题。就是说,仁固然是指“浑然天理”,但这天理在后天实践中却时时面临着可能失去的问题,从而突出了胜欲复礼的反求本心功夫的重要。朱熹说:
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极好,尽用子细玩味。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间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来。理是此心之所当知,事是此心之所当为,不要埋没了它,可惜!只如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为之。③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三,第558页。
湖湘学的“不失本心”所以好,就在于点出了圣学的核心所在。为什么?因为本心固然是道德实体,但同时也是实践主体,人之知理行事,修身治国,无不凭借本心而行。但要做到不失本心,必须从私欲的裹挟中去扶持它,这样又回到涵养本心的问题。
当然,这一问题最初仍是由孟子发端。孟子首提本心的概念,在他这里,本心是指与物质欲望相对应的道德心,此心从根本上维系着人的价值存在,也就是孟子在此之前刚表述过的仁义之心——良心。本心或良心虽是“人皆有之”,但人若不操存涵养,没有坚定的道德操守,则又可能失去它,这便是孟子所说的“失其本心”④《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兴起,推尊孟子,自然也接过了本心的概念,并且,与孟子相似,强调了环境对本心的影响,如张载以《尚书》的“习与性成”为据,说明从政为官者的德行,是“入治朝则德日进,入乱朝则德日退”,如同婢仆初到时勉勉敬心,随后的走向却取决于环境一样,结果是“谨则加谨,慢则弃其本心”⑤张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张载集》第282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那么,张载的本心就是人未受环境熏染前的爱敬之心或初心。这一观点,在程颐获得了完全的共鸣,但在分析上又有加深,即本心的渊源问题。
程颐曾要弟子思考“孝弟为仁之本”的问题,既然是“思本”,就要回到先秦文献这个文献之本去全面考察为仁之本。故而弟子后来的理解,便将《左传》的“天地之中”、《礼记》的“五行之秀”和《孟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统合了起来,以天地五行之灵秀中正发明人初生所具之爱敬,即从生成之良善证成道德之根本——本心。以此“本心”解释孔子的“本”而要求“务本”,是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创建,原来经学视野下的具体德行规范,变成为理学氛围中人之为人的普遍道德良心。为维护这一良心或本心,就必须注意周围环境对本心影响,这在张载和程颐师徒,都利用了《礼记·乐记》的理欲关系模板,说明人被物欲所感而不节,就可能逐物而灭理,从而丧失本心:“及夫情欲窦于中,事物诱于外,事物之心日厚,爱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随丧矣。”弟子此解,程颐深以为然,认为“能如此寻究,甚好”①程颐:《遗书》卷二十三,《二程集》第309~31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进一步,从孟子到张、程,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本心丧失的问题。这在他们眼中,人在艰难的情况下保存本心较不困难,困难的是安乐的环境中,人反而容易丧失它。孟子当年便有揭示:“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②《孟子·告子上》。至于为什么会是如此而不会是其反面,并未见有更多的解释,大致仍是基于“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一般历史教训。
程颐学生曾问老师,颜渊住在陋巷,贫贱的常人也住在陋巷,二者区别在哪里呢?程颐回答说,二者在穷困时没有区别,都能保持本心,但一当到了富贵的环境,常人诱于物欲而不能自持,故失去了本心,颜渊则能保持本心不变③见程颐:《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第320页。。之所以是如此,就在于常人不能节制欲望。程颐思量的前提仍然是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对待“欲”需要考虑量的多少,因为只有寡欲才能养心。但孟子并未说明“欲”到底是如何一种心理状态,程颐则有发挥,认为心只要有向往追求便是物欲,而不必是完全沉溺于其中④见程颐:《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45页。。朱熹接下来分析说: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⑤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下》,《四书章句集注》第374页。
从二程到朱熹,“欲”本身不是一个否定的范畴,欲可以寡而不能绝,绝欲等于否定了人的生存本身,所以不可。问题的关键,在对于欲望能否恰当节制,如果不节甚而放纵,它便成为与天理对立的人欲,结果便不得不被否定,本心或者说仁德的丧失也就不可避免。
那么,如何才能挽救呢?朱熹引来了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认为只有克除私欲而复归天理才能回复到本心仁德。他说:
仁者,本心之全德。……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⑥朱熹:《论语集注·颜渊》,《四书章句集注》第131页。
对于“克己复礼为仁”的本来意义,朱熹并不十分关心,他是按天理论的胜欲返理思路来予以阐释的。在他这里,天理被人欲所坏似乎也具有必然的性质,但正是因为如此,本心全德的“全”,就不能依赖先天存在的本身,而是需要从修养功夫上着眼,立足道德实践去保证本心天理的寻回和保全。
在这里,本心全德之仁的概念,突出了本心的意义在于为人的后天道德实践提供先天必然的善的根据,但是仁这种先天必然地位又不是绝对的,它随时可能由于后天人欲的污染而丧失,所以,它的意义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要肯定本心的先天必然性质,人克己去私的道德自律才有可能进行;另一方面又要承认本心会受到污染,因为只有如此,主体自觉的道德修养实践才有存在的必要。
那么,问题也相应有主客两个层面。从客观层面看,“仁只是一个浑然天理”⑦朱熹:《朱子语类》卷六,第117页。,而天理的客观必然性在朱熹是全部理论的基石。所以,从孔孟到胡宏、朱熹,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归结无疑都在心与仁的一致性上,只是这种一致在理学集中表现为仁心的实体化和天理化,性理本体融入了仁与心的耦合之中,从而才便于解释心中之理基于内在潜能的自然生发。如称:“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⑧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85页。与理合一之心便是仁心、本心,它的随事而发即是本心自明的客观实现机制。但是,仅有客观层面又是不够的,随事而发本身受外界环境影响可能走偏,必须要主观层面的涵养操存作为保障。故称:
人心“操则存,舍则亡”,须是常存得;“造次颠沛必于是”,不可有一息间断。于未发之前,须是得这虚明之本体分晓。及至应事接物时,只以此处之,自然有个界限节制,揍着那天然恰好处。⑨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第1401页。
从未发到已发,操存涵泳之功不可有一时之中断,才能由未发之前的“虚明之本体分晓”顺序走向已发之后的“天然恰好处”的中节。在这里,“本体分晓”实际彰显了心本体或本心所具的自明而明它的资质,同时也表现出自明资质与操存涵养相互依赖的工夫特色。即本心要发用得正,离不开时时处处的操存涵养;但操存涵养又非以他心来涵养本心,“只以此(本心)处之,自然有个界限节制”。由于人并没有本心之外的其他资源,所以最终仍只能依赖本心的自明。
孟子当年曾批评墨者夷子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是“二本”,朱熹认为夷子最后接受了孟子的批评,原因就在于夷子有本心之明。他说:
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于先后之间,犹知所择,则又其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也。……盖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学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①朱熹:《孟子集注·滕文公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62~263页。
夷子虽然主张爱无差等,但在爱的施行次序上又有先后之别,这种有别的选择,在朱熹眼中就是本心之明的觉醒,说明本心虽然曾遭受蒙蔽,但终归不会熄灭而能自觉其非。本心的这种自觉作用是道德修养之所以可能的最后根据,一切为善去恶的工夫最终都落实在本心之明上,以所明攻所蔽,结果自然是事半功倍。
由此,本心或者虚明本体的实际上担负了循环解释的功能:一是作为知觉意义上的认知和行为主体,能够摒除蒙蔽而发明本心;二是知觉主体所以能明善去恶又是源自于本来仁心的先天善德。例如,朱熹强调“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此一心来整合现实中的人心、道心之异,必须的方法是“惟精惟一”,所谓“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②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可是,鉴于虚灵之心可能导向人心、道心之异,并不能当然地“守本心之正”和“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那么,作为结果的本心得正和道心为主,又变成了为虚灵之心发挥作用定向的前提。
所以会是如此,除了在本心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手段可资利用这一基本现实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人不失本心本来是朱熹治学传教的最终归结。朱熹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四书集注》中引胡氏语说:
圣人之教亦多术,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循其序而进焉。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声为律而身为度矣。③朱熹:《论语集注·为政》,《四书章句集注》第55页。
显然,“不失本心”的目的属于结果的方面。从其“欲得此心”的说法看,本心的自明起初至多是一种志向,它只能落实于长期念念在兹而为之不懈的工夫之中。而且,这还只是形式的方面,内容上则是一疵不存而万理明尽方可。明理也就是明本心,使其“本心莹然”,其标志是随所意欲莫非至理,是将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安放在了天理论的框架中。在此框架中,欲为心用,矩乃道体,然道体又是心体,欲不逾矩在于作用本来是本体的表现,声便是律而身即是度,本心的光明莹然即心中之理发用流行的结果,从而最终实现本体与发用双方的完全协调一致。朱熹通过他的本心论与心之本体说,再一次为他体用合一的宗旨作了论证。
就本心论自身来说,朱熹是以得本心为基本的线索的。遥想当年,孔子与宰予辩三年之丧,到宰予离开而孔子再发其论,以宰予为不仁,朱熹评论说,孔子这是“深探其本而斥之”。本者,仁也,本心也。孔子“又言君子所以不忍于亲,而丧必三年之故。使之闻之,或能反求而终得其本心也”④朱熹:《论语集注·阳货》,《四书章句集注》第181页。。就是说,假如宰予知晓了孔子后来所说之话,当能由此反求而得其本心,体验到内在的仁德。同理,齐宣王以羊易牛,若能于此反求,同样也能得其本心。尽管这在齐宣王并未成为现实,“然见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⑤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07~208页。,无疑是在反求的道路上了。本心是仁心,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也就在所难免,从而导致行为的颠倒错乱,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一句话,本心失则万事皆失也。而得本心的手段惟在于反求,反求本心也就成为了朱熹心论的最后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