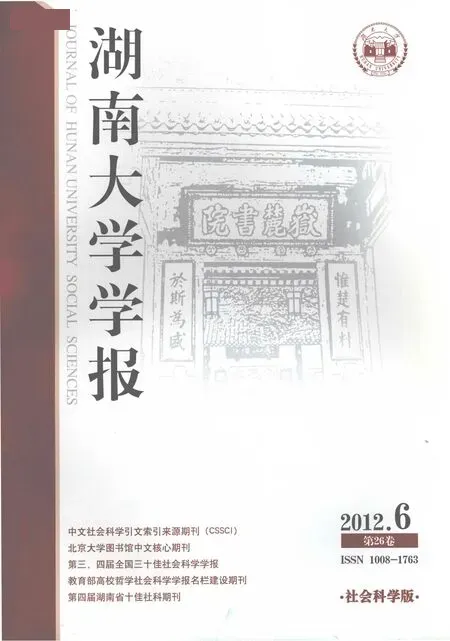礼文学正名、祛惑与有关原则*
2012-04-08陈戍国
陈戍国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什么是礼文学?两个要素:一、必须是文学,不是哲学、经济学等区别于文学的其他社会科学,更不是自然科学;二、必须与礼有关,反映礼制礼典礼义或礼俗。就具体作品而言,用比较大的篇幅说明礼制、阐述礼义、描绘礼典或礼容而富生动性、形象性的各体文章,或用情节、形象反映礼制或礼俗的文学作品,才是我们称呼的礼文学。
随便举几个例子:《尚书》的《金縢》《康王之诰》,《诗经》的《鄘风·相鼠》《小雅·宾之初筵》,《楚辞》的《国殇》《招魂》,荀子《礼赋》,西汉司马长卿《子虚赋》《上林赋》,扬子云《长杨赋》《羽猎赋》,晋潘安仁《籍田赋》,梁武帝《孝思赋并序》,唐杜甫“三大礼赋”,宋王禹偁《南郊大礼诗》,元吴草庐诗《赠人求赙》,明成祖《阙里孔子庙诗》,清凌廷堪《学古诗》,中华民国时期毛泽东写的《祭母文》、挽易昌陶诗,余季豫先生写的《亡室陈恭人墓表》,杨遇夫先生《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等等。这些诗赋文章就是典范的礼文学之林中极小的一部分。
是战国荀卿、唐杜甫、北宋王禹偁诸贤启发了我们。既然可以说礼赋礼诗,扩而大之,为什么不可以说礼文学呢?
上个世纪中国结束所谓文化革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文艺理论家解放思想,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产生了一些新理念。他们说:文学既是无功利的,也是功利的;既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既是情感的,也是认识的。①童庆炳先生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65、67、69页。因此,这里可以说:我们所指的礼文学是功利的,但并不缺乏审美意义,除了反映礼俗礼制等内容之外,与一般的文学概念基本相同。
现在,中国礼文学这个概念或名称,总算第一次正式提出来了。
从来没有别的人提出过“礼文学”这个概念。我们心胸里藏有此概念已久,①《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曾言及“礼文学”(见《问丧》篇)。而今再次公诸学界。世人或不能无疑:有必要设立“礼文学”这个新名词吗?标新立异究竟为什么?近代现代众多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文学批评、中国美学的大学者,几乎没有不认为中国历代礼俗礼制与文学作品中人物情感互相对立的,哪里有什么礼文学?礼文学史又何从而来?
对于这些问题,请允许先作简单的答复如下:设立“礼文学”这个新概念很有必要,提出研究礼文学这个新课题是时候了。标新立异不为惊世骇俗,但为求真务实。众多学者一概否认礼与情的正常关系,断言礼与情完全对立,那是对礼制礼俗的误解。中国礼文学是文学史的客观存在,撰写一部《中国礼文学史》正是时候。以下试详论之。
一 历代礼文学众多作品的客观存在不容否认
拙著《中国礼制史》分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夏卷、元明清卷凡六卷,②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每一卷都不曾忘记以文学作品证礼,譬如以诗证礼,以赋证礼,以散文证礼。那些已经例举的诗、赋、散文,都是文史研究者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可以证明礼文学的客观存在。我们现在着手写的《中国礼文学史》,必将列举更多的文学作品并作出必要的分析,证明历代都有礼文学,证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里有一条分支确实是礼文学史,这条支流同样源远流长。
有不少文学史、美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忽视礼文学与礼文学史的存在。或者认为那些写到礼仪礼典的诗文算不上文学,或者以其为数不多而不予重视。但是,毕竟已有学者注意到中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中礼文学的分量,譬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关于《诗经》的介绍:
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不仅祭祀、燕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③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第65页。
这样讲,承认《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载体的“很大程度”,承认《诗经》不但有“直接反映”周代礼乐的诗歌,而且“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甚至承认“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难能可贵了。
然而就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而言,对礼文学作品与礼文学史视而不见的情况是严重的。不少研究者甚至一笔抹杀礼文学作品的意义,何足以向学界向世人显示学术之公?何足以显示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与近代文学的真实的全体的面貌?
如果承认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④沈凤笙文倬先生《菿闇文存·附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以及拙著《中国礼制史·绪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那就必须承认反映礼的礼文学作品的大量的客观存在。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二 长期以来存在的解读历代文学作品时发生的礼类错误应引起关注
早在古代的《诗经》学者,就有因礼制不明而产生误解的情况。譬如《诗·宾之初筵》第一章前八句写“初筵”,后六句写大射礼;第二章(“籥舞笙鼓”至“以奏尔时”)后六句由射礼向燕飨礼过渡;第三第四第五凡三章集中写燕飨礼。当代礼学大师沈文倬先生曾经指出:“其实,射礼在饮酒礼的怀抱中举行,不能单独成礼。”⑤见沈文倬先生撰《接近民间的乡礼》。该文先生生前未发表,但学生有幸反复读过手稿全篇。《礼经·乡射礼》《燕礼》《大射仪》证明沈先生的概括是完全正确的,《诗·宾之初筵》也证明射礼之前之后都是燕飨礼(包括饮酒礼)。《宾之初筵》第三章郑笺:“此复言‘初筵’者,既祭,王与族人燕之筵也。”孔疏:“此与上章虽古今不同,而相承为首尾。”后来马元伯《毛诗传笺通释》说:“前二章为陈古,举初筵以见宾之始终皆敬。此章以刺今,则举初筵以刺始敬终怠,非必有异礼也。”郑笺是对的。孔疏与马说皆非,只因为不知道射礼与饮酒礼的关系,所以强生古今之别,把本来联系紧密的前三章活生生地拉开了。北宋欧阳修、清代陈奂与方玉润亦不察,误同孔疏以及马元伯之说。⑥拙著《诗经刍议·说〈宾之初筵〉与〈行苇〉》(岳麓书社1997年版)。
拙撰《诗经校注》①岳麓书社2004年版。一书序言说过:“清代以前的治《诗》专家几乎没有不注重《诗》礼关系者。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个世纪的‘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及其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过分地批判、否定、践踏礼义之邦的礼制与礼学,以致文化大革命过后终于觉悟到传统礼学礼制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与学术研究(如《诗》学研究)的重要关系的时候,有志焉而力未逮也,不少学人竟感到困难,甚至无从措手。”这段话说到清代以前的治《诗》专家。上文提到的孔颖达、欧阳修、陈硕甫、马元伯诸位,皆清或清以前人,都是了不起的大学者,他们是懂得《诗》礼关系的,只是由于偶有不察而发生疏失。
让我们再举一个具体例证,《诗经》首篇《关雎》的解说,很能发人深醒。
上个世纪的“五四”运动以前的两千余年,说《关雎》者多追随《毛诗序》;后来则以判断为自由恋爱并结婚的意见居多。《毛诗序》的“后妃之德”说,固然是凭空揣测;后来的琴瑟钅童鼓迎娶淑女说,也只是捕风捉影罢了。我们不赞成这两种意见,因为大量的文献给了我们立论的根据,这就是婚礼不用乐的当时礼制,此制通行于东晋之前全社会,通行于中唐之前社会上层。②《诗经刍议》(岳麓书社1997年版)之《说〈关雎〉》一文。这就不容许我们的文学研究者、美学研究者驰骋形象思维尽想当然。
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选译》,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选》,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经今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经译注》,有关译注者都是著名专家,都把《关雎》结局说成结婚迎娶,美满得很,浪漫得很。上个世纪的1996年,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发表了如下意见:“《关雎》之中,有思慕淑女的缠绵哀感,有钅童鼓迎婚的愉快欢乐,表现得都恰如其份,真挚而和谐。”③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7页。又说:“……《关雎》一诗作为一篇客观存在的‘房中乐’,可以用于‘乡人’,也可以用于‘邦国’,甚至可以理解为这首诗之所以能产生,归根到底是由于‘文王大姒德化及民’的结果,但从这首诗的创作‘本意’、‘诗人始意’来看,它当是周邑民间流行的一首‘咏初昏’的歌曲。”④王运熙、顾易生主编、黄霖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前一说结局是“钅童鼓迎婚”;后一说用清人方玉润的意思,结局也归于结婚,确实让人感到“真挚而和谐”。后一说实际是《毛诗序》的说法和后来的迎婚说的结合,和谐是够和谐了,但是否“恰如其份”,是否真切可信,恐怕就难说了。
最近的例子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在《诗经》学界颇有影响的权威学者说《诗经》的书(《诗经讲座》),仍然将《关雎》说成迎娶新娘之诗。
大量的事实证明:礼文学作品是客观存在的,研究文学而忽视同样客观存在的礼制(或礼俗),那就很难避免胡乱的揣测以及错误的结论。学界有名望者尚且难免,何况粗涉学界的我辈普通百姓呢?
三 对礼与情的关系应该有恰当的理解与把握
人类社会生活中,诚然有礼制与人情互不相容的时候,譬如舍生成仁、捐躯报国与逃死尽孝、苟活养家,譬如白衣书生与相国门第的千金之间的婚姻,那确实难以通融并存。在这种情况下,舍生取义的原则就有必要坚持,克己复礼的决断就有必要考虑了。然而不应该怀疑:在大多数场合,礼制与人情应该可以统一,可以和谐,特别在同一阶级内部是如此。其实古人并不认为礼与人情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诗大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应该是社会各阶级内部、甚至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之间都可以遵循的言行准则。难道可以因为一时一己或少数人的感情冲动而违背阶级或民族、国家大义吗?《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是为国人所谓礼义之大者。
古人有一种说法:“礼本于人情,情生而礼随之。”⑤《礼经奥旨》,旧说为南宋郑樵所撰。出土文献记载了战国以前的古人更为明确的说法:“礼因人之情而为之。”⑥《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九四页。“情生于性。礼生于情。”⑦《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二》第二0三页。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的《性情论》说“礼作于情”,与“礼生于情”意同。意思是说感情从人的性格产生,礼则产生于感情。“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性自命出》)①《郭店楚墓竹简》第一七九页。《战国楚竹书(一)·性情论》有同样的话。这里所谓道与义,实即礼义,实即礼。就人类社会的始初阶段而言,上引楚竹书的说法是对的,只是不够完整罢了。我们认为:礼与情感都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实践。礼产生之后,对感情会产生配合与影响之外的作用。
在人类社会之初,人们为不同目的、不同需要而举行不同活动,同时产生不同的感情,渐次生出不同的礼典礼仪。人的感情产生于人类实践活动,人间诸礼与人的感情互相配合,互相影响。小戴辑《礼记·礼运》说: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这一段话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真理。试问:人类何时没有七情?所谓升平之世,难道不应该到处讲人义吗?今天建设和谐社会,难道不正是要除人患、兴人利吗?治人七情,现在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借鉴优秀传统文化提倡的公民基本道德,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靠什么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靠当时的礼以及当时从属于礼的法,别无他途。“舍礼何以治之?”如果《礼运》说的“七情十义”被指斥为“人性论”,“人利人患”被指责为违背阶级分析法,而“以礼治情”也被一概视为谬论,那一定在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不肯容忍和平与稳定,而“阶级斗争学说”盛行之时。
人生天地之间,礼是人类处理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活动。这环境就是天地,就是人类内部。礼是人们为自身目的处理人与天、地与他人(包括生者与死者)关系而求得和谐、安定与发展的过程与准则。感情必须适应这些过程,必须遵守相关准则;如果不适应,那就不能不以礼治之。关系各异,对象不同,人们付出的感情也不能不有区别,这就是所谓“情”况不一了。
古人对天、地与先人,不能不怀抱敬畏之情(由畏惧而生敬意),对活着的长辈与尊贵的统治者亦复如此。小戴辑《礼记·曲礼》郑注:“礼主于敬。”《说文》:“敬,肃也。从攴苟。”“苟……从勹口。勹口,犹慎言也。”又说:“肃,持事振敬也。”不错,礼是要求慎言,要求持事振敬。《曲礼》又说:“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注:“庄,敬也。”《音义》引郑云:“求福曰祷。”“求得曰祠。”按:《周官·小宗伯》注:“求福曰祷,得求曰祠。”《曲礼》孔疏引熊安生的话:“祭祀者,国家常礼。牲币之属,以供给鬼神,唯有礼乃能诚敬。”
其实,不仅仅祭祀之礼必须诚敬。难道朝觐可以不诚不敬?平时与师长相处,为长辈或者在上位者料理后事,难道可以不诚不敬?招待宾客又岂可不诚不敬?夫妻之间又何尝不可以相敬如宾呢?诚敬是处理任何关系的礼都不可缺少的。处于相同水准、相同环境的社会生活中的人类必有相同的情感,因而产生表达相同情感的礼,这不是反对阶级分析法的人性论,不是唯心论,而正是唯物论。《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宾客之礼必有夫齐齐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齐齐之敬,居丧必有夫恋恋之哀。”②《郭店楚墓竹简》第一八一页。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性情论》有同样的说法。③《战国楚竹书(一)》第262页。但《性情论》整理者谓居丧之哀“累累”然。以图版字形而论,窃以为释作“恋恋”较妥。小戴辑《礼记·少仪》:“宾客主恭,祭祀主敬,丧事主哀,会同主诩。”这样说,当然是普天之下认同的正常情况。难道礼与情不应该这样结合吗?
上世纪被大加挞伐的古礼,依其激烈程度而言,大致有四。一是祭祀,统统斥之为封建迷信,一概废除。二是丧服制度,基本上也废除了。三是朝觐跪拜,全国全社会看不到了。四是古代婚姻制度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寡妇不再嫁”诸项。我们认为由上个世纪“五四”运动激发的与这四个方面相应的对古礼进行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对的,都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伟大胜利。但是祭祀,三年丧服,朝觐跪拜,婚姻而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寡妇不再嫁”,确实是古代古人的礼制,这是不可也不必否认的,何况古代古人自有其当时的道理,自有其当时的思想基础。
上世纪“五四”运动前后的先进知识界批判中国传统礼教为吃人的制度,多举古代婚姻制度为例,多以古代婚姻情为礼所制所困为缘由。其实早有古人为传统婚姻制度做出必要的适当的辩护。譬如不少学者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礼教思想的金圣叹(1608—1661)就说过:
夫才子之爱佳人则爱,而才子之爱先王则又爱者,是乃才子之所以为才子;佳人之爱才子则爱,而佳人之畏礼则又畏者,是乃佳人之所以为佳人也。是故男必有室,女必有家,此亦古今之大常,如可以无讳者也。然而虽有才子佳人,必听之于父母,必先之以媒妁,枣栗段脩,敬以将之;乡党僚友,酒以告之。非是,则父母国人先贱之;非是,则孝子慈孙终羞之。何则?徒恶其无礼也。(《西厢记·琴心》总批)
同样具有反封建观念的王锺麒(1880—1913)著《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说:
夫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人之情也,然一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执路人而强之合,冯敬通之所悲,刘孝标之所痛,因是之故,而后帷薄间其流弊乃不可胜言。识者忧之,于是构成小说,言男女私相慕悦,或因才而生情,或缘色而起慕,一言之诚,之死不二,片夕之契,终生靡他。其成者则享富贵长孙子,其不成者则併命相殉,无所于悔。吾国小说以此类为最夥。老师宿儒或以越礼呵之,然其心无非欲维风俗而归诸正,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焉已耳。
《礼记·礼运》早就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古人从来不否认男女之情,而所谓老师宿儒不赞成私奔野合,而要求“听之于父母,先之以媒妁”,其中含有尊重男女双方而维系风俗之正的意思,未必就是扼杀青春,未必就是礼教吃人。后世社会主张性开放以试婚同居为快乐者,固然张扬了情爱与青春,但若彼此不负责任,到头来恐难免上演一幕又一幕悲剧。可见所谓情为礼所制所困,未必统统是坏事。当然,最好的婚姻制度应该是男女自主恋爱、自愿结婚,一如现在的婚姻法的规定。
然而古代礼制中真有坏东西。譬如不许寡妇再嫁,甚至不许订婚后男人早死的少女另择丈夫,这可真是戕贼青春,无端地扼杀自由与幸福而毫无道理!赵宋理学家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实在是他们的理(礼)论的严重失误,招致后世学人与思想家的严厉批判,毫不足怪。
今按:古代礼籍对礼与情的关系曾有不少直接的议论,兹从小戴辑《礼记》选择相关五条评说之,以便从中领会先贤所把握的情与礼之关系的实质:
(1)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檀弓下》)
(2)君子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熟。是故君子之于礼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礼器》)
(3)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祭统》)
(4)故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问丧》)
(5)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运》)
关于第(1)条,孔疏:“微,杀也。言若贤者丧亲,必致灭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数,以杀其内情,使之俯就也。”引何胤云:“哭踊之情必发于内谓之微。微者不见也。”孔疏又说“‘有以故兴物者’:兴,起也;物谓衰绖也。若不肖之属,本无哀情,故为衰绖,使其睹服思哀,起情企及也。”看《檀弓》本文,“戎狄之道”与“礼道”分明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孔疏认为戎狄之道“谓直肆己情而径行之也,无哭踊节制”,又说:“陶者郁陶。郁陶者,心初悦而未畅之意也……郁陶情转畅,故口歌咏之也……犹者,摇动身也。咏歌不足,渐至自摇动身体也……摇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扬,乐之极也……愠,怒也……叹,吟息也。愤恚转深,故因发吟息也……辟,抚心也。叹息不泄,故至抚心也。抚心不泄,乃至跳踊奋击,亦哀之极也。”自“人喜则斯陶”句以下,到“辟斯踊”句,说的都是人情及其表现。从“初悦”到“乐之极”,怒而叹息到“哀之极”,表现够充分了。“品节斯”句以下郑注:“舞踊皆有节,乃成礼。”孔疏:“品,阶格也。节,制断也。斯,此也。”元代陈澔(云庄先生)《礼记集说》用郑注孔疏说。《檀弓》这一段话值得注意的主要是:行礼,有时候是要杀情的。适当地节制感情,才是礼道。若是把“微情”理解为不让感情太露太张扬,亦通。譬如《檀弓下》又说:“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没有比丧礼更让人悲哀的了,可是这时若是根本不节哀,一直哀戚下去,倒反而不合礼了,反而成戎狄之道了。这里“戎狄之道”与“礼道”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品节感情。与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情况比较,这里所谓戎狄之道应该还要算是文明的行为。
第(2)条提出了礼学礼制的一个重要观点:“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郑注:“近人情者亵,而远之者敬。……血,腥,爓,熟,远近备古今也。尊者先远,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作,起也。敬,非己情也,所以下彼。”孔疏:“礼之近人情者,谓若‘一献孰’,饮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啗,最近人情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极也。”用现代汉语说得更明白一点,这个观点意思是:近人情的礼不是表达最敬意的礼。换句话说:最隆重的典礼不必最近人情。这也就是说:“礼主于敬”,不主于人情。礼学礼制看重的“情”,与世人看重的“情”未必完全一致。
第(3)(4)两条告诉我们:礼学礼制决不束缚,更不反对真情,而是看重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纯情。行祭祀之礼固如此;痛哭刚刚去世的亲人,为刚去世的亲人服丧,也是如此。这两条重要的是反对虚情假意的行礼。古人之于祭祀与服丧,都是认真的,对神灵的恭敬是纯朴而诚恳的,对先人的思念是真挚而深情的。当然,这与前面第(1)条,与后面的第(5)条并不矛盾。
第(5)条引孔圣的话,强调承天道以治人情的重要性,而这就是礼。须知治人情与第(1)条说的节制感情并不完全相同,治者包括治无情者在内,而“品节斯”只是治人情的一个项目,只是节制过分者罢了。小戴辑《礼记·曲礼》说:“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唯禽兽纵情肆欲,无礼而不知节制。由此可见礼制(礼节)是何等重要!若无礼节礼教,人与禽兽无别,还有什么文明可言!
音乐也是表现感情的。《乐记》说:“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又说:“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拙著《中国礼制史·先秦卷·绪论》曾经论说过礼乐关系,认为礼是乐之主导,礼典中用乐即行礼。这《乐记》说礼以著诚去伪为经,礼乐管乎人情,很对。
礼与情之间还有一层关系。礼是必须实践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情则产生于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礼是人类社会实践与生活经验的升华,反过来又是社会实践与生活价值取向的规范,当然会指导或约束情感的表现方式及其程度。情感可以在礼的实践中培养并趋于纯正,而前文引《檀弓》说的“以故兴物”,引孔疏言及的“起情企及”(譬如“睹服思哀”),当然也就很有可能发生了。清嘉道咸同年间在世的何子贞(1799—1873)《与汪菊士论诗》云:
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物,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时时培护,字字持守,不为外物摇夺,久之,则真性情方才固结到身心上,即一言语一文字,这个真性情时刻流露出来。
此公所谓“孝弟忠信大节”,“日用起居及外间应物”,不就是礼义之邦的礼吗?这礼还真是平平实实的!在“平平实实”的礼的实践中“自家体贴得真性情”,就有了做诗人的必备条件,他做的诗就有感动人的真性情。创作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应该也是这样。
只要对礼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礼与情的关系有恰当的理解与把握,就不会怀疑甚至否认礼文学与礼文学史的客观存在。只要对礼义之邦的悠久的礼制与礼学传统有正确的认识与深入的钻研,又认识到学界以往误解文学作品反映的礼制所发生的问题的严重性,就会觉得提出“礼文学、”“礼文学史”的概念与研究课题是合理而且必要的。拙著《中国礼制史》已经正式出版十年,现在开始董理中国礼文学史的条绪,正是时候。
四 对礼文学的解说必须求真务实
我们说的《中国礼文学史》,撰作至今已经快六年了。该书一直并且还将继续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对礼文学作品创作背景、作者、作品主旨以及主要内容的解说一概求真务实。唯有与礼制精神、礼典实际或礼仪过程相合并且具备相当的文学性者,始许其为礼文学。与中华礼义之邦的礼制礼仪礼义无关或者根本相违者,可视为礼之外的文字;虽然与礼制礼仪礼义有关,但质木无文因而读之味同嚼蜡者,亦不许其为礼文学。耐读的好诗文,不必尽属于礼文学;然而在“人”的意义被真正认识之后,在“人民”登上历史舞台之后,那些违背礼的精神的作品,则可以肯定不是好作品。
根据上述原则,《诗经·关雎》《楚辞·橘颂》并非礼文学,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它们与包括昏礼冠礼在内的礼制礼典礼仪无关。这里容不得指鹿为马,容不得想当然。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祭母文》,可以说是礼义之邦标准的出色的动人的礼文学,但他所谓“焚坑事业要商量”、“孔学名高实秕糠”之类的大作,我们就不敢恭维了。同样,我们也不会说朱熹作的《家礼》是礼文学,因为它实际上不是文学作品。
由于有关各方的支持,我们的《中国礼文学史》即将问世。虔诚地期待着学界的批评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