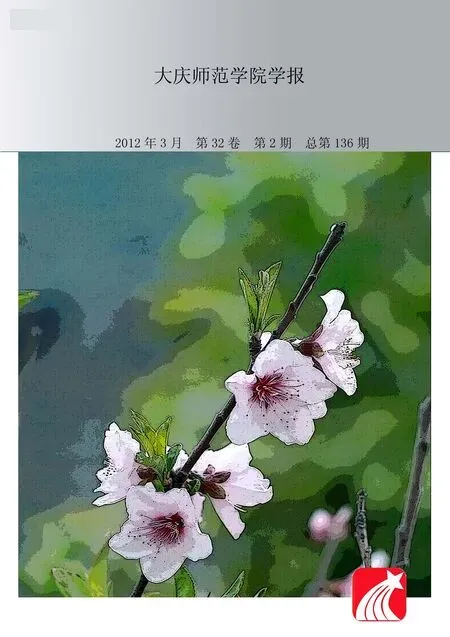试论小说中的话语信息差
——以《像我这样一个女子》为例
2012-04-02谢建娘
谢建娘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修辞行为是一种具有意识性和目的性的社会行为,发挥言语在各种交际领域的作用,恰当地表现发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使受话人接收,达到互相沟通思想感情的目的。修辞行为的这一人际功能,是通过话语输出和话语接受而实现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修辞行为的这一人际功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话语输出(信息发送)与话语接受(信息接收)常常会出现不等值现象,由此产生了话语信息差。本文就西西的小说《像我这样一个女子》谈谈话语信息差产生的原因和审美价值。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的。”小说以这样一个近乎绝对的——“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语气开始,给人以强烈的好奇心。“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怎样一个女子呢?小说接下去写明:“我长时期的工作,一直是在为一些沉睡了的死者化妆。”而对于这个“真实”的职业,作为“我”的男朋友——夏(简称),是不知道的(我们这里暂且这样认为,并且实际上“我”也认为夏不知道“我”的真实职业),由此,“我”在碍于这一特殊工作时与夏产生了这样两段对话:
当我和夏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很久了,所以当夏问我是在做事吗?我就说我已经出外工作许多年了。
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问。
替人化妆。
我说。
啊,是化妆。
他说。
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
他说。
我可以参观你的工作吗?
夏问。
应该没有问题。
她们会介意吗?
他问。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介意的。
我说。
从这两段“我”与夏的对话和小说主人公“我”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和夏实际上产生了话语信息差。在“我”认为,“夏就像我曾经有过其他的每一个朋友一般直接地误解了我的意思,在他的想象中,我的工作是一种为了美化一般女子的容貌的工作,譬如,在婚礼的节日上,为将出嫁的新娘端丽她们的颜面”,而实际上“我”所说的“化妆”是指在殡仪馆替死人化妆。通过第一段的对话,如果说没有后面作者的自解,我们也很难发现夏和“我”之间的对话存在着信息差。在第二段对话中,当夏问“她们会介意吗?”时,“我”的回答是“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介意的。”在夏的理解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介意的”指的是“她们”不会反对他去参观工作,而“我”的真实的意思则是:他们都是死了的人,死了的人是不会说话的,更不会介意的。
以上两段话,不论是从文本表面,还是从“我”的观点来看,一直是夏在“误解”“我”的话语信息,而“我”也始终带着这种“误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有意使“我”的话语带有“被误解的性质”来进行上面两段对话的。然而,我们想想,夏难道真的不知道“我”的真实工作吗?祝敏青的《小说辞章学》指出信息差形成的其中一个因素是:“言语代码具有‘言外之意’,解码者只接收了表面的理性信息,未能接收潜在信息。”从小说中的两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我”实际上一直充当着一种自认为的“编码者”形象,在“我”认为,“我”所发送的信息,夏始终未能真正地接收,并且读者若跟着“我”的想法走,也会认为夏一直是在“误解”“我”的话。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到作品中,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不然。小说中话语信息差的产生还有另一些原因:编码者所发送的信息被解码者准确地接收了,然而,解码者对编码者所发送信息的反馈未能被编码者准确真正地接收。这种信息差的产生,可以看做是解码者说话的一种技巧,或者说是解码者的有意而为之。小说中的夏,在“我”(编码者)所认为的他未能准确接收“我”的话语信息时,或许是准确地接收了“我”的话语信息了。
从叙述学的观点来说小说始终以“自知观点”,即通过小说主人公的口叙述出来的。这位忧郁的女子独坐在咖啡店幽暗的角落里,用忧郁而又平静的语调告诉读者她如何与夏相识、相爱,告诉读者她正等待夏的到来,今天她要带夏去看她工作的地方,向夏公开自己的职业,还告诉读者夏在知道她的职业是给死人化妆而不是给新娘化妆之后会大吃一惊,失魂落魄地逃走……所有这一切的叙述以及上面我们提到的两段对话,都是建立在“我”的角度,然而,我们应该明白,“我”仅仅是爱情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对自己的爱情故事的叙述就很可能是主观的、片面的。“我”之所以会认为夏是在误解“我”的话语是基于到目前为止夏一直把“我”所谓“化妆”理解为给新娘化妆这个前提,但这个前提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这里我们可以大胆作一个假定:夏其实早知道恋人是在给什么人化妆,因为恋人常常穿素白的衣服,因为恋人说自己的职业是“替人化妆”的时候他说“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因为闻到恋人身上那股特殊的气味儿(防腐剂的味道)的时候说“你用的是多么奇特的香水”。只是他懂得女性的脆弱,理解恋人近于自卑的忧郁,不愿贸然将话题点破给她造成窘迫而已。
“在他的想象中,我的工作是一种为了美化一般女子的容貌的工作。”这里所谓的“他的想象”与其说是一种事实,还不如说是“我”的想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的一种“逻辑预设”——“夏就像我曾经有过其他的每一个朋友一般直接地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曾经的碰壁,“我”的自卑,使“我”从日常生活中推导出一种逻辑,“我”自认为正确的逻辑——夏不知道“我”的真实职业。
小说中“我”与夏的话语信息差之所以会产生是双方的心理差异造成的。人的心理都是各不相同的,没有哪两个人的心理是完全一致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相对的,一个人能百分百地把握对方的心理是不可能的。有人说“理解万岁”,然而绝对理解是不可能的,所以“万岁”也是不可能的。王希杰认为:“交际的目的在于人际之间——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而沟通和理解就要求减少‘信息差’。交际的双方都力求减少和消灭信息差,然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困难,几乎办不到。”减少双方的心理差异,是取得良好交际效果的保证。而小说中的人物恰恰是利用双方存在的这种心理差异,造成信息差,以期达到各自的话语目的。小说中的“我”是自卑的,以“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的”的绝对观念来否定自我,否定自我的职业,正是基于这种自卑,“我”期望用“话语拯救”来实现“现实拯救”,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珍贵爱情,一句模糊的“替人化妆”掩盖了话语的真实性。然而,“我”又是勇敢的,明白语言拯救并非现实拯救,话语的“被误解性质”——“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介意的”。实际上是用话语的拯救来达到对现实的破坏:“我知道命运已经把我带向起步的白线面前,而这注定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在一间小小的咖啡室等夏来。然后我们一起到我工作的地方去。到了那个地方,一切就会明白。”夏对于“我”回答的反映,“但你的脸上是那么朴素”,是夏的一种引导恋人谈论自己的职业的谈话技巧,夏是以期通过语言拯救来达到现实拯救。可以说,夏是勇敢的,在面对与恋人谈话时,是能够理解恋人内心的。“我”的自卑,“我”的对于过去——“我的诚实使我失去几乎所有的朋友,是我使他们害怕了”的恐惧和夏的“谈话技巧”,使得两人彼此无法真正的接收对方的话语信息。
交际双方缺乏共知信息也是形成小说话语信息差的一个原因。小说中夏不知道(这里我们就以小说主人公“我”的看法来理解)“我”的职业是替人化妆,才会说“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不知道“我”的“朴素”是因为职业原因,才会说“他喜欢朴素的脸”;不知道“我”的真实职业,才会说要参观“我”的工作地方……才会对“我”的话语一直存在误解。而“我”作为编码者的同时,对于解码者(夏)的信息反馈的接收,只接收了理性信息,未能接收潜在信息,也使话语双方产生了信息差,所以才会有“我”的自认为夏不知道“我”的真实职业的固执坚持,才会有“命运已经把我带向起步的白线前面”的结论。可以说,小说中“我”和夏之所以会产生信息差(双方的),其实是交际双方有意造成的。“我”为了挽救爱情而含糊其词,夏懂得恋人的脆弱和自卑而使用了委婉的谈话技巧,使得双方都未能真正理解对方的内心。
也正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两段话语信息差,才会有“我”的“坐在咖啡室的一角等夏”,才会有“我”在等的过程中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才会有“我”的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将来的假想。两段话语信息差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两段话语信息差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夏和“我”到了“我”的工作地方,是正如“我”所想的——夏不知道“我”的真实职业,当明白“我”的真实职业后,便失魂落魄地逃跑了,还是……
[参考文献]
[1] 祝敏青.小说辞章学[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2] 谭学纯.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3] 宗守云.功能修辞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