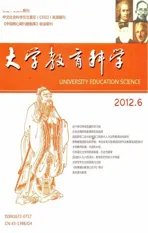校长筹资与大学权益诉求——以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
2012-04-02薛国瑞商丽浩
□ 薛国瑞 商丽浩
引言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复辟闹剧惨淡收场后,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北京大学的身份使其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作为国立大学,它拥有校长及教师等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足以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以避免军人政治之侵扰;但另一方面却因其经济问题——无法获得“自给自足”的经费,而不得不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致使其无法完全挣脱国家权力的统制。因而,在“军人干政”、中央财政不断被侵蚀、教育事业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北京大学的领导者处于寻求经费支持与谋求独立发展的双重困境中,诚如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言,“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尔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1]。由此,本文考察1920-1927年间北京大学校长的筹资问题,以期对其时大学校长在利用自身独特条件及摆脱科层控制的过程中如何谋求大学自主发展等问题有进一步认识。
一、“自力救济”的尝试:校长向社会募资
一所大学的成功往往与其校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校长在推行其教育理念时则须有经费的支撑。1919年8月9日,蔡元培回京执掌北京大学。他强调,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生应“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并提出北大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2](P245)。为此,蔡元培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研究院”两方面入手,着力提高北京大学的研究水平。
可是,“五四”之后的国内局势较为混乱,各路军阀忙于内战,国家预算多用作军费。“据统计,这时北京政府的预算仅军费一项就占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百分之一·二”[3],拨付给北京大学的教育经费也更加短缺。1934年蒋梦麟在准备旅欧参观教育时回忆道:“北大经费在民八以前,北京国立各大学教育经费每月十六七万时,北大每月经费为六万元。俟民八以后,各大学经费增至念二万,北大经费亦增至七万二千,以后北平各大学增至三十六万,北大经费未再增加”[4]。“七万二”这个数目直至1924年仍未变更。而且,北京政府常以国库支绌为由不照预算发付。教师的工资也常常被拖欠,加之工资的70-80%以纸币支付,“这些纸币常常由于不能兑换而变得一文不值”[5]。
蔡元培深知,此时张作霖、曹锟等对他这个校长及北京大学深为不满,必然要在经费供给上增设各种限制。为此,他决定培植北大“自力救济”的能力,着手转变当下完全依赖政府的筹资方式,寻求社会团体的资助。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为发展北京大学科学研究事业筹集经费,他遍访欧美,参观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及大学,与各地教育相关官员及大学校长交流,沟通大学发展思路及经费事宜。1921年蔡元培赴美考察教育,在“经过纽约、费律特尔(Philadelphia)、波士顿、支加哥、温哥华”提及为北大图书馆募资时,华侨们“郡[都]极赞助”[2](P420-422)。蔡元培对此深受感动,并认为,北大“非政府立的(Government),乃国立的(National),为何只向政府商量,而置全国人于不顾耶!”[6](P361-362)。
校长新的筹款思路在提升北大“自力救济”能力上的效果逐步显现。其中,图书馆事业首先取得明显效果。1920-1922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平均每年增数都达万余册。而关于图书馆建设经费筹集数额,据考,1922年7月8日罗家伦纽约来函中介绍了美东募捐情况:“五月十四日晚间,在中华公所,由两梅君[廷献及纽约安良工商会会长梅宗尧]及同学会雷国能君演说,当场认定美金一千九百元,……次日分头捐得者又一千余元,……现在期望于纽约者在美金一万元以上”[2](P538)。可惜的是,此时,由于政府积欠北大巨量经费,北大债务累累,图书馆建设最终搁浅[7](P59)。
图书馆事业艰难开展的同时,发展“研究院”事业也在推进。1921年12月,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以下称《大纲》)。《大纲》中提出了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特建立研究所作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业学术之所。研究所计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同时还决定设立奖学金若干名,鼓励研究生专心研究学问[8]。但是,极度穷乏的北京政府对于北大“现在固有之教育经费,尚不可靠”,更难以另投经费支持北大研究事业。于是,蔡元培将希望寄托于各国庚子赔款退还后“每年拨给北京大学研究所补助经费若干元。以为搜集材料,培养人材,延聘学者,建筑房屋之用”[9]。可急于发展北大研究所的校长在还未得到庚子赔款退还的消息之前便依靠着北大内部教师的支持于1921年11月开办了唯一的研究所——国学门①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其中规定,研究所组织暂分四门:国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称谓开始逐渐被采用。参见:郭建荣.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变迁(上)[J].文史知识,1999(04):114-119。。
1923年1月,蒋梦麟代理校长之职,北大教育经费此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他对于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仍是竭尽全力。蒋梦麟指出,当经费有着落时,“拟将经费划出一部分用在充实学术上的内容。购买图书要注重专门,请各系计划应购的书报杂志。这层做到,学术自能渐渐提高”[7](P60)。1924年9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成立,蒋梦麟担任中方董事之一。针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促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宗旨,蒋梦麟于1924年组织成立了教育学系和东方文学系,1925年又成立了生物学系等,以此寻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
在政府投资缩减的情况下,校长们筹资观念的转变,似可看作是对学校归属的重新定性,但这显然也是“求告”政府“无门”的无奈之言。“国立”大学的筹办与发展确应与国人相商,只是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承担其发展的经费也是理所当然。若将此责任重新归入国人所承担之范围,那么政府责任又将归于何处?可以说,大学在寻求其独立性的过程中始终无法规避其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这不仅仅表现在经费依赖方面,还有传统中国“政教合一”思想下潜藏的“教育从属于政治”的深刻影响。因而,校长的筹资努力虽推动了北京大学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却始终无法摆脱国家权力的掌控,承受着政治与教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
二、科层内权益的诉求:校长上呈文与辞职
筹资渠道的扩展并未彻底改变北京大学对政府的依附性。北京大学虽可在图书、实验仪器等方面获得资助,却难以筹到足额经费维持大学的日常运作。为了争取政府对大学的切实资助,处于科层体制中较为弱势的北大校长决定联合京师其他学校校长,力图凭借群体的力量以获得体制内的保障。
(一)校长上呈文
1922年春,北京政府已积欠北京大学及京师其他国立七校经费达两个月。为确保教育经费的正常供给,北大校长及其他七校校长与北京政府展开了不懈的抗争。就在这年2月至11月的十个月内,8位校长向北京政府上呈文逾30次[6](P526-813)。其中涉及教育经费呈文数21次,递交辞呈5次。据史料统计显示,因教育经费问题呈文21次,是1919-1927年间所上呈文次数最为频繁的时期,且呈文内容与对象等又都不尽相同,基本上囊括了北京大学校长前后几年涉及的主要经费筹措问题。同时,这一年反反复复的呈文也极具代表性地展现了以北京大学校长为首的校长群体在学校经费问题上从试图影响国家权力到与其对立抗争的整个过程。
第一,扩充学校教育经费,设立教育基金。如向大总统、国务总理和教育总长三方面呈请将德国、法国等庚子赔款作为教育基金。而后因未得到回复,对政府愈加不信任,便于1922年2月6日,又请求参与法国赔款委员会,监督庚款分配情况。这其中,校长对于保障教育经费的权益诉求已经显现。大学校长把大学认定为国家行政团体之一,试图将掌管教育的权力平行植入国家权力之中,为获得教育经费的配置权寻求合法基础。
第二,借助权力,保障教育经费按时拨付。校长们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试图借助上位的国家权力干预下位的国家权力。如1922年3月4日和3月6日,在呈请教育部拨付经费无效时,则以期通过大总统、国务总理更为上层的权威力量明令教育部拨付经费。其中在呈文的措辞上也从“请拨发”变为“请从速拨发”,以强调其紧迫感。同时,也正由于教育部存在截留经费抑或是无法为其筹集经费的现实,各大学校长在对其无能为力的情形下,为不受教育部之管辖,开始不断呼吁废除教育部。校长们这种要求对大学进行独立管理的愿望是其对教育部科层制度的一种反抗,也是其参与国家权力遭到无视而做出的回应。
第三,保证教育经费来源之稳定及长久。如呈请抽调关税、盐税等中央财政固定收入。1922年6月2日,交通部、财政部相互推诿导致经费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时,便开始呈请大总统、国务总理解决学校经费之长久办法,要求请关税值百抽五以及海盐税等以为供给。这是校长们最无奈之办法,同时也是对国家权力的最大挑战。其重点便在于政府国家权力未能践行宪法,校长也鉴于此而据理力争,意图通过宪法影响政府对固定收入的分配。可是,近代中国的军人政治环境下讲求实力强弱对比,校长群体根本无实质意义上的强制性力量,只有依靠宪法来约束政府。然此时的军阀政府早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凌驾于宪法之上,处于弱势的大学校长也无能为力。
(二)校长辞职
大学校长试图影响国家权力的努力终究力不从心,学校经费也依旧支绌不堪。在此情形下,辞职成为其摆脱科层控制及孤立国家权力的近乎唯一的“武器”。据笔者所查,京师校长辞职现象在民国教育界中极其普遍,尤以二十年代前期较为突出。1921年和1922年校长辞职达11人次,而因积欠经费,无法维持学校而辞职的数量达14人次①根据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王学珍.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等统计。。从如此高比例的辞职中可以反映出大学校长摆脱科层的努力。“中央政府未能按法定要求承担起教育职责”[10],而校长们也“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拥有着“合法性”,也只能被政府设计为充当重视教育的“门面”。政府对于校长屡次辞职不批准,一方面利用校长威望尽最大限度的筹集资金以维持教育;另一方面,如果学校因经费而无法维持,校长辞职未准而离校,便可以将“停顿教育的罪名”安到他们的头上。虽然,在每次校长以辞职作为抗争政府的最后手段时,总还能得到部分经费以维持学校运作。可是,校长又怎会不厌倦这种屡屡请辞不准、四处筹集经费的工作?他们期待着教育经费得到持续稳定的保障,除却后顾之忧而专心发展大学教育。遗憾的是,美好的愿望终究取代不了残酷的现实。在军阀混战中,政府官员中多数无心发展教育,而是借用职务之便大肆搜刮钱财,或攀附军阀寻求升职。校长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被认为是独立的,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更没有参与旨在统治国家的军事斗争。”他们“没有统治中国的野心”,也“没有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而“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国的福利,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的”[11]。正因此,军阀和政府才让他们担任诸如教育事业的领袖,一方面迎合这些人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其统治营造出一个重视教育的好名声。而当校长们开始要求进行国家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以维持教育时,这对于军阀和政府来说便已构成一种威胁,在经费问题上的再三推诿与积欠也就自然发生了。
三、校内外群体的响应:教师、学生与舆论
为配合校长在筹资中与政府的抗争,1921年3月,欠薪已逾四个月的教职员们决定联合起来争取教育经费。12日,北大教职员会率先议决:“自3月14日起暂行停止职务,要求政府于直辖铁路收入项下,拨付教职员积欠薪俸及国立六校常年经费”[12](P84)。15日,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会召开,各代表讨论后一致决定,“组织一永久的联合机关”,成立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与政府进行直接沟通。教职员联席会的成立,显示着大学教师权利维护的行为获得了广泛认可,构成了具有丰富社会资源作为支撑的社会力量。随着这种群体性的组织运动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校长的独特的权力行使方式。
第一,以个体公民权为法理依据的停职、罢工。与各校校长们纷纷以辞职的行为争取政府拨付经费这一方式不同的是,教职员们为教学工作的一线人员,如果他们停职罢工必然导致教育事业的瘫痪。所以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以挽救这种局面。1921年3月30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致函教育总长范源廉及教育部,要求切实筹定及指拨教育经费。次日,国务总理作出批示,教育经费自本月起,按月准25万元。至积欠60万元,由财政部设法清还[12](P84)。但到4月时仍未见到政府有切实行动,这种欺骗性的政令产生的平静转瞬即逝,教职员对政府的信任也跌至低谷。
第二,教职员联席会寻求学生支援,这是群体性权力向学生群体的蔓延。1921年4月10日,因教职员对政府诉求无果表示失望,各校教职员代表在美术学院召开联席会并议决,各校经费极度困窘,教职员不得已全体辞职。这一举动立即得到了学生的声援,当然这也是基于教职员联席会主席与“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连系”。12日,北京国立八校全体学生上总理呈文:“请三日内指定的款,克日上课恢复原状。如果政府认为教育不必维持,或不能维持,则请即日颁布明令,解散各校”[12](P85)。教职员与学生的联合,在京师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年6月3日下午,各校教职员及学生齐赴新华门请见总统总理,处于明显弱势的教职员及学生拿着他们合法的诉求和道德以期能“感化”政府,结果遭到无情打压,这就是“六·三事件”[14](P2847)。所以,作为群体性抗争的索薪运动只是一种弱势群体的强力爆发,而作为政府,出于政治道德的考虑对教职员进行种种敷衍、妥协,但却始终表现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漠视。
第三,在教职员及学生实质性的行动遭到了残忍镇压后,教职员联席会开始发动社会舆论界寻求帮助。首先,“通电全国”,联合社会各界——成为了教职员及学生群体对于力量诉求最深处的呼唤。1921年“六·三”事件之后,北京教职员联席会及学生联合会借助“上海时事新报、申报”等向全国各地通电,告之详情。各大报纸的纷纷介入,在教职员索薪运动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其次,他们还通过报馆转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江苏教育会、各省教育会、各学校、商会、省议会”等团体并要求声援。北京教育会也向全国各省区教育会发电召开全国教育联合会,商讨教育经费问题[14](P2879-2883)。至此,全国的教育团体及舆论力量得以融合。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政府被迫选择了妥协,正如马叙伦所言:“当时的政府当局还晓得老夫子不好过于得罪的,对于我们的要求,三件敷衍两件,我们也将就了事,总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13]。
在与政府的“拉锯战”中,教职员的抗争性质只停留在维护合法权益的界线上。虽对政府丧失信心,教育事业仍有教职员自觉维持。1922年5月,北大教职员“以经费无着,而又不愿罢课,但个人之生计又不能不虑及,特主张互相扶助,筹款五千元。司月薪在百元上者,得借二十元,百元下者得借十元。如家中有急学生,无论月薪如何,皆将借二十元或四十元”[9](P2852)。教职员们仍依靠教职员联席会与校长们继续着与政府之间的斗争。
四、结语
1920-1927年间的中国陷入了一种丧失“绝对权威”的混乱局面。由于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足以使其从内心折服”的政治力量统摄,各路军阀进行着战国式的分裂和争夺。处此情形下,大学校长为谋求大学独立的发展权利,只能在寻求社会资助与摆脱科层控制的夹层中寻求一个较为稳妥的办法。他们通过上呈文与辞职的方式,并在群体力量的影响下试图对军阀掌握国家权力构成合法性危机。实际上,这种合法性危机并未对当时政府形成足够强大的威慑力。故此,在这段时期,校长或被利用,或被无视,虽因其社会影响力得到部分经费以维持北京大学的运转,但终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
可以说,1920-1927年间大学校长筹资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凸显了民国时期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中无力的一面。主要问题在于,社会的各种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人们的一直行动才能改变它,然而在民国这一波诡云谲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参与改革的一个个人,他们的期望也可以各不相同”[14]。正因此蔡元培才着力强调,教育独立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各个学校的教育经费也皆由该区中“抽税充用”[6](P585-587)。然而,无奈的是,法律在难以转化为抗衡国家权力的有力武器的情况下显得无力,教育独立也只是这种情形下的制度空想,大学权益的诉求只好依靠旧式的人事关系和大学校长及教师群体的抗争蹒跚前行。
[1]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137-138.
[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3]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67-268.
[4]蒋梦麟将赴欧参观教育[N].申报,1934-07-13(4):14.
[5][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376-377.
[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7]郑小花.行走于风雨飘摇的年代——记上世纪30年代北大校长蒋梦麟[J].高教观察,2006(09):59-60.
[8]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48.
[9]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1.
[11]顾维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7.
[12]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67.
[14]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