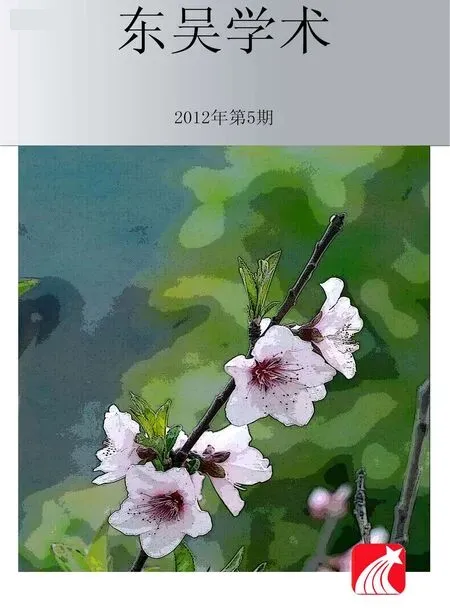译与讹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2012-04-02依兰斯塔文斯
〔美〕依兰·斯塔文斯 著 林 源 译
东吴讲堂
译与讹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美〕依兰·斯塔文斯 著 林 源 译
主持人 傅大友 丁晓原
林建法(《东吴学术》执行主编):今天是我们东吴讲堂的第二十五讲,非常荣幸地请来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安姆赫斯特学院的资深教授依兰·斯塔文斯,大家欢迎。
依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一九六一年出生在墨西哥一个中产犹太家庭,父亲是墨西哥的著名话剧演员,母亲是教师。他在欧洲、拉美、中东都有过生活经历,一九八五年迁居美国。对上述经历,他在自传《借来的文字》(On Borrowed Words)里有所描述。此前他还在犹太技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二〇〇一至二〇〇六年,他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主持节目 “与依兰·斯塔文斯对话”,颇受好评。
斯塔文斯教授以研究语言与文化著称,撰有《编字典的年月》(Dictionary Days)。他的著述涉猎广泛,有学术专著 《西班牙语环境》(The Hispanic Condition),《拉丁美洲人的USA:漫画史》等。他还编辑过几部文选,如《牛津犹太小说选》。他本人的作品集二〇〇〇年出版,取名《依兰·斯塔文斯精选集》(The Essential Ilan Stavans)。二〇〇四年聂鲁达百年诞辰之际,他编辑出版了 《帕布罗·聂鲁达的诗》(The Poetry of Pablo Neruda),全集一千页。他应美国图书馆之邀,编辑三卷本 《艾萨克·辛格小说选》(Issac:Collected Stories Singer)。
此外,他对大众文化也很感兴趣,撰文多篇,思想新颖,文字有力。
一九九三年以来,他被马萨诸塞州的安姆赫斯特学院聘为拉丁美洲和拉丁文化系的教授。这所大学是美国著名的文科大学,走出过一位总统,四位副总统,数十名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的学生。学校虽然不大,但有百分之六十的校友为母校捐款,在美国也不多见。斯塔文斯曾获得拉丁文学奖,智利的总统勋章和鲁文·达里奥特别贡献奖。
斯塔文斯教授在语言方面造诣极高。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少年在学校读书用的是意第绪语,一般写作用英语,而且还能读希伯来语,语言特长是他的依托,所以他从事文化文学研究,总能发他人所未见。《纽约时报》称他是“美国研究拉美文学的沙皇”,《华盛顿邮报》说他是“拉美最活跃最大胆的批评家,最有创新精神的文化学者”。
斯塔文斯教授第一次来到中国。他的著作《加西亚·马尔克斯传:早年生活》第一次被译为中文,二〇一二年五月刚在北京的现代出版社出版。
今天他讲演的题目是“译与讹”(Translation and Hypocrisy)。在讲演之前,先请斯塔文斯教授朗读他的专著《加西亚·马尔克斯传:早年生活》(Gabriel Garcia Marquez:The Early Years)中的一个片段。
斯塔文斯(用英文朗读,林源译):
一次次拖延之后,小说的出版日重新定在六月五日星期一。在当地这个日子没法与纽约相比:对公关部门来说,纽约的周一是推出书评的日子,其他媒体也要纷纷亮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一就是个简单的时刻,读者在这一刻能读到出版的小说。六月五日,阿根廷的报纸(包括那些大报,《国家》、《号手》和《理性》)将头版都送给了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争。以色列士兵在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指挥下经过加沙地带侵入属于埃及领土的西奈沙漠。当时空气极度紧张。约旦和叙利亚准备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同回击以色列犹太复国者的入侵。①Eligio García Márquez,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14-15.
《百年孤独》第一周销售八百册,根据马蒂尼斯的说法,不知名的作家能把小说卖到这个份上已是出人意料。接下来的一周数字增长三倍,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版”在封面上的推荐。前两次印刷——一万一千册左右——一个月内销售一空。等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他的小说已连续一个半月排在畅销榜上。②John King,El Di Tella:14.马蒂尼斯还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飞机下半夜两点三十分着陆。他和普鲁亚“在机场里是那个冬末唯一被严寒折磨的人。我们看见他穿着难以名状的格子花呢上衣走下飞机。他身旁有一个美丽的女人陪伴,她长着一双东方人的大眼睛,看上去就像尼菲尔提提女王在哥伦比亚海边的化身。那是他的妻子梅赛德斯·巴尔查”。根据马蒂尼斯的说法,他们两位已是饥肠辘辘。“他们假装将目光投向大草原那边就要出来的太阳,篝火那边有人在烤牛肉。正是这一时刻。在普莱特河上的一家饭店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用讲不完的故事来款待那里的服务员,黎明的曙光使我们大为惊讶。不论是他还是我,谁也没有忘记那家饭店的名字。名字是Angelito el insólito——令人惊愕的小天使。那个黎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我们时已经是如痴如迷,疲惫不堪。这是普鲁亚和我第一次看见日出时分的热带。”
马蒂尼斯对那些时光的回忆极为重要,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永远改变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的那一刻。他对那两位哥伦比亚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行描述周详,既有他们镇定自若的一面,又有他们欣喜若狂的一面。他回忆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赛德斯默默地度过了不公平的两三天。”阿根廷读者成百万地购入这部小说,他们“忘记了《第一版》封面上的照片,所以在大街上没有认出他来”。这一状态很快发生变化。第三天清晨,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在圣达菲大道旁吃早饭,这时他们看见一个家庭主妇从市场上回来,她的购物袋里装着生菜和新鲜的西红柿,等女子从他们身旁经过时,他们发现她手里还有一本《百年孤独》。根据马蒂尼斯的说法:
同晚我们去了剧院。在迪特拉文化中心,《难分彼此的双胞胎》即将首演,这出戏是阿根廷剧作家格里塞尔达·格姆巴洛最好的作品之一。大幕拉开前几分钟我们走入剧院,剧院里的灯还没关。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赛德斯被那些没用的皮子和闪光的羽毛搞得眼花缭乱。我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两三步的距离。他们刚要落座,不知是谁高喊一声“你好!你好!”然后就鼓起掌来。一旁的女子:“为了你的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名字刚一说出来,剧院里的人就开始起身鼓掌。正是在这一刻,我感觉,名望仿佛从天而降,宛如一个精灵。
三天之后,我找不到他们了。外面打进来好些电话要找他们,我们请来工作人员为他们挡驾,又把他请入另一家宾馆,不然读者不让他休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与他见了倒数第二面,为的是在地图上告诉他,帕拉尔默公园哪里有秘密的地方,好让他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吻吻梅赛德斯。最后一次是在机场见的面,他们两人就要返回墨西哥城,怀里抱满了鲜花。他身上披着的光环,此后成了他的第二层皮肤。①GarcíaMárquez的另一部长篇TheGeneralinHisLabyrinth(1989),写的是 Simón Bolívar最后的时光,Álvaro Mutis从中汲取灵感,创作出短篇小说“El último rostro”,两者虽有长短之分,但写法相同。
一九六七年六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旅为他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章。他的名望是在这里获得的,但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难免要感到震撼,所以还不大适应。他天生的腼腆、他的隐私感都遭到了读者的挑战。没完没了的读者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过去、他的写作技巧以及《百年孤独》是怎么写出来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返回墨西哥,但他们在那里没住多久就来到巴塞罗那,作家希望找个合适的、安静的环境,完成他构思已久的另一部作品。这是一部长篇,写一个拉美的独裁者,小说的名字是“家长的没落”。故事情节与文学爆炸时期推出的“la novela del dictador”(描写独裁者的小说)如出一辙,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无一不是暴君。后来作品于一九七五年出版,在这部作品之外,还有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危地马拉,一九四六)、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巴拉圭,一九七四)、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古巴,一九七四)、瓦兰苏拉的《蜥蜴的尾巴》(阿根廷,一九八三)、马蒂尼斯的《贝隆小说》(阿根廷,一九八五)及略萨的《公羊的盛宴》(秘鲁,二〇〇〇)。②Adam Feinstein,Pablo Neruda:A Passion for Life. London:Bloomsbury,2004,p.351.
一九六七年,聂鲁达来巴塞罗那,这位诗人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见。③Adam Feinstein,Pablo Neruda:A Passion for Life. London:Bloomsbury,2004,p.351.聂鲁达的诗歌集《世界之角》收入他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创作的诗歌,他在X一章里,特意写诗五首,对爆炸文学作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广泛兴趣,表达他的个人祝福。聂鲁达借用诗歌称颂科塔萨尔、瓦列霍、略萨、鲁尔福、奥蒂洛、巴斯托斯、富恩特斯及其他作家。但聂鲁达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首诗,他是得到这一礼遇的唯一作家,不过这首诗还没有译成英文。在这首十三行的诗歌里,聂鲁达为《百年孤独》的作者歌唱。诗的名字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林建法:谢谢斯塔文斯先生。大家注意到没有,《百年孤独》的出版日重新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号,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二〇一二年六月五号,斯塔文斯教授在我们“东吴讲堂”上朗读他的著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中的片段,同时为我们做讲演。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或许是一种天意。
现在,我们请斯塔文斯教授为大家做题为“译与讹”的讲演。
今天我应邀来给大家做讲演,十分荣幸。我这一点点的中国文学知识来自经典诗句的阅读,尤其是王维的《辋川集》。我也曾研读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译作。我所熟悉的诗都是英文版的。因我的母语之一是西班牙语,我与西班牙文学的接触多少就发生了迁移。那种迁移不仅是由于译本自然要造成的丢漏,也是由于我不断地阅读各种语言的诗歌所引起的,这里就是指英语。
我想和你们说说丢漏这一要素。对于我来说,那个丢漏是文学阅读中普遍存在的东西:作为读者,我们从书中获取的信息总是取决于我们个体的特质和主观存在。但是说到文学翻译,却好像在我们和文本之间有一层面纱。面纱这个隐喻来自希伯来诗歌复兴奠基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比亚利克说过:“读译作就好像隔着面纱亲吻新娘子一样。”
另一个隐喻也能用来说明上文提到的丢漏,说明与翻译相关的迁移,这个隐喻取自《堂吉诃德》的第二卷,有一章写到堂吉诃德和桑丘走进巴塞罗那的一家印书馆,骑士看了看各种各样的印书,又和印书匠攀谈,他对桑丘说:“一般翻译就好比弗兰德斯的花毯翻到背面来看,图样尽管还看得出,却遮着一层底线,正面的光彩都不见了。”
一座桥、一张弗兰德斯的花毯——这些是翻译所能表达的形象。但是,译者为了制造这些形象都做了些什么呢?
这里,我想进入另一个领域:间谍行为。做一个译者就是做一个双重间谍。一个双重间谍为两个雇主服务:他代表彼方刺探此方,但他又是此方的一分子。这一身份使他拥有内部消息,又因其在目的语群体中的地位而能传递珍贵的信息。这种双重的忠实表明双重间谍是伪君子。他行为矛盾,在矛盾中成为艺术家。双重间谍过的是两面派的生活。
把翻译称为伪君子是种贬低。如果这给你们大家的印象是我个人对译者没有好感的话,那我先在这里道歉。有时候译者令人不高兴,有时候他们就不是。在任何情况里,译者并不因为矛盾而壮大,尽管翻译是无法摆脱矛盾的。做翻译就是在两种语境里搭桥梁,每种语境代表不同的文化。那座桥把这些文化聚在一起,但聚合中丢漏是不可避免的,翻译想做好就需要知道怎样操控丢漏。因两种语境的有所不同,一种语境中的表达在另一种语境中就有所不同。
在目的语中传递语言的精髓,译者需要造假、再编、再创作。所谓再创作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丢漏。就是说源语中的某方面将不能传递给目的语。其中该丢什么和怎么把意思表达完整,是不容易的。译者需要全面地掌握双语的语言习惯知识,尽管源语的知识相对于目的语来说是不那么必要的,是“外来的”。很少有译者能在两种语境之间自由自在地转换,因两种语境中的一个总是起支配作用。
意大利人说:“译者,即叛逆。”(traduttore,traditore)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准确地讲,译者需要作出叛逆源语的准备。但是叛逆给人的印象是背信弃义,有意辜负人家的信任。翻译依靠的是“信”。他的译本希望使读者不仅读着顺口,而且还要保证源语中的意思传达到目的语中。其实这是办不到的,所以才有叛逆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叛逆是随“信”的产生而产生的。
“讹”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伪君子装模作样,假惺惺的,好像自己相信,其实并不相信。他希望诱人凭表象相信他,然而他的表象是谎言,是移花接木。伪君子要遭到社会谴责唾面,因为他们对别人不真诚。而我们的共识是,对人假情假意的间谍,对自己也是假情假意的。
另一方面,严格来说,译者又不是伪君子,因译本是针对源语真实意思的表达。但因完全的真实再现是办不到的,一定程度的误译和背离就不可避免。那么“讹”就不是一种行为,而是译本的一部分。为了使“讹”最小化或最大化,译者悟出了一些技巧:要么使译本尽可能地自然流畅,使读者感觉译本犹是另一部原作,要么强调翻译技术,由此使读者觉得面前的译文是精心调制、重新整理和重新混合出来的。
无论用什么技巧,对于译者来说要意识到自己充当双重间谍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要知道自己是个叛逆者,是伪君子。这种感悟相当于一位老师认识到无所不知是办不到的,但要设法为学生提供正确的工具,让他们在宇宙中获得方方面面的知识。
正如大家所见,我把翻译看作充满荆棘的行为。为了把作家作品介绍到另一种语言语境中,我已经用了好多宝贵的时间。例如,我曾尝试把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歌总集》(Canto General)用英语流畅地翻译出来。我发觉那种流畅是海市蜃楼。聂鲁达生活在西班牙语里,事实上,他的诗歌使西班牙语更有弹性。他诗歌的英语译本永远赶不上西班牙语的。这种认知并不能阻碍我们对其作品进行多国语言的翻译。不尝试就是承认失败。每一部译本都是误译,是丢漏,是不完美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力而为。不然的话,我们将生活在没有文化交流的惟我主义的世界里。
我也曾把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作品从英语译到西班牙语。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疯狂的。狄金森隐晦的主题、有个性的标点是英语所必不可少的。作为一名译者,我希望有最通达最接近的译文。是的,接近是一种叛逆,但却是我情愿写上名字的叛逆。
倘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让大家觉得我是在批评翻译,那我要再次抱歉。可能大家将因伪君子、叛逆者和两面派等社会谴责性词汇才这样觉得。事实上,尽管你不像我是个译者,人类行为中的叛逆也是无处不见的。为了达到目的,我们自欺欺人,忘记了梦想。精神生活矛盾重重,如此而已。正因如此,间谍们才总是有趣的人。
谢谢大家来听我的演说。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用汉语朗读一首唐诗。我担心这个梦想无法实现,因为我知道年龄大了,再学一门语言有多不容易。然而,我们还是要活到老,梦到老。
林建法:斯塔文斯教授的讲演非常精彩,首先他是一位实践者——译者,然后才有他的这一番理论阐释。他说:“在目的语中传递语言的精髓,译者需要造假、再编、再创作。所谓再创作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丢漏。”他结合自己的实践,深入浅出富有创造性地阐释了翻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见——译与讹,这个讲演尽管简短,但给我们的却是众多的启示与导引,我想会对有志于翻译与研究的老师与同学产生潜在的影响。
今天讲演就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斯塔文斯教授的精彩讲演。
【译者简介】林源,复旦大学法学学士,现为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翻译与双语传意文学硕士研究生。
东吴讲堂
依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美国马萨诸塞州安姆赫斯特学院拉丁美洲和拉丁文化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