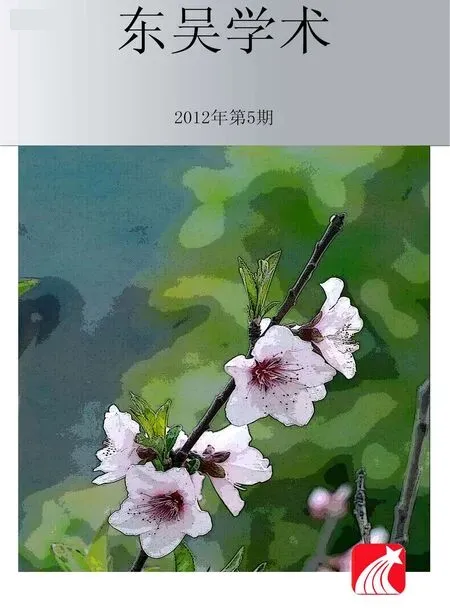博采中西积力久入——漫谈张隆溪与钱锺书学问之道
2012-04-02蒋洪新
蒋洪新
哲学与文化
博采中西积力久入
——漫谈张隆溪与钱锺书学问之道
蒋洪新
一九八○年六月上旬某一天,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来北京大学访问,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张隆溪陪同并作翻译,佛克马要他陪同去见钱锺书,他自己也想借机见见这位敬仰已久的大学者。临行前北大外事处一位办事员嘱告张隆溪,钱锺书学问大,脾气也大,若发现他对你脸色不好,你就中途开溜。张隆溪不以为然,心想学问愈大者应该愈平易近人,不会跟他这样的后生闹脾气。话虽如此,但他还是有点忐忑不安。抵达三里河南沙沟钱锺书寓所,钱锺书亲自开门迎进,随后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语和佛克马滔滔不绝。在会谈中他们谈到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的理论,张隆溪发表了与佛克马不同的看法,这引起了钱锺书的好感与注意,也许开始钱锺书以为张隆溪是外事处随员,还说不定附带监视“涉外”活动的任务(因当时“文革”才结束不久),听到张隆溪用英文谈弗莱《批评的解剖》的体会,钱锺书立即表现出很大兴趣,并转过身来对张隆溪说,中国现在大概还没有几个人读过弗莱的书。当时国门才开,对西方当代批评的理论著作,国内学者能问津者不多,何况张隆溪已读出自己的见解,怎能不引起钱锺书对他的好感呢?会见完后,钱锺书把张隆溪叫到另一间房子,用毛笔题赠《旧文四篇》一书,并要杨绛将家里电话号码告诉张隆溪,对张隆溪说:“以后你要来,尽可以先打电话。”①张隆溪:《怀念钱锺书先生》,《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22-2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从此张隆溪与钱锺书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学术交往。
鲁迅曾云:“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第4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鲁迅此话是研究一个作者及其作品较为全面的论述。钱锺书的大名在海内外已是家喻户晓,这里不必赘述。如今张隆溪在国内外比较文学界也是大名鼎鼎,但圈外的人对他可能还有些陌生。他们属于两代人,不同时代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人理当有许多不同,但鲁迅所提及社会状态以及他们在那种社会状态下如何作为,的确值得我们关注。钱锺书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钱基博乃著名文史学家,从小国学童子功扎实,又进教会学校习英文,青年时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吴宓、朱自清等名师教导,大学阶段其学问被师生称颂,誉为人中之龙。清华毕业后获奖学金负笈英国牛津大学,在此获文学学士学位(B.Litt.Degree),又到巴黎大学研读两年,回国到清华(当时为西南联大)做教授时还不到三十岁。此时钱锺书已是地地道道学贯中西的大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出版的英文著作《现代中国小说史》有专章研究钱锺书,其中讲钱锺书学成归来,已通晓英、拉丁、法、德和意大利文学。①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ThirdEdition,p.432.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一九八三年,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说,钱锺书对中国和西方两方面文学和传统的了解“在今日之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无人可比”。②见Simon Leys(Pierre Ryckmans)发表在LeMonde1983年6月10日文章。通过与钱锺书多年交往和深刻研究钱锺书著述,张隆溪对钱锺书横贯中西的学问非常了解并极为敬仰,他纪念钱锺书百年诞辰有一篇文章,题为“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他在文中写道:“在近代学人中,钱锺书先生堪称是真正了解中学与西学,以其独特方式探讨中西学问的大学问家。”“中国不仅古代学人不通外文,就是现代学者对西方典籍也了解有限,而且通外文往往限于英文或法文,能兼通德、意、西、拉丁等多种文字,则非常少见。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锺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③张隆溪:《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书城》2010年3月号,收入《一毂集》,第279-28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相比钱锺书的家学与少年青年的教育背景,张隆溪就没有那样幸运了。张隆溪中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美好的时光抛撒在田野与车间,但他发奋自强、好学不辍,高考恢复后他直接报考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结果在众多高手较量中夺得第一名。李赋宁在他的回忆录《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中说:“许同志把张隆溪的作品拿给我看,问是否能达到北大英语系硕士研究生的标准。我看后,立即鼓励他报考。他那年三十一岁,考试成绩在第一次录取的十二名硕士生中名列第一。”④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第1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到北京大学读书应该说是张隆溪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里不但有充足的时间和丰富的藏书,而且名家云集,西语系当时有朱光潜、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田德望等著名教授,还有外籍教员。在北大读书期间尤为可贵的是,张隆溪经常得到朱光潜与钱锺书的入室指导,这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张隆溪北大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又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这应该是张隆溪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革”十年的自学和北大五年的积累,他来哈佛做研究生时,觉得自己在阅历与学识方面不逊于周围同学,一些美国学者倒把他当作来自北大的学者,而不仅是研究生。在哈佛六年,他有充足的时间潜心读书,而且读到了大量国内没有读过的书。这里还有世界一流的名师,他说:“在哈佛上课得益很多的是听一些造诣精深的学者讲他们自己最深入的研究。如詹姆斯·库格尔(James Kugel)讲《圣经》与文学批评,芭芭拉·卢瓦尔斯基(Barbara Lewalski)讲弥尔顿《失乐园》,杰罗姆·巴克利(Jerome Buckley)讲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批评,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讲比较文学,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讲莎士比亚和精神分析等……此外还有一些教授,虽然我没有正式上他们的课,但平时却颇多交往,得益很多。如英文系的丹尼尔·爱伦(Daniel Aaron)和摩顿·布隆菲尔德(Morton Bloomfield)教授,人类学系的张光直教授,东亚系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等。斯拉夫语系尤里·斯垂特尔(Jurij Striedter)教授生在俄国,长在德国,曾做过伽达默的学生,以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理论著名。他知道我对阐释学有兴趣,愿意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尤里熟悉文学理论,做事一丝不苟,思想清晰而讲究逻辑联系,对我帮助很大。”⑤张隆溪:《一毂集》,第49-5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他还有幸在耶鲁见到德里达,并与他就“道与逻各斯”等学术问题讨论两三小时。在哈佛学习期间,德国的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恰好在邻近的波士顿学院讲学,与他探讨阐释学问题,这次见面与交谈坚定了他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深入阐释学研究。一九九二年在哈佛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王元化,他们一见如故,此后有书信交往与面谈。
在哈佛阶段,张隆溪已经在美国的《批评探索》、《比较文学》、《得克萨斯语言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并受邀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作学术讲演。一九八七年他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时,同时在哈佛教授专修西方文学二年级学生的文学课,这在留学生中亦属少有。一九八九年他哈佛毕业后,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比较文学教授,在那里工作近十年。一九九八年,张隆溪在美国生活十六年之后回到中国香港,受聘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继续作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从如上经历可以看出,张隆溪在青少年时期虽失之桑榆,但“文革”梦魇结束时还年富力强,可谓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我与张隆溪已有多年交往,他也是博通古今中外,我多次听他讲演,中英文流畅优美,音色漂亮,往往讲到德国与法国文学时,德文、法文脱口而出。他的学术成果在近几十年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迄今仍源源不断。这里我举一些他出版的主要著作:《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一九八六)、The Tao and the Logos(一九九二,中译《道与逻各斯》,一九九八、二○○六)、Mighty Opposites(一九九八)、《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二○○○、二○○四)、《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二○○五)、Allegoresis: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二○○五)、《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二○○六)、Unexpected Affinities:Reading across Culture(二○○七)、《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二○○九)、《灵魂的史诗:失乐园》(二○一○)、《一毂集》(二○一一),在比较文学界当今中国学者中,能像他那样用中英文写作且在国际上有如此大影响者,可谓凤毛麟角。
与张隆溪相比,钱锺书出学术成果的年代颇为艰辛,中青年时山河破碎,战火纷飞,解放后政治运动迭起不休,学术研究受到干扰,“文革”结束时钱锺书已入古稀之年。好在他宝刀不老,厚积薄发,其旷世之作《围城》、《谈艺录》、《管锥编》面世后,被誉为中华文化瑰宝,此乃国家与民族之幸。钱锺书长张隆溪三十七岁,他们所处社会状态有不同和相同的时期。在他们令人瞩目的成就面前,人们也许会说他们有超常的记忆力,在我看来,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学问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非常人可比。钱锺书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读书人实乃“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钱锺书这样说,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有关他的“钟爱书”、“书痴”的故事已经在许多传记和研究他的著述里描写不少,我不想重说,这里仅叙述一些他抗战期间在国立师院任教的故事。一九三九年,钱锺书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到上海度暑假,然后去了湖南国立师院(国立师院乃笔者目前工作的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就职。一路上颠沛流离,受尽饥饿折磨,还随时有日军轰炸之险,他旅途所见后来都写进小说《围城》里。《围城》有一段描写方鸿渐一行的遭遇,实乃钱锺书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方鸿渐在金华“欧亚大旅社”一夜遭受跳蚤、臭虫叮咬,小说幽默地写道:“外国人说听觉敏锐的人能听见跳蚤的咳嗽;那一晚上,这副耳朵该听得出跳蚤们吃饱了噫气。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蚤虱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够成个人,可是并没有成佛。”在鹰潭“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来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旁边一碟馒头,远看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这段经历后来钱锺书在《谈艺录》里评论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一诗时,被情不自禁插入再现:“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云:‘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当异事徵。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任诩东坡渡东海,东川若到看公能。’写实尽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军舆兴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所历之境,迄今未改。行羸乃供蚤饱,肠饥不避蝇余;恕肉无时,真如士蔚所赋,吐食乃已,殊愧子瞻之言。每至人血我血,搀和一蚤之腹;彼病此病,交递一蝇之身。子尹诗句尚不能尽焉。”①钱锺书:《谈艺录》,第183-1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可见小说中方鸿渐此处遭受的痛苦,与钱锺书所遭的难是相当的。到吉安,方鸿渐等人“住定旅馆以后,一算只剩十来块钱”,“鸿渐饿得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公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辛楣笑里带呻吟道:‘饿的时候不能笑,一笑肚子愈掣痛。好家伙!这饿像有牙齿似的从里面咬出来,啊呀呀——”更滑稽的是,李梅亭躲着吃山薯的形态,“鸿渐看见一个烤山薯的摊子的生意,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忽然注意有人正作成这个摊子的生意,衣服体态活像李梅亭;仔细一瞧,不是他是谁,买了山薯脸对着墙壁在吃呢。鸿渐不好意思撞破他,忙向小弄里躲了”。与钱锺书同行的徐燕谋在《纪湘行》写道:“艰难抵庐陵,囊空如洗括。街头食薯蓣,饿极胜崖蜜。羞为识者见,背面吞且噎。”如此恶劣旅途,钱锺书却依然能“怡然自得,手不释卷”,②邹文海:《忆钱锺书》,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第81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哪怕在他同伴邹文海看来一本索然寡味的英文字典,在钱锺书读来都会津津有味。③见蒋洪新《〈围城〉内外的故事:钱锺书与国立师院》,《文景》2006年第6期,该文收入蒋洪新《大江东去与湘水余波》,长沙:岳麓书社,2006。二○一一年我陪张隆溪和赵一凡冒酷暑访问钱锺书曾经工作的地方——蓝田国立师院(今湖南涟源市一中),钱锺书在《围城》将此地写成“三闾大学”,其中说“这乡镇绝非战略上的必争之地,日本人唯一豪爽不吝啬的东西——炸弹——也不会浪费在这地方”。这里地处湘西,迄今还不算发达,当年更是穷乡僻壤,钱锺书在这里度过近两年,寂寞而清苦,同时在此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在国师完成了一半中国诗话里程碑作品《谈艺录》的写作,在国师季刊发表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并开始构思小说《围城》。诚如《谈艺录》序言所言:“《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由此可见艰难困苦也未动摇钱锺书读书与研究学问的干劲。杨绛在三联出版的《钱锺书集》中说道,钱锺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顾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④钱锺书:《钱锺书集·管锥篇(一)》,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6月初版,2004年4月第4版。此朴实言语道出了钱锺书的终身志向与追求。
同理,张隆溪能成为今天的张隆溪,好在他于“文革”特殊年代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停歇。他中学毕业后插队到农村,那时不但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精神生活对于有思想的青年人也极为枯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三年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知青对书本和知识,都有如饥似渴的追求。”⑤张隆溪:《锦里读书记》,《书城》2006年8月号,收入《一毂集》,第15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爱读书的人没有学上,甚至找些好书读都不容易,对于酷爱西方文学的张隆溪而言,要弄到原版的外国书更是困难。他自述在下乡做知青时,他中学英文老师潘森林将抄家劫余的两本书送给他,一本是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另一本是英美文学选读。这对张隆溪而言可谓如获至宝,在微光如豆的煤油灯下,他常常诵读至深夜。下乡三年他白天种地,晚上苦读,靠煤油灯的墙壁被油烟熏得黝黑,积了厚厚一层油灰。韩愈《进学解》有名句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用来形容那时张隆溪的勤学是恰如其分的。一九七二年春天,他从四川德昌的山村调回成都,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车队当修理工。他每天背着书包上班,就像学生背着书包上学,一有空隙,洗去满手油污,开卷就读。经同事介绍认识解放前曾在《中央日报》当过记者的欧阳子隽,欧阳子隽藏有很多英文原版书,他当时在百货公司做售货员,由于他为人谦和低调,未遭受冲击,这些好书也幸存下来。他结识张隆溪时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动乱岁月还有这样好学的年轻人,且居然还能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于是他跟张隆溪成为忘年交,他一屋子的英国文学经典书也就成为张隆溪的精神食粮。在大家不读书而且缺书的年代,张隆溪能较为系统地阅读莎士比亚全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他还从欧阳子隽那里借阅到钦定本《圣经》、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帕格瑞夫(F.T.Palgrave)所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这些书是张隆溪最好的朋友,似乎冥冥之中专门为他准备的。张隆溪后来深情地回忆说:“我永远感谢欧阳先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为我打开书的宝藏,提供精神的食粮,这对我后来的发展,的确起了关键作用。”①张隆溪:《锦里读书记》,《书城》2006年8月号,收入《一毂集》,第15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我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讲述张隆溪这段经历,因为这些事迹对现在许多年轻人来说,已是久远的故事。那个年代耽误了国家的发展,也误了一代人,许多人自此沉沦,惟有意志顽强者方能如此坚持不懈读书。古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下乡与工厂的经历从某种意义看来,对张隆溪也是意志的磨练。须知,在那荒唐的岁月,谁知道自己的未来与读书有多少联系呢!何况张隆溪偏爱读的是些洋书,当时的口号是:“不读ABC,照样搞革命”。但天不丧斯文,好读书者自会有天助的。在那不幸的年代能有机会找到这些书已经不易,能读到这些好书更是幸运的,但幸运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文革”结束后张隆溪凭着十年自学,一举考取北大研究生,以后留学哈佛,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做比较文学教授,现为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如今他在东西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与荣誉,这里举几例就知道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二○○五年二月底至三月初,他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邀请,作了四次亚历山大讲演,这个讲座传统上是治英国文学的欧美名家方有资格,近年来一些国际著名的文化批评学者与作家前来主讲,能受邀参加此讲座的莫不引以为荣。张隆溪是该讲座设立以来唯一受邀的亚洲学者。二○○七年三月,他获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为期三年,每年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作短期讲学。香港城市大学在二○○七-二○○八学年设立了全校教员公开竞争的研究奖,他获得了大奖(Grand Award)。我当时在香港城市大学做客座教授,参加了香港城市大学有史以来首次研究奖的颁奖仪式,场面非常隆重。那一年城大全校仅两人获奖,张隆溪获得唯一的大奖,第二名获得研究杰出奖的,是一位物理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是素以理工及工商管理见长,该校拥有多名院士、一大批世界级知名学者教授,张隆溪作为人文学科教授能脱颖而出,获此殊荣,证明了他确实作出了非凡成绩。二○○九年春节刚过不久,张隆溪的学术生涯又增添喜讯,他被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这是一项极高的学术荣誉,入选的该国外籍院士有三十九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欧美各国的学者,亚洲只有两人。香港城市大学郭位校长为他专门举办了一个庆祝会,来参加的人很多,除本校同事之外,还有如李欧梵、陈方正、罗志雄、毛俊辉、钟玲、Henry Steiner、荣新江、傅杰等。二○○九年九月底,他应邀到瑞典皇家学院讲演。二○一○年是张隆溪学术讲演繁忙的一年,三月中旬,参加瑞典皇家人文学院的庆典,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演,在此前后还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爱丁堡大学讲演。四月十二日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作二○一○年的波吉奥里讲座(The Renato Poggioli Lecture),十三日在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讲演,十五日在韦斯里大学曼斯菲尔德·弗里曼东亚研究中心作二○一○年的弗里曼讲座(The Mansfield Freeman Lecture)。二○○七年六月,欧洲布里尔出版社(Brill)聘请他和德国学者施耐德(Axel Schneider)共同主编布里尔中国人文学术丛书。二○一○年五月,美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邀请张隆溪担任这份刊物的顾问编辑。该杂志在美国人文学科杂志中享有极高声望,其顾问编辑包括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伊琳·希苏(Helene Cixous)、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知名学者。二○一○年八月,在韩国首尔召开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九届大会,张隆溪获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委会委员。
自一九八○年张隆溪陪佛克马踏进钱门,此后他们交往频繁,钱锺书给张隆溪的书信达五十多封,在张隆溪这一代学人中,能与钱锺书如此联系密切并得到赏识的人为数不多。钱锺书在解放后没有教书与带学生,在某种意义上,他把张隆溪视为私淑弟子与同道,在他送给张隆溪一部书的题记里,钱锺书用《论语》里的典故,以孔子和子夏来暗示他和张隆溪的关系。①张隆溪在《怀念钱锺书先生》中提到他去哈佛时到钱锺书那里辞行,钱锺书送他上下册的一套《全唐诗外编》作为纪念并题字云:“相识虽迟,起予非一。兹将远适异域,长益新知。离情固切,期望亦殷。”这是用《论语·八佾》里的典故:“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张隆溪看到这几句话,感到无限亲切,但又觉无比愧怍,他写道:“尤其在钱锺书面前,是连作学生的资格都没有的,然而钱锺书对我却特别厚爱。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卞之琳先生开玩笑说我是‘钱锺书的死党’。钱锺书故意把这玩笑直解,大笑着对我说:‘钱某还在,你活得还会更长,怎么能说我们两人是‘死党’呢?我听了这话深为感愧,因为做这样的‘死党’是要有条件的,而我还不够这样的条件。钱锺书给我题的字里,‘起予非一’当然是溢美之辞,‘期望亦殷’四个字,在我只觉得有相当的分量。”见《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36-2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张隆溪更把钱锺书视为自己的学问导师,这在他的言谈与文章里常有提及。他的著作有题献给钱锺书的,如《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还有专门研究、怀念甚至捍卫钱锺书的文章,如《钱锺书谈文学的比较研究》、《钱锺书的语言艺术》、《思想的片段性与系统性》、《怀念钱锺书先生》、《读〈我们仨〉有感》、《论钱锺书的英文著作》。②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不过张隆溪虽然与钱鍾书过从甚密,又有许多书信往来,但在国内兴起“钱学”时,他却少有参与,绝不以“钱学”为依傍或标榜,而自己走一条中西比较研究的路。但在钱锺书辞世之后,一些人对这位大学问家毫无道理地评头品足,张隆溪则忍不住要起而捍卫曾经对他如此厚爱、他也如此尊敬的前辈。二○一○年我访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这里曾是张隆溪工作过的地方,他的哈佛大学博士同学叶扬教授在此。这一年是钱锺书百年诞辰,面对这位大学者,海内外有不同反响,有纪念和颂扬的,也有不少批评甚至攻击的声音。针对轻诋钱锺书之风,张隆溪当然拔剑而起,写出反驳文章《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③此文最初发表在《书城》2010年3月号,后收入张隆溪《一毂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因该文涉及一些学界大腕,有几位朋友不免为他担心,但张隆溪心怀坦荡,更有学术底蕴来迎接辩论。老友叶扬形象地描绘了张隆溪的学术性格:“隆溪的性格我是了解的,他像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若钱锺书此时地下有知,我想他也许会神秘地笑着说,此乃真吾死党也。在我看来,钱锺书与张隆溪投缘,除了好读书和中西学问大之外,主要是他们淡泊名利、坚持真理、卓尔不群的学术品格相似。
柯灵评论钱锺书的一段话颇为精到,他说:“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两者相互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撇得开,灵心慧眼,明辩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④周振甫、冀勤编著:《钱锺书〈谈艺录〉读本》,第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由此可见钱锺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那就是“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同时他能做到“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钱锺书自己在《谈艺录》序中说道:“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其言曰:‘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⑤钱锺书:《谈艺录》,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钱锺书这些话在张隆溪看来,“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他的学术视野与治学方法。不仅较早的《谈艺录》具有这样的视野,依照这种方法,其后论述更广的《管锥编》亦如是。这种开阔的视野不仅未见于中国传统著述,在现代学术著作中亦是凤毛麟角”。⑥张隆溪:《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书城》2010年3月号,收入《一毂集》,第228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从这话可以看出,张隆溪非常赞赏钱锺书这些思想,并认为这奠定了东西方比较研究在学理上的基础。钱锺书自己的实践已为大家树立了很好的楷模。
在张隆溪看来,当代的学术发展有两个趋势愈见明显,一方面诚如钱锺书所云专门学科愈分愈细,另一方面又逐渐有分而复合的趋势,即跨学科或科际整合研究的出现。①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鉴于此,他主张向朱光潜和钱锺书那样的前辈学人学习,要有开阔的眼光与胸怀,绝不以做某一门学问的专家为满足,而总是超越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由精深而至于博大,由专门家而至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通人。他在《道与逻各斯》里说:“打破学术领域的疆界,跳出自己熟悉的蓬篙而看到更大的天地,尽管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世界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冒险,但在我看来却似乎始终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②张隆溪:《道与逻各斯》,第11-1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他在《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一书中说得更为晓畅而富有警示作用:“在今日的学术环境里,知识的发展已分门别类到相当细微的程度,不同门类的知识领域之间又各立门户,壁垒森严,结果是学者们都不能不成为专治一门学问的专家,眼光盯住自己专业那一块狭小的地盘,不愿意放眼看出去。专家们往往眼里只有门前草地上那一两棵树,看不到大森林的宏大气魄和美,反而对森林抱有狐疑,投以不信任的眼光。”③张隆溪:《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第2、4、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然而,涉及东西文学或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两种倾向需要厘清与批判。一是文化对立说和文化相对主义,持文化对立说或者不可通约论者,认为东西方语言与文化的鸿沟无法跨越,把东西文化的差异尽量夸大,使两者形成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断言东西方完全没有任何比较的可能。然而除专家们对范围广阔的比较普遍表示怀疑之外,东西方比较研究还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有许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常常习惯于把东方、西方或东方人、西方人当成建构思想的概念积木块,粗糙笼统地积累起来思考。习惯于用笼统粗糙的概念积木块来思考的人,不会去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得出简单化、脸谱化的结论,抹杀个人的种种差别,把具体的个人都归纳在东方和西方、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类粗鄙的概念积木之下。④张隆溪:《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第2、4、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根据张隆溪多年的治学经验,他发现:往往是读书少,知识面较窄的人,反而勇气与眼界成反比,见识越小,胆子越大,越敢于一句话概括东方,再一句话又概括西方,把东西方描述成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对立。⑤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第4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张隆溪认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当然存在差异,可是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文化之内。在同一传统甚至同一时代的诗人和作家们之间,确实也有各种差异。文化的完全同一和文化的决然对立,都实在是骗人的假象。⑥张隆溪:《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第2、4、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在西方汉学和整个亚洲研究中,文化相对主义可以说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会刊《亚洲研究学报》主编巴克(David D.Buck)在九十年代的一篇引言中指出,文化相对主义是美国大多数亚洲研究者所抱的信念,他们怀疑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任何概念上的工具,可以用不同人都能接受的方式理解和解释人之行为和意义”。⑦David D.Buck.“Editor’s Introduction to Forum on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in Asian Studie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Feb.1991):31.转引自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这样一来,汉学或亚洲研究就形成了张隆溪所定义的“文化的封闭圈”,汉学家们往往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与西方文化之差异,使汉学成为西方学界一个特别的角落,非专门研究者不能入,于是这个领域与其他方面的文化研究隔得很远,也没有什么关联。汉学研究变成汉学家们自己关起门来说话的一个小圈子。⑧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张隆溪认为,我们另一方面需要警惕“东方文化优越论”的陷阱。西方理论家们在对西方传统作自我批判的同时,往往把中国或东方浪漫化、理想化,强调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反面。此时张隆溪提醒国人一定要首先清点一下自己的家当,切不可把别人的迷魂药当作宝贝,而呈现夜郎自大的姿态。中国二十世纪初贫穷落后,到现在则初显繁荣,但随时都不乏高歌猛进者,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①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转引自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人类的前途岌岌可危,只有中国传统即东方文化历来提倡的‘天人合一’,庶几可以对症下药,拯救濒于灭绝的自然和人类。”②见季羡林、张光璘编选的上下两册《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转引自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这固然可以满足国人的虚荣心,但理论依据与现实的可能在哪里?张隆溪在他与德里达等许多西方学者对话以及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都表现出理论的锋芒,并以具体的例证来正本清源。③这方面的文章有:《非我的神话:论东西方跨文化理解问题》、《文化对立批判:论德里达及其影响》、《经典与讽寓:文化对立的历史渊源》、《汉学与中西文化的对立》。著作有:《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十论》、《强力的对峙》、《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讽寓解释:论东西方经典的阅读》。那么,理清这些重要的理论分歧之后,我们以何种方法或者途径来展开跨文化的比较与研究呢?这是一个横亘在众人面前的难题。张隆溪认为:要展开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就必须首先克服将不同文化机械对立的倾向,寻求东西方之间的共同点。只有在此基础上,在异中见同,又在同中见异,比较研究才得以成立。④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第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他在《道与逻各斯》中说得清楚了然:“发现共同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使异质的东西彼此等同,或抹杀不同文化和文化固有的差异。”⑤张隆溪:《道与逻各斯》,第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过分强调文化、种族、性别等种种差异,张隆溪却另辟蹊径,集中在对同一性的强调,把不同的文学传统聚集在一起,使之有可能展开跨文化的对话,因此寻求东西方之间的共同点有着深远文化意义,正如赫尔博斯所说:“我们总爱过分强调我们之间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我们的仇恨,那真是大错特错。如果人类想要得救,我们就必须着眼于我们的相通之处,我们和其他一切人的接触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强化差异。”⑥Jorge Luis Borges,“Facing the Year 1983”,Twenty-Four Conversations with Borges,Including a Selection of Poems,trans.Nicomedes Suarez Arauz et al.Housatonic: Lascaux Publishers,1984,p.12.转引自张隆溪《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第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在避免强化差异的同时,我们还要避免把中国与西方的文学作品随意拼凑在一处,作一些牵强附会、肤浅浮泛的比较。我们不仅要熟悉中国和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而且要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传统背景上理解这些文学和文学批评演化变迁的历史。换言之,文学研究不能仅限于文本字句的考释,我们要有范围广阔的知识准备,不仅了解文学,而且要了解与之相关的宗教、哲学、艺术和历史。⑦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第5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其实,要真正做到如此境界,就要朝钱锺书所说的“通人”看齐。
近来有人评价钱锺书,说他只是学问家,但不是思想家。⑧李泽厚、刘再复:《共鉴五四新文化》,《万象》第11卷,第7期,2009。我认为,持这种看法者未必深入研读过钱锺书的著作,试看钱锺书无论是用英文写的《英文文集》,还是用现代文写的《七缀集》,或是用文言文写的《谈艺录》、《管锥编》;无论是像《中国诗与中国画》长达几万字的论文,还是如《谈艺录》与《管锥编》著作中分条评点式的短文,都无不厘清问题,凸显思想与智慧的光芒,且在论证过程中,常常纵横中西、旁征博引、具体入微,文字充满机趣与感染力。事实上许多时候一个人的学问与思想并不是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的。这里我举庞德研究为例:钱锺书在他的著述里有几处提到庞德,他在一九四五年《中国年鉴》发表英文文章“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提到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风格的关系,他指出庞德总认为中国文学是具体的,源于中国文字的具体性,因此,庞德想以表意法来写诗,将意象浇铸在视觉想象上。庞德自以为所有意象都是视觉的,而不知表意法在中国文字传统构造中仅是六种之一,在中文诗中听觉意象与嗅觉意象并不像视觉意象那么具体,但也并不少。因此钱锺书认为庞德对中国诗与中国文字的了解是一知半解和自以为是,他说:“Pound is construing Chinese rather than reading it,and,as far as Chinese literature is concerned,his A.B.C.of Reading betrays him as an elementary reader of mere A.B.C.”①钱锺书:《钱锺书英文文集》,第28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请看钱锺书此话说得多么中肯而又机智。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有将《文心雕龙》与庞德的诗论进行比较:“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文心雕龙·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按Ezra Pound论诗文三类,曰Phanopoeia,曰Melopoeia,曰Logopoeia,与此词意全同。参见How to Read,pp.25-28; ABC of Reading,p.49。惟谓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物象,则稚马矣之见矣。”②钱锺书:《谈艺录》,第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这两处文字说明钱锺书曾研读过庞德的理论著作,而且批判庞德的话语不多,却能一语中的。钱锺书把中文诗歌追求的形、声、情与庞德的形象诗、音乐诗、意义诗对读比较,虽然仅是行文中偶附的片言只语,但也开了中文诗学与庞德诗学相比较的先河,这在前人的介绍中是找不到的。③当然,把中国古诗的“情”等同于庞德Phanopoeia还有待商讨。另外,钱锺书在此按语末尾说:“惟谓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物象,则稚马矣之见矣”,实际上是在批评庞德,因为后者在上述两部著述中都认为,中文由于自己文字的特殊性,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形象诗。④Ezra Pound:ABC of Read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p.29.这应该是中国庞德研究中对庞德的汉语言观提出质疑的最早案例。改革开放之后,钱锺书在中美首次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的开幕词中说到庞德:“假如我们把艾略特的说话当真,那么中美文学之间有不同一般的亲切关系。艾略特差不多发给庞德一张专利证,说他‘为我们的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⑤钱锺书:《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58、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钱锺书一提到庞德,就往往带点调侃:“庞德对中国语文的一知半解、无知妄解、煞费苦心的误解增强了莫妮克博士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庞德的汉语知识常被人当作笑话,而莫妮克博士能成为杰出的汉学家;我们饮水思源,也许还该把这件事最后归功于庞德。可惜她中文学得那么好,偏来翻译和研究我的作品;也许有人顺藤摸瓜,要把这件事最后归罪于庞德了。”⑥钱锺书:《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58、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这是钱锺书为《围城》德译本所写的前言,文中提到的莫妮克是位汉学家,她研究过庞德与中国的关系,后译《围城》和研究钱锺书。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钱锺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注意到庞德,据此不得不佩服钱锺书之学术视野,而且他不局限蜻蜓点水,而是细致研究庞德的书,三言两语就能指出庞德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翻译之谬误。钱锺书将庞德的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进行比较,挥洒自如,充满机智与幽默。近十年我读过的关于庞德研究的著作不下百部,我认为钱锺书的这种片断式点评与分析绝不逊于某些鸿篇巨制。
钱锺书的主要学术著作《谈艺录》与《管锥编》采用中国传统著述方式,分列条目评点古代经典与前人著述,行文是典雅的文言文,却又大量引用西方著述,以中西文本之具体比较来阐发中国古典著作的思想意蕴。⑦张隆溪:《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书城》2010年3月号,收入《一毂集》,第2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对钱锺书这种独特的文体,也许会有人纳闷,钱锺书为何不把这些丰富深邃的思想发展成系统的理论?张隆溪在其论文“思想的片段性和系统性”中做了翔实的论证,他认为“这种写法毫无疑问体现了钱锺书对理论系统和方法的怀疑”,⑧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因为钱锺书本人在《读〈拉奥孔〉》一文谈到过:“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张隆溪对此有一段精妙的论述:“片断和系统本无所谓优劣,我们没有理由一概否认系统理论的价值,更不能借口重视片断思想,偷懒不去认真读大部头的著作。钱锺书的著作虽然写法是非系统的,但却基于对古今中外许多系统大著作深切的了解之上。没有钱锺书那样博富的学养和深刻的洞见,也就写不出《管锥编》、《谈艺录》那样处处闪烁思想光芒的著作。”①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张隆溪觉得钱锺书的著作可像一般系统性的学术著作那样从头到尾读,也可像字典、辞典那样随时翻检,挑选某部分某章节来读。钱锺书的著作没有空话,却处处给人启发。张隆溪自己每次阅读,均有收获,“使我愈来愈认识到钱锺书著作丰富的意蕴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天下读者可以共同享用的真正的精神财富”。②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大诗人艾略特曾有一段高论:“未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窃取,手低的诗人糟蹋他所拿取,高明的诗人使之更好或与原来相当。高明的诗人把他窃取的熔化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之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而手低的诗人把它投入一团没有粘合力的东西。高明的诗人往往会从年代久远的、另一种文字的或兴趣不同的作家借取。”③Alasdair D.F.Macrae,York Notes on the Waste Land,p.51.艾略特在此提出借鉴他人同时,要融会贯通,不要限于模仿,而是要善于“窃取”。我通读钱锺书与张隆溪的著作之后,除了佩服这两座学术高山之外,还好奇地比较了他们行文的风格。张隆溪目前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中英文大致各占一半,他所处的时代与钱锺书不一样,当然不是条目评点的文言文,而是按照西方严格要求系统的学术著作方式,但他高屋建瓴、横跨东西的学术视野,细致入微、绝不空疏的文风是与钱锺书一脉相承。
张隆溪对钱锺书的继承与发扬还在于“阐释之循环”的研究方法,钱锺书在《管锥编》论乾嘉“朴学”一节时说道:“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俾识古,鸟之两翼、剪纸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钱锺书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提到阐释学,且与中国文论思想相比较的学者。在张隆溪看来,钱锺书的看法与当代德国阐释学名家伽达默尔不谋而合。钱锺书在自己的文章与著述中,不正是反复运用古今相察、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的阐释循环吗?张隆溪深得钱锺书与伽达默尔两位大师文章之道,他早在一九八二年受钱锺书之命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的英文论文《诗无达诂》(后用中文改写,发表在《文艺研究》一九八三年冬季一期)就初现这种文风,他后来一系列学术著作更是“阐释之循环”的系统展现。一九九二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隆溪的英文专著,题为The 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后有中文与韩文译本,中文本为《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这本书可以说多年来在世界范围里,对东西方比较文学颇有影响。该书绝不是机械地套用德国阐释学来解释中国文学,而是把阐释理论还原到它所以产生的基本问题和背景,即深入到语言和解释之间的关系中去,看看西方批评传统和中国古典诗学是怎样理解这种关系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为西方读者和学者引入一种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阐释角度;另一方面,通过把卷帙浩繁的中国哲学、诗歌、批评著作中零散的洞见和说法汇集在一起,也有助于使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理解变得更有系统。⑤张隆溪:《道与逻各斯》,第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张隆溪富有创见的东西方文学阐释学至少有如下方面的积极意义:避免长期以来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分割,尤其有可能避免文化研究中的种族优越论,避免把一种文化中的价值和概念强加给另一种文化的不良做法,也避免把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随意拼凑在一处,做一些牵强附会、肤浅浮泛的比较。全书的中西资料都很有逻辑地层层推进,组织在一种批判的跨文化对话之中。尽管中西文学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通过把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文本和思想聚在一起,就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被理解为彼此相通的共同基础,并从中西文学与文论的阐释与比较过程中,逐渐理出中国诗学的一条一以贯之的阐释学思路。当然,这样富有开拓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不易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隆溪高屋建瓴、囊括四海的学术胸襟与视野,更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纵横东西、跨越学科的深厚学术功力。全书主要有四个部分:对书写文字的贬责;哲学家·神秘主义者·诗人;无言之用;作者·文本·读者。每个部分都由可以单独发表的篇章构成,但通读全书,就会发现这些貌散而神不散的篇章都指向书的主旨——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每一篇章都从东西典籍中披沙拣金、旁征博引并娓娓道来,例证皆实实在在,如讲“道”与“逻各斯”的中西起源,其中批判德里达依据费诺罗莎和庞德对中文不准确的理解,将东西方语言文化对立,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乃西方独有的错误观点。同样,中国诗文与绘画讲究简约意蕴,强调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我们不能一言蔽之以为吾国独有,西方文学亦有如此传统,从《圣经》到哪怕是以叙述见长的荷马史诗,也都有简练描写的片断。不仅陶渊明和中国诗文传统,而且西方的诗人和作家如莎士比亚、T.S.艾略特、里尔克、马拉美等,也都深知如何运用语言之比喻和象征的力量,以超越语言本身达意能力的局限。这些好篇章段落在全书俯拾即是,美不胜收。该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赞扬,后被译为韩文和中文。
近年来张隆溪将他的阐释学理论与研究深入到中西经典的对读中,他二○○五年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Allegoresis: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讽寓解释:论东西方经典的阅读》)又是东西跨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所谓“讽寓”,是指文本在字面意义之外,还深藏着另一层关于宇宙和人生的重要意义,即一个文本表面是一层意思,其真正的意义却是另外一层。讽寓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就是在作品字面之外找出另一层精神、道德、政治或宗教的非字面意义。例如,《圣经》中的《雅歌》,从字面看这是一首艳丽的情诗,语言中有许多描写少女身体之美和欲望之强烈的意象,通篇无一字道及上帝。教父们为了维护宗教经典的地位,用讽寓解释的办法,说《雅歌》并非表现男女之爱,而是讲上帝与以色列之爱,或上帝与教会之爱,具有宗教的精神意义。在中国,《诗经》的评注也有许多类似情形,如以《关雎》为美“后妃之德”,《静女》为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等,把诗之义都说成是美刺讽谏,成为一种超出字面意义的讽寓解释。②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第60、6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这种讽寓解释一方面使类似《雅歌》、《诗经》等许多情歌得以保存下来,但另一方面不顾文本字面意义,甚至强加外在意义,亦会导致牵强附会的“过度解释”。张隆溪在这本颇有分量的著作里广泛涉猎东西经典,从宗教、道德、政治等角度解释文学作品的相关问题,按主题展开比较,探讨东西方文本与评注传统,相互对照,超越东西语言与文化的局限,以栩栩如生的大量例证来说明东西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和意义。③Zhang Longxi,Allegoresis: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1.
诚如前面所论及的,张隆溪早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同佛克马、钱锺书谈过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弗莱的原型批评在不同的文学作品里寻求表面差异之下一些最根本的意象。弗莱的博识与开阔视野在当代西方批评界应该说富有开创意义,但他基本上仍局限在西方文学的范围,因他不通东方。张隆溪从弗莱这里得到启发,同时打通东西,在主题比较方面来考察中西文学传统在意象、构思、主题、表现方式等各方面的对应、交汇与契合。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作了四次亚历山大讲演,内容集成一本专著,题为《异曲同工:跨文化阅读启示》(Unexpected Affinities:Reading across Cultures),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二○○七年出版,又是另一本具有标志意义的主题比较的佳作。该书以一些基本的概念性比喻和意象,如人生如行旅的比喻、珍珠的比喻、药与毒的象征、圆形和反复的意象,等等,举证中西文学、哲学、宗教的文本,论证东西方跨文化比较的价值。①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第6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负大翼也无力。”荀子曰:“真积力久则入。”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学问道德如水,积之厚,方能不舍昼夜、放乎四海;如风,积之厚,方能负鲲鹏展翅高飞、纵横万里。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昆仑钱锺书虽已逝去,但他的学术思想与精神不竭之源泉,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学人奋进。张隆溪的学问之道师承钱锺书,并发扬光大,为我们在跨东西文化的研究树立又一楷模,而今他步入花甲之年,但他的学术生命如充满活力的青年,正奋马扬鞭,疾驰朝前,我们衷心祝愿他生命之树长青。
二○一二年一月一日写于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
蒋洪新,湖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