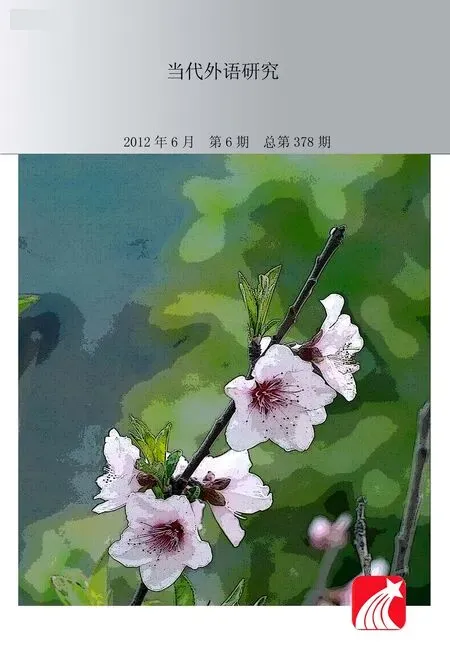哲学与翻译①
2012-04-01罗斯玛丽阿罗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罗斯玛丽·阿罗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著
梁真惠(北京师范大学)译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实践提出的哲学问题都鲜有人关注。实际上,直到近期,哲学思潮和翻译研究的关系显然也是失衡的:翻译家或者是翻译理论家对哲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哲学家对翻译问题的思考(Pym 2007:25)。直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当代西方哲学越来越意识到哲学和翻译之间无法回避的联系时,这种动态关系才得以改变。有人说翻译对当代哲学思想不仅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到了“着迷”的程度,因为当代西方哲学提供了一种“观念”,由此展开了“哲学可能性(如果不是实际发生的话)问题的讨论”(Benjamin 1989:9)
哲学的可能性问题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语言观和翻译观密不可分。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尼采之后最有影响力、最活跃的哲学思潮之一)思考的就是哲学与语言以及翻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哲学要为自身保留一席之地,即保留系统探索真理的特权,就不得不承认“单一明确意义”(univocal meanings)存在的可能性。这个单一明确的意义能够摆脱任何一种语言的限制,在语言之间穿梭时始终保持不变。那么,相信可译性的存在也必然意味着坚信翻译是“意义或真理在语言之间的传输(transportation)”(Derrida 1988:140)。
1.翻译即意义的传输:本质主义翻译观
影响深远的本质主义翻译观完全植根于西方形而上学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根本假设,即形式与内容(或语言与思想、所指与能指、语词与意义等二元对立概念)不仅是可以分离的,而且是相互独立的。语言被视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传达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意义。语言的作用就是外衣,保护着它所携带的意义,从而使意义能够被安全地送到这里或那里。
上述观念的基本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哲学传统那里。苏格拉底在《克拉底鲁》(Cratylus)中这样推理事物的本质:既然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等地属于所有的人,也不可能总是属于所有的人”,那么它们一定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并且“有它们自身的特性和一成不变的本质”(Hamilton & Cairns 1961:424-425)。这样一来,如果“事物不受主体的影响”,如果“名称本质上含有一个(永恒的)真理”,这个永恒真理代表它们所指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真理”的确能够超越任何一种语言系统的形式束缚,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以完美地复制出来,哪怕是语词或者语境,甚至语言发生了变化(译者按:这就是柏拉图‘绝对存在’观念的由来)。
主体(人)与客体(事物)可以分离,意义与语词可以分离,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翻译就是一种非人称(impersonal)的转移,即本质意义在语言之间的游走。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抗拒或谴责译者的干涉作用。实际上,对译者这个中介人(agency)的拒斥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传统翻译理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般来说,这些规定性的传统理论旨在维护译者与作者、译文与原文之间壁垒森严的界线。
本质主义翻译观也存在其伦理依据,人们常常用外衣这个比喻来阐释它。语词是外衣,用以保护意义这个裸体,并赋予它风格。译者不允许去触摸文本的意义裸体,只需要小心改变包裹它的外衣。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译者的任务就是机械地服侍,对原文抱一种敬畏的态度,不能越雷池一步(Van Wyke 2010)。本质主义翻译观拒绝接受译者的创造性角色,摒弃译文的政治性作用,否认翻译对身份构建和文化构建的影响,并且秉持古老的偏见:与创作相比,翻译是一种次要的衍生形式。这种观念把译者视为一个无所作为的隐形者,从而大大降低了译者地位。
2.翻译即操控与变形:后尼采主义模式
德里达明确指出翻译与哲学之间的亲密关系,他的思想来源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尼采最先把哲学任务和对语言的批判性反思联系起来”(Foucault 1973:305)。尼采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成为当代各种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潮(anti-foundationlist trends)的桥头堡,比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哲学等等,开辟了质疑探询的新道路,如女性主义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
1873年尼采在《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一文中概括了实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语言观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语言毫无疑问是人创造的,没有任何本质意义和概念能够与包裹它的语言纤维清晰地分离,因而意义和概念无法被完整地传输。语言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概念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它必然是人创造的,是“来源于不相等事物的等式”(译者按:从并不相同的现实事物中概括出一个共同的等式即概念)。这个结论可以如此证实: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在自然界中发现那片理想的“叶子”,也就是“叶子原型,其他所有的叶子不管是编织的、素描的、涂彩的、卷曲的,还是油画的,都从这个原型而来”(1999:83),但我们仍然把它当作一个概念来使用。简而言之,语言之所以起作用就在于约定俗成的力量引导我们忘记那些差异,幻想着那个“相同”或“共同”的东西能够被我们复制出来。
概念和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由于建构它们的语境永远不可能相同,因此概念和意义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复制。每一片叶子都是不同的,不可能忠实地复制那个理想的原型叶子,因为原型叶子只存在于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同样,每一个文本的复制都不可能是那个所谓原文的完整意义,而是建构了另外一个不同的文本,这个文本携带了它(再次)成文时的历史印记和社会语境。这个建构出来的文本也许被接受,也许被拒绝,甚至可能被视为对原文的可靠复制。译文和原文这种对立关系的形成不可能独立于语境之外和我们的习惯思维之上,“而一定是建构出来的和普遍认可的”,因此“总要受到不断的修正”(Davis 2002:16)。
尼采对柏拉图思想进行批判,让我们认识到翻译不再是本质意义在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游移。就翻译概念而言,这种批判让“我们不得不用变形(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来代替它:即一种语言或文本对另一种语言或文本进行的操控和变形”(Derrida 1978:20)。这种批判产生了广泛影响,早期对这些影响进行阐释的有博格斯(Jorge Luis Borges)。他于1935年出版《〈一千零一夜〉的译者们》,把翻译看成是写作的一种合法形式。此外,他审查了19世纪《一千零一夜》的几种阿拉伯文本翻译,指出尽管译者明确声称其译文忠实于原文,但译本却历史性地证明他们对翻译的态度和观点。在这几种译文中,异化和归化并用,重新建构原文,凸显了译者的作用:译文成了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译者本人的兴趣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Borges 2004:94-108)。博格斯没有批评《一千零一夜》译者们的不忠实译法,反而肯定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建构作用,为我们揭开了今天已经成为翻译学研究领域重要论题的讨论序幕:翻译在文化建构和身份建构中的作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的不对称性;最重要的是译者的介入作用;以及翻译使“创作”的传统观念变得复杂化等问题。
作为原文和译文关系中不容忽视的创造性要素,“差异”(difference)已经成为当代各种哲学思潮的一个关键词汇,这或明或暗地揭示了后尼采哲学对翻译的影响。译者在翻译时不可避免地要做出种种选择,因此,在译入语允许的情况下对原文进行改写时,译者必然显形。这种深刻的洞察使翻译研究最终摆脱了两千多年来贬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作用的传统偏见(试比较Venuti 1995)。
3.人文学科的翻译转向
尼采对“生产意义的语言”进行了重新思考,阐释了真理和习惯思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真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不仅对当代哲学和翻译研究,而且对整个人文学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当今人们对语言的再次青睐以及语言对当代思想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已经模糊了不同学科(这些学科的目标都围绕着主体性和文化展开)之间的界限。
在这种语境下,翻译——被视为一种操控和变形——变得至关重要,不仅重新界定了文化被建构的种种方式以及文化间的相互联系,而且也重新界定了文化概念本身,即文化是翻译的一种形式(Bhabha 1994)。在比较文学领域,与翻译相关的论题正被用来重新构建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Apter 2006)。同样,翻译问题对于跨学科研究变得意义重大,它揭示了语言政策对殖民化的影响(试比较Rafael 1988)以及女性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试比较Simon 1996)。
语言和权力纠缠在一起,这种深刻的认识让我们日益关注自己是如何构建和关联异文化的,以及这种关联又是如何改变和重新界定本民族文化的。因此,对翻译——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还是翻译概念本身——的日益重视也昭示着对国际化和全球化问题的普遍关注。翻译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使专家学者们不仅提出了人文学科的“翻译转向”,而且实际上把人文学科干脆就称为“翻译研究”(Bachmann-Medick 2009:11)。
令人激动的是,当代哲学介入翻译研究开辟了翻译研究的各种新方向,也足以证明翻译已经摆脱传统的本质主义观念。这种介入给翻译学科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认识到译者的政治身份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也许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着力运用我们从当代哲学和翻译研究关系中获得的这种创建性洞见,开始对译者——包括笔译者和口译者——职业领域的研究。
附注:
① 原文2010年刊登于《翻译研究手册》(HandbookofTranslationStudies)第一卷第247页至251页上。作者Rosemary Arrojo教授书面授权梁真惠翻译发表该文。
Apter, Emily.2006.TheTranslationZone:ANewComparativeLiteratur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chmann-Medick, Doris.2009.Introduction: The translational turn [J].TranslationStudies2(1): 2-16.
Benjamin, Andrew.1989.TranslationandtheNatureofPhilosophy:ANewTheoryofWord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Bhabha, Homi K.1994.TheLocationofCulture[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Borges, Jorge Luis.2004.The translators of theThousandandOneNights(2ndedition) [A].In Lawrence Venuti (ed.).TheTranslationStudiesReader(Esther Allen trans.)[C].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94-108.
Davis, Kathleen.2001.DeconstructionandTranslation[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
Derrida, Jacques.1978.Positions(Alan Bass trans.)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rrida, Jacques.1988.TheEaroftheOther:Otobiography,Transference,Translation(Peggy Kamuf trans.) [M].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Foucault, M.1973.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M].New York: Vintage.
Hamilton, E.& H.Cairns.1961.TheCollectedDialoguesofPlato(Benjamin Jowett trans.) [M].Princeton: Princeton UP.
Nietzsche, Friedrich.1999.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 [A].In Daniel Breazeale (trans.& ed.)PhilosophyandTruth:SelectionsfromNietzsche’sNotebooksoftheEarly1870’s[C].New York & Amherst: Humanity Books.79-97.
Pym, Anthony.2007.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 [A].In Piotr Kuhiwczak & Karin Littau (eds.).ACompaniontoTranslationStudies[C].New York: Multilingual Matters.24-44.
Rafael, Vicente.1988.ContractingColonialism:TranslationandChristianConversioninTagalogSocietyunderEarlySpanishRule[M].Ithaca: Cornell UP.
Simon, Sherry.1996.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al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Van Wyke, Ben.2010.Imitating bodies, clothes: Refashioning the Western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A].In James St.Andre (ed.).ThinkingthroughTranslationwithMetaphors[C].Manchester: St.Jerome.17-46.
Venuti, Lawrence.1995.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