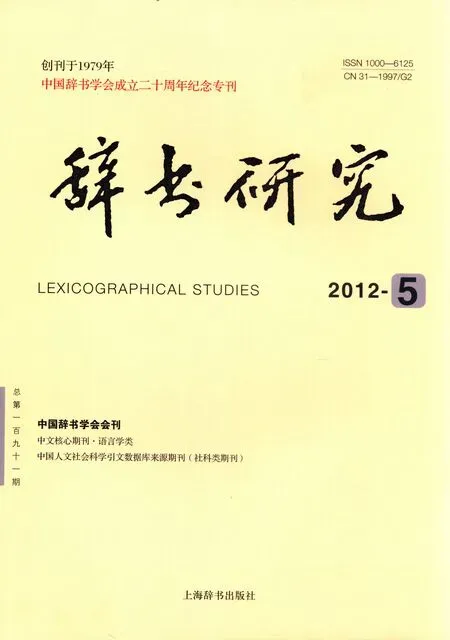胡明扬先生对我国词典学和辞书事业的重要贡献
2012-04-01孙德金
孙德金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明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在深切缅怀先生一生语言学贡献的时候,不能忘记先生除了在诸多研究领域(语言理论、社会语言学、汉语语法、近代汉语、方言、对外汉语教学等)做出突出贡献外,还曾在一方园地辛勤耕耘过,并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就是词典学及辞书事业。在这一领域,先生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1)词典学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2)辞书编纂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贡献;(3)辞书编纂实践方面的贡献。限于笔者学力,本文恐难全面评价先生在词典学领域的贡献,只能就目力所及的资料从上述三个方面谈谈认识,也借此机会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深切缅怀之情。
一、词典学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
(一)主持编写《词典学概论》
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持编写并通改的《词典学概论》(1982),是国内第一部词典学研究著作。该书与国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察了国内近几十年来(截至1979年)词典编纂的实际经验。内容包括单语语文词典的资料、选词、注音、释义,双语语文词典的资料和蓝本,词条的组织以及词典的体例、编排法等。因此,对我国的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纂工作有参考的作用。
关于这本书的编写缘起,先生在该书“前记”中说:“一九七八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语言学教研室的同志先后回到人民大学。我们鉴于近年来词典编纂工作正在全国蓬勃开展,而国内迄今还没有一部词典学著作可供参考,为此,计划编写一本《词典学概论》。”(胡明扬等1982)凡了解历史者都知道,那是国家刚刚结束“文革”、走出混乱局面的百废待兴的年代,先生就能把学术目光聚焦在词典学领域,要为我国的辞书理论建设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这无疑是一种富有学术担当的高尚品格的表现,也体现了先生在其一生的语言学事业中不断创新的精神。
先生近些年一直希望修订《词典学概论》,但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未能如愿,成为先生的一大遗憾。他临终前说:“(《词典学概论》)出版若干年后,商务印书馆的张万起先生曾与我讨论过修订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至今遗憾。”(胡明扬2011a)至于先生说的“种种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国度人人痛恨又感无奈的“谋人内耗”。许多人不清楚《词典学概论》为什么是五个人署名,而不是“胡明扬主编”。先生生前和我谈过,当年先生提出编写《词典学概论》的计划后,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在全系明确宣布“这本书由语言学教研室主任胡明扬担任主编”,但后来由于作者间有不同意见,先生为了“成事”,把书写出来顺利出版,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共同署名的方案。试想,如果当年先生不是顾全大局,着眼团结做事,纠缠于“主编”的名分,很可能就没有这样一部对辞书事业有重要贡献的《词典学概论》了。但也正因此,后来的修订工作未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辞书事业的一大损失。
(二)提出词典编纂的一些重要原则
1.强调语料
先生在语言研究中非常强调一切从语言材料出发,反对“空对空”。在辞书编纂实践方面,先生更是十分重视语言材料。先生在总结吕叔湘对词典编纂事业的贡献时指出:“从原始语料出发,而不靠编辑凭自己的脑袋去冥想苦想,这可以说是词典编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吕先生开了一个好头,遗憾的是后人并没有都继承这种优良作风,遵守现代词典编纂的这一经典准则。一个人的学问再好,知识面再宽,记忆力再强,也是有限的,没有语料,凭个人拍脑袋,怎么都比不过白纸黑字的语料。……有了语料,例句就比较可靠,义项也不至于遗漏,释义也不至于太离谱。这也是语料的价值。”(胡明扬2004a)先生1993年在谈到规范词典的编写问题时也指出:“新编一部规范词典没有丰富的语料是不能想象的。凭编纂人员拍脑袋或冥思苦想去写词条是早已落伍并且很不科学的方法,结果会是灾难性的。……国家语委正在建立大型语料库,应该把语料库的建设工作和词典编纂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规范词典要充分利用语料库的语料,把词典的内容建立在足够数量的语料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保证词典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胡明扬1993)先生的上述主张无疑是十分确当的,理应尽早在我国语文辞书的编纂实践中加以实现。大家在分析包括《现代汉语词典》在内的一些语文辞书时常常会发现一些释义、标注等方面的问题,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对语料的占有和分析的不足。没有对大规模语料的调查和分析,词典编纂中的遗漏或偏误也就在所难免。
2.关于义项排序
义项排序是语文辞书编纂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理论上必须面对的问题。先生在担任《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顾问的过程中,因为曾因义项排序问题和词典主持者发生分歧,他不主张按照词义的演化过程来安排义项顺序。李行健在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具体谈了这件事:“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就是词条的义项要不要按词义引申脉络排列的问题。这本来是王力先生早年编‘理想的字典’时提出的主张,我们词典开编时又经过论证,词义按引申脉络排列也得到吕先生认可,没想到胡先生坚决反对。我仍坚持原来的做法和理念,争论得很激烈,胡先生甚至提出‘顾问我就不当了’。他的理由是这件事很难,担心我们做不好;现代汉语词典也无须这么做。”[1]最后这部词典仍然按照词义引申脉络排序,并没有接受先生的意见,但我想我能够理解先生这样主张的初衷,更倾向于赞同先生的主张。他之所以如此固执己见,很重要的原因是先生亲自做过“打”这个词的研究(见下文),深知义项引申问题之复杂、困难。某些词也许容易搞清楚义项引申的脉络,但要把所有词的义项引申脉络都搞清楚,恐怕很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务实地采取其他的排序原则。特别是对于一部中型的规范性语文词典,主要是满足大众语文生活需要,义项引申脉络并非词典使用者最关注的,按照义项的常用度排序或许是更切合实际的做法。这一点应该并且可以和《辞海》一类的大型语文辞书有所不同。因此我认为这恰恰是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表现。
3.关于收词
收词是词典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先生既坚持不同种类的词典应有不同的收词原则,同时又能够持客观公允的态度。比如在谈到《现代汉语词典》收方言词和文言词问题时,他说:“那么《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符合不符合一部规范词典的要求?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词典》当时这么做是做对了。”(胡明扬1996)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现代汉语的情况和西方国家语言的情况很不相同。真正的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是在50年代才开始的,即使是在今天,哪些是现代汉语的规范词语,哪些不是现代汉语的规范词语,如果不掺杂三分主观武断,是谁也说不清楚的。”(胡明扬 1996)这无疑是一种尊重客观现实的态度。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他的话里含有的一个意思是,《现代汉语词典》当时这么收词是对的,但就规范词典的性质来说,则未必是无可挑剔的,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未来的目标,把真正意义上的规范词典的实现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所以他说:“当然,现在来看,文言和方言词语可能收得多了一点,像‘纪纲(法度)’、‘圭臬(标准)’这样的文言词语也许可以不收,像‘趿拉板儿(没有帮而只有襻儿的木底鞋)’、‘倔巴(倔)’这样的方言词语收不收也可以商榷。”(胡明扬1996)这表明,先生基于规范词典的基本属性,认为必须坚持非全民性的、非规范的词语不收的基本原则,但同时又能够历史地看待问题,不超越现实地苛求《现代汉语词典》。此外,在讨论到新词语的收词时,他强调了两个原则:稳定性、全民性。对此或许有不同的主张,但反映了先生在这方面的思考。
4.关于注音
注音是语文词典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名从主人”原则提出了商榷意见:“最近在安徽听说六合的青年人不少已经不说lùhé而说liùhé,看来向普通话靠拢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人名、地名一律按普通话读音读恐怕也是大势所趋,所以‘名从主人’的原则值得重新考虑。”(胡明扬1996)这是基于对民族共同语和方言之间的共变关系的认识提出的重要主张。这一主张也通过先生的顾问工作落实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李行健在追忆文章中谈到:“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后的读音问题,一直有‘音从主人’还是按普通话音系改造的争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实际读音规范问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给‘拆烂污’注音时,就有注‘cālànwū’或‘chāilànwū’之争,经过两次讨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应按普通话给‘拆’注音,不应因吸收某个方言词打乱普通话音系,给‘拆’增加一个又音。但为了稳妥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听取胡先生意见后再敲定。我们专门请胡先生来指导讨论,他的意见很明确,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后读音就应按共同语音系标注,因为它的身份已经不是方言词,而是共同语的成员了。如方言中来的词按方音标注,必然会打乱共同语的语音系统。于是我们决定,《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拆烂污’标‘chāilànwū’,不标‘cālànwū’。又如‘哟、唷’的注音问题,一般词典注‘yō’,我们认为不妥,因为既为推广普通话的规范型词典,就不能按方音注音,而应按普通话注音。普通话音系中y和o不相拼,也就是说普通话音系中没有这个音节。但具体怎么注音,还是找词典顾问胡先生请教。胡先生对普通话很有研究,先生说‘哟、唷’不应注‘yō’,应按北京人读音,重读时注‘yāo’,轻读注‘yōu’。这同我们的想法和调查北京人读音的结果完全一致。于是就不管别的词典怎么注音,我们决定不能标注‘yō’,而改注‘yāo’和‘yōu’。这些都是胡先生为提高词典的规范性做出的贡献!”[2]
5.关于标注词性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年第1版开始标注词性,《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也标注了词性。但在是否给非词(语素)标注词性问题上,二者处理不同,前者在第1版中给语素标注了词性,后者只给词标注词性。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明确的主张。程荣回忆说:“我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去胡先生家请教,或是通过电话就某些疑难问题听取胡先生的意见,其中较多的是关于现代汉语辞书中的词类标注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社会上对汉语辞书加标词性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此项工作涉及的问题较多、较复杂,胡先生不赞成给非成词语素加标词性,并提醒标注词性不能忘记释义的概括性原则,要防止随文释义、把义项划分得过于琐碎。”[3]然而不知道作为顾问的胡先生关于词性标注的意见没被采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1版给非成词语素标注了词性,由此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笔者从词性标注的目的性角度认为:“词性标注的前提是要承认有词的存在。‘词性’是词的句法属性。只有承认一种语言有词存在,才谈得上标注词性的问题,所以词性标注的基本原则是只能给词标词性。”[4]我们看到,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2010修订后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都执行了只给词标注词性的原则。
(三)在有关“规范词典”的论争中提出客观公允的意见
随着2004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问世,一段时间里出现了辞书界众所周知的关于“规范词典”的论争。各方火气都很大,以各种方式展开了论战,其中也不免有些过激的言行。胡先生和论争的各方都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到语言学界(具体到语文辞书界)团结的大问题,这对先生来说确实是个难题。现在看来,先生完全站在学术的立场上,通过对“规范词典”类型的划分和解读,为各方能够心平气和地化解纷争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早在1993年,先生就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从规范词典的性质、收词、注音、释义、词性标注等八个方面发表了重要的意见(胡明扬1993)。1998年先生再次就规范字典和规范词典问题发表意见(胡明扬1998)。面对上述棘手的问题,先生通过对词典史的回顾指出:“尽管《现汉》并没有标明是‘规范词典’,《约翰逊博士词典》、《简明牛津现代英语词典》也没有标明‘规范词典’的字样,但谁都承认这几部词典是规范词典。因为这几部词典的共同点是词典编纂者个人或集体经过研究,确定和推广赢得了广大群众认可的语言文字规范。这是一类原创性的规范词典,有关的规范也是词典的编纂者确定下来的,当然必然要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才能推行。还有一类规范词典,编纂宗旨是以推广已有的语言文字规范为己任,这类词典往往标明‘规范词典’字样,意思是关于某种语言的规范的词典。‘规范’不是修饰词典本身的,而指的是词典收录和推广的是有关语言的词音、词形、词义等方面的规范。”(胡明扬2004b)正由于先生能够从学理出发,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这样一桩学界“公案”,所论持之有据,以理服人,所以能够赢得各相关方的认可和接受,为促进学界的团结做出了贡献。
二、辞书编纂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词典班,先生主其事,为这个班的组织和教学殚精竭虑,培养了包括冷玉龙(现任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等在内的一批辞书事业骨干人才。在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冷玉龙说道:“胡先生和谢自立、梁式中等先生先后邀请王力、杨伯峻、姜亮夫、陈原、吴小如、曹先擢、许嘉璐等知名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培养了出版界和辞书界的一批力量,自己就是当时词典班的一员,有幸成了胡明扬先生的学生。胡明扬先生在中国辞书史上是不能忘记的人。如果要写中国辞书史,请不要忘记他和同仁谢自立、梁式中等先生编写出版的我国第一部词典学专著《词典学概论》,也不要忘记他们为中国辞书事业培养人才而开办的人大词典班。”[5]
除此之外,先生还以其他方式指导、鼓励、培养辞书编纂人才。先生指导了不少辞书的编纂,并作序。[6]在此仅举一例。先生特别为彭泽润等主编的《中国当代语言学学者词典》写了序言,他说:“陈建初、吴泽顺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学学者大辞典》(岳麓书社,1997年)是一本朴实无华,信息量特别大,非常有用的工具书。现在彭泽润等主编《中国当代语言学学者词典》,是继承和发展这个好传统,值得提倡和推荐。”在给彭泽润的信中先生说道:“你编写的人名词典好处就是不限于少数人,而是可以包含讲师以上多数发表过文章的语言学者,查找很方便。我始终觉得这两条标准很民主:(1)讲师以上,(2)发表过语言学论文。也许只要后面一条更加民主,有的发表了不少论文还是农民。”[7]在非语文类辞书的收条原则上先生能够强调“民主”,这突出反映了先生可贵的人文精神。[8]
三、辞书编纂实践方面的贡献
先生在语文辞书和其他类型辞书的编纂实践中都曾留下过耕耘的足迹。
语文辞书方面,虽然先生没有亲自主编过语文辞书,但实际上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做的“打”的研究就是一次语文辞书编纂的实践活动。先生在1984年《说“打”》一文的“前记”中说:“1962年至1964年间,为了摸一下词汇研究,也因为当时有的单位计划要编纂一部汉语历史词典,想试写一条词条,选择了‘打’这么一个常用词进行了一番摸索。……当时这篇稿子没有最后定稿,但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并已经过初步整理,对词汇研究和词典编纂工作或有可供参考之处,这恐怕就是唯一的价值吧。”(胡明扬2011b:172)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经历对于先生在词典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先生主持编写过《中外名诗赏析大典》。在谈到先生主编该辞典时,冷玉龙回忆了一件事:“先生是主编,我是责任编辑。在审稿过程中,我们免不了就书稿问题通信。记得一次在信里我谈到个别书稿引录原诗有误的问题。先生很重视,为此专门开了一次编写人员会,会上念了我给他写的信,严肃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所有作者把自己引用的诗根据权威版本再核对一遍。一百多万字的书稿,编写人员硬是全部重新核对了一遍。由于严把质量关,编纂有特色,此书出版后社会反响不错,后被评为四川省优秀图书。”[9]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却充分反映出先生严谨、科学的态度。正因为他能够充分认识到“典”的特殊意义,才会在辞书实践中抱持着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这种精神是需要很好地发扬光大的。
更为重要的是,先生通过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汉语大字典》等多种辞书的顾问、审订专家等学术职务,为我国辞书编纂实践做着或宏观(包括编写原则等)或微观(包括一个词条的收立、一个义项的设立与解释等等)的重要贡献。
谈到先生在审稿方面的贡献,冷玉龙回忆了一段往事:“作为审订专家,胡先生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审稿工作,为了不耽误出书时间,许多时候先生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审稿。他审读得很仔细,字斟句酌,大小问题都不轻易放过,为提高书稿质量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如‘啿’字第二个义项,原释义为‘吃’,引例是《唐语林·德行》:‘肃宗举饼啿之,上大悦。’此处释义举例都没问题。‘肃宗举饼啿之’,‘啿’就是‘吃’的意思,义例吻合,无可挑剔,但先生在‘吃’字前添加了一个‘啖’字。收到稿件后,我仔细琢磨,此字加得实在太妙!尽管原释义从准确性的角度来讲并无问题,但它没有揭示与被释字在语音和通行字使用上的关系,添一‘啖’字,则脉络清楚,关系昭然。这不是是与非,而是优与劣的问题,添加此字,可谓精益求精,锦上添花。《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此处采用的正是先生的审稿成果。”[10]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先生也曾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先生在充分肯定《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后以“裁决”为例,指出“经过考虑,做出决定”的释义“不很全面”。他认为:“至少缺少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裁决’必须是权威机构或权威人士做出的决定,一个是‘裁决’必须是对有争议的问题做出的决定,至于是否‘经过考虑’倒是不重要的。”(胡明扬1996)显然,先生指出的这两点是“裁决”一词具有的关键性语义要素,可供相关语文词典编纂时参考。
四、先生何以有此重要贡献?
先生之所以对词典编纂理论和实践有比较多的思考,做出以上诸方面的重要贡献,概括说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古今、中外兼通的通才素养
先生从小接受私塾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对古典文学,先生有特殊的喜好,他说:“虽然我没有系统学过《说文解字》、《尔雅》等古籍,但是我对中国古典的东西非常有兴趣,这可能与我爱好古典文学有关。”(胡明扬2011a)正因为先生在古文方面具有深厚的基础,因此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敏锐的眼光。比如前文冷玉龙提到的审读《汉语大字典》时的精彩处理,如果没有这种素养,是不可能做到的。
先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会学校),专业是英美文学,自然英语水平很高,晚年还曾在《世界汉语教学》等刊物上发表过直接用英语写作的论文。此外,他还在法语、德语、俄语等方面有良好的造诣。这些外语方面的优势使他具有了广阔的视野,可以方便地获取国外的信息、资料等,掌握第一手的学术资源。比如他之所以率先提出编写《词典学概论》这部著作,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先生在谈到《词典学概论》编写经过时说:“虽然没有编过辞典,但是联合国辞典学家编著的《词典学概论》(兹古斯塔1971年版)中译本是我校对的,也算是一点经验吧。”(胡明扬2011b)事实上这恐怕不只是“一点经验”,其实校对的同时也是学习词典学理论的过程。再以先生对语料库的重视为例,先生在1992年就对英语语料库的情况做了调查和介绍。(胡明扬1994)
先生晚年对我国的教育问题有深入的思考,认为国家要从根本上改变自1952年形成的过于专门化的教育模式,主张通才教育,这是切中要害的重要主张。先生自己就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通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通才”,因此才能在包括词典学在内的语言学多个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二)勤于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
先生一生在语言学领域贡献卓著,这与他的勤奋刻苦是分不开的。先生去世后林师母告诉我,“文革”结束后,先生为了抢回被耽误的时间,常常同时做四五个项目。《词典学概论》就是在那个时期先生同时做的诸多项目中的一个。[11]在谈到《词典学概论》编写过程时先生还说道:“我还仔细阅读了《简明英汉词典》、《简明牛津辞典》以及《法兰西学院词典》的前言部分,并且进行了翻译,这也是词典学的一部分。”(胡明扬2011b)虽然没有词典学的基础,但是先生凭着扎实的外语基础,以及可贵的学习精神,在词典学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这种精神一直贯穿于先生的整个学术历程,是我们需要继承并发扬的。
(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理念
在先生的语言学生涯中,无论是哪个领域,先生都十分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既反对照搬理论、空谈理论,也反对轻视理论。他在《词典学概论》(1982)“前记”中就说:“词典学理应兼顾理论和实践,我们正是努力这样去做的。针对国内目前的实际需要,我们在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同时更偏重实践。”这无疑是非常务实的。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给周荐的《词汇学词典学一得集》所作的“序”中,先生谈到:“1979年我带了《词典学概论》的初稿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的词典编写组去征求意见,事先没有想到的是各个词典编写组都反对插入词汇学这一章,认为词汇学对词典编写毫无用处。”(胡明扬2003)姑且不论词汇学和词典学的关系,这番话至少让我们了解到,先生在撰写《词典学概论》的过程中,绝不是像现在的一些理论著作那样闭门造车,而是主动地结合实践。
先生在辞书理论和实践中能够提出很多精到的主张,与他在实践中的亲力亲为有很大关系。前文谈到,先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写有《说“打”》一文,发表于1984年的《语言论集》第二辑。先生在去世前还说到这件事:“为了学词典学,我还做了一项十分具体的工作,在吕叔湘先生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试编了一个长条,那便是对‘打’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我搜集了6000多条关于‘打’的例子,梳理了从东汉到现代各个不同时代‘打’的意义,分成100多个义项,最终写成了《说‘打’》一文。”(胡明扬2011b)正如有人在追忆文章中评价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条汉语历史大词典的词条”。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扎扎实实的编纂实践(也是语言研究实践),先生无论是在词典理论上还是在编纂实践上才会有诸多令人信服的见解,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近些年来,先生还积极推动辞书理论研究。程荣在回忆中谈道:“胡先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应当认真总结《现汉》的编纂经验,原来写过的一些挺好,应当继续深入地做下去。他希望我配合他写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研究的专书,把所有优秀汉语辞书的编纂经验和方法都归纳进去,加以提升,启迪后人。然而由于胡先生年事已高,我调语言所之后,工作更加繁忙,此项研究一直未能启动。……2010年参加第6版审订工作会议时,他再次跟我谈起词典研究的重要性,并告诉我,关于出版词典研究专书的想法已跟商务印书馆谈妥,具体如何操作等《现汉》第6版完成后再具体商量。然而在半年前——2011年6月22日可敬的胡明扬先生却永远地离去了,留下的是那尚未开始的词典研究写作计划,成为世人永久的遗憾。”[12]先生去世前还告诉过我,上海辞书出版社要推出系列的辞书研究著作,要他为这套书作序。在第四届全国辞书理论与辞书史学术研讨会(芜湖,2012年4月)上,徐祖友老师向我介绍了此事的详情:“2011年5月,遵江蓝生先生推荐,我给胡先生打电话,请他为‘辞书研究文库’写序。胡先生欣然同意,只是说‘近来胃不舒服,等好一些就写’。没想到不久就听到了胡先生去世的噩耗。文库已出版的书上就只有曹先擢先生的序了,实为憾事。”
或许是因为在先生的心中,词典学、辞书事业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有份特殊的“情结”,当笔者2011年5月30日到病床前告诉他商务印书馆希望先生为《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增订本)写个序时,先生略做思考,口述了一份增订本序,其中主要谈的就是词典学。先生说完这番话后不到半个月(6月22日19时零3分)就离开了我们,带着他的诸般遗憾走了。斯人虽去,薪火未熄。先生在词典学、辞书事业方面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史册。
附 注
[1][2][3][4][5][9][10][12] 参见《胡明扬先生纪念文集》(即出)。
[6]如黄涛《袖珍分类成语词典》(知识出版社,1993),高进智《湖北常用方言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冷玉龙《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陈刚、宋孝才、张秀珍《现代北京口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97)等。
[7] 引自 http:∥www.yywzw.com/show.aspx?id=1435&cid=149&page=3。
[8]关于先生的人文精神,笔者曾撰文论述。详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学林”版之《学生眼中的胡明扬》。
[11]我知道的还有对北京话做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等。
1.胡明扬.英语用法调查语料库及其他英语语料库(附文:英语用法调查).国外语言学,1992(4).
2.胡明扬.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几点意见.语文建设,1993(4).
3.胡明扬.《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释义和注音.∥吕叔湘、胡绳等.《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胡明扬.规范字典和规范词典的重大社会作用.语文建设,1998(3).
5.胡明扬.《词汇学词典学一得集》序.汉语学习,2003(5).
6.胡明扬.吕叔湘先生对汉语词典编纂事业的重大贡献.∥人民网(www.people.com.cn)“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专题,2004a.
7.胡明扬.规范化和规范词典.语言文字应用,2004b(4).
8.胡明扬.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增订本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a.
9.胡明扬.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b.
10.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11.孙德金.略谈词性标注的目的性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