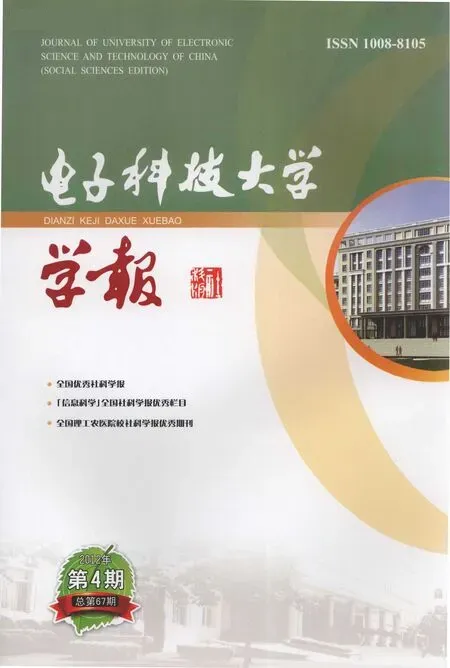中国社会管理创新路向思考:基于社会建构的思维方式
2012-03-28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224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2249]
中国社会管理创新路向思考:基于社会建构的思维方式
□李程伟[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2249]
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是达成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路径。本文从马克思社会系统论的角度,界定了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意涵及价值追求。论文概要分析了公共行政研究之社会建构途径的思维特质及学术意义,以为社会管理创新走向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启发。基于行政学社会建构的思维方式,论文从转换社会管理思维方式、构建城乡社区治理网络、推进重点环节制度创新、重塑基层社会服务机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向及政策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路向;社会建构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与之极不相称的是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经济与社会相脱节和失衡的问题十分严重,诸如贫困、失业、社会排斥、贫富差距、犯罪多发、家庭解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等问题,无不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的具体表现。这种现象在发展研究上被称为“扭曲发展”[1]4。当前中国发展扭曲程度之大,已经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产生了巨大威胁。尽管执政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管理这一命题的大的背景可以概括为多个方面,诸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公民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等等,但无可置疑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和脱节乃是其直接背景和现实依据。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关系上,前者偏于宏观聚焦,后者则偏于中观和微观聚焦,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乃是达成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路径。本文借鉴公共行政研究的社会建构途径,力求对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路向问题作一学理上的思考。
一、现代社会管理意涵与价值追求
研究社会管理的前提是明确“社会”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社会乃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要素或单元(即社会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系统)。这其中,个体的人(“社会存在物”意义上的个人)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基质。如果说社会是复杂的活生生的有机体,那么每一个现实的人就是它的一个细胞。是社会主体(个体的人及其各种组合形式)的各种功能活动分别构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这四大社会子系统或领域。维持社会系统良性运行和发展的前提,是使社会成员处于一定的福利状态和秩序状态,使关涉其具体生活及利益的问题和矛盾得到合理解决,使其基本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和机会得到满足和提供。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看来,前者(社会整体系统良性运行与发展的维持)就属于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它一般包括政治统治与管理、经济调节与管理、文化导引与管理和社会协调与管理这四大方面;而后者(社会成员一定福利状态与秩序状态的维持)则属于狭义上的社会管理。
展开来说,社会管理(狭义)实际上是指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单位和组织所进行的规范、约束、协调、服务等活动[2]。现代社会管理是控制与服务有机结合的过程,不仅是对社会成员一定行为的约束和控制,还是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对个体社会权利的保障和实现[3]。这与传统的专制社会不对社会成员承担福利(服务)责任,单一满足统治者的秩序诉求是根本不同的。可以说,“控制”和“服务”既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两个基本功能形态,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成员对现代社会管理的两大基本价值诉求,即“秩序”与“福利”。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达成社会成员的一定“福祉”或“福利”,亦即社会成员能够处于幸福、满足与富裕的状态。它又包括社会成员的“直接福利”和“间接福利”两个方面。其论证逻辑是:作为个人的社会成员是社会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他才能拥有个人自由,获得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下(再加上本人的努力),具体解决社会成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顿及问题(如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障其能够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这构成了他的直接福利。同时,作为社会成员各种关系组合的社会,也需要协调与管理,以保持其稳定、秩序和再生产。对于社会成员来说,社会关系的秩序及其再生产属于公共物品,它可以为全体成员提供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其能够无身份差别地从中受益,这构成了社会成员的间接福利。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追求。有国外学者从人文发展的角度,对社会福利所包含的三个要素进行了界定[1]16:1)社会问题(如犯罪、暴力、失业、环境污染等)得到控制的程度;2)主体需求(如健康、营养、安全饮用水、住所、社会保障等)得到满足的程度;3)社会机会(社会成员能力成长与境遇改善的机会)的创造或提供程度。这样一种界定和分析就为社会福利的测度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标准。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相对于政治统治与管理、经济调节与管理、文化导引与管理这三大管理领域,社会协调与管理对于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具有基础性的保障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对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紧迫性和现实针对性。
二、行政学社会建构的思维方式及其意义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行政学发展历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可简单地将其称之为行政学的“管理主义”、“功能主义”或“实证主义”。这是一类与牛顿科学哲学相契合的研究范式。但是,自1970年代以后,受相对论、混沌理论和量子力学等新物理学范式的影响,质疑或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不断出现,行政学的诠释理论、批判理论和非均衡理论日益发展,行政学研究的内容有不断加深和拓宽的现象[4]。在此背景下,韩裔美籍行政哲学家、海沃德加州大学的全钟燮(Jong S.Jun)吸收融合现象学、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等后现代哲学观点,提出了行政学的“社会建构研究途径”(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6年他出版了系统概括和阐释其社会建构研究途径的集大成著作——《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批判与解释》,从而在管理途径、政治途径、文化途径之外,又为行政学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途径或视角。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强调公共行政客观外在性的逻辑实证思维和强调主观内在性的社会建构思维始终存在,其不同比重的组合构成了行政学研究管理途径、政治途径、文化途径和社会建构途径的不同特色。下面拟结合相关文献,将行政学研究社会建构思维的特质概括如下:
第一,社会建构思维的起点是“主动-社会性”人性假设。社会建构思维对人性的假设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自我概念,而是与儒家“个人的道德自主性”相通,是一个与他人和世界相关的自我概念。在这一人性假设下,人是自主的而非被动的受控对象,他拥有追求公共利益或公共性的自主性,公共决策者有责任授能组织成员发展自主意识或自我管理,并促进对价值的共同理解。此即为“公共性的自主概念”。同时,自我也是“社会性建构”的,这就是主观互证的理性交往和相互调适的过程[4]44。
第二,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是社会建构思维的方法论基础。行政学的社会建构分析途径受物理学爱因斯坦范式的影响,在方法论上超越了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预设,而坚持行政“事实”的多元性、相对性和主观建构性。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认为任何“事实”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历史进程中被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种族等因素来型塑的,而每个人又是在具体的历史、地域、情景和个人经验中体验、感受到“事实”的。这种相对主义的取向使得它认为社会事实并非绝对的、凌驾一切的真理存在,相反,它主张在认识过程中,人们是经由主体间的互动、沟通和对话来获得彼此的理解,达成共同的观点[5]。同时,面对后现代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社会建构论认为单向度的思考难以把握复杂的行政世界,人们必须拒绝诸如个人对组织、艺术对科学、行政人员对公民、定性对定量等等的“行政现象的二元性”,而应充分发展辩证思考和批判反思的能力[4]46。
第三,社会设计模式是社会建构思维的政策主张。依据对“相关行动者的价值体认”与“冲突和问题的解决以及变革取向”这两个维度,全钟燮提出了公共行政与政策设计的四种模式:一是危机设计。这一类型的设计对他人的声音或价值的体认度低,而对冲突决议、问题解决和变革策略往往是被动的回应;二是理性设计。这一类型的设计是理性的经济模型,它假定公共行政依据科学的专业知识即有能力控制所有相关因素,而忽视公民的态度、经验和参与。它偏爱长期的和前瞻的目标建构,因而基本上是规范性的。三是渐进设计。这类设计重视他人的声音,但对冲突和问题的解决以及变革的回应则是被动的。其在行政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强调运用有效领导、政治技巧、持续沟通说服,以求相异观点的相互调适。四是社会设计。这类设计对相关行动者的价值高度体认,在组织与社会的关系(和行动情境)中强调诠释、理解、分享与学习,同时对于冲突与问题的解决、学习与变革等采取前瞻性的态度[5]66-74。在社会设计模式看来,行政管理的目的和目标是社会建构的,是从人类的互动、对话和相互学习中发展出来的。“发展促进互动和参与的过程是社会设计的本质属性。当行政管理者、专家、政治家、社会团体、顾客和因特殊议题和问题而联合起来的公民之间建立起社会互动和网络,可行的方案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时候,社会设计过程就被创造出来。”[5]75与前三类设计相比,这类设计最具开放性和包容性,饱含哲学和社会的思考,较能反应真实的行政世界。
第四,社会建构思维与公民治理的精神实质相契合。公民社会的存在是达成社会善治的基础,公民治理是民主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对此,全钟燮提出了“公民社会三角”(civil society triangle)的概念。在此概念下,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彼此互依,并持续转换各种关系,以协助发展可行的民主社会。这三角之一若太强或太弱,就有可能发生社会不公正、经济不平等、贪腐和政治动荡。面对后现代愈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或企业越来越无法单独面对,这就需要培养公民意识,使之热心参与公共事务,而行政人员则有道德责任去促进共享价值的理解,以公共理性与经济理性、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弥补,促进民主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基础[4]46。在社会建构思维中,公民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合作生产者,而非仅仅是科层体制下权力驱使的被动受命者,或受企业组织金钱诱惑的利益追逐者。公民社会乃是公民集体行动的场域,公民治理乃是公民社会具体的运行机制,公民社会和公民治理的精神实质与行政学的社会建构思维是紧密契合的。
三、社会管理创新路向审视
缘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脱节、权贵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已呈现出大范围的失衡、失序和冲突的景象,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尽管朝野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政治民主才是社会秩序可持续再生产的机制,但由于政治转轨的风险及其不确定性要远比经济转轨复杂,于是理性的决策考量便是加强和完善社会控制与服务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简单再生产。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思维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社会秩序简单再生产的局面恐怕也难以维持。出于对当下社会形势的上述判断,本文拟借鉴公共行政研究的社会建构思维,对中国社会管理创新路向及对策建议作如下思考:
第一,转换社会管理思维方式。归纳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社会管理的不同认知,大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倾向:一种是强调“自上而下”的以行政为中心的运作逻辑,倚重行政强制力量的作用,注重社会秩序的价值优先性;另一种是强调“自下而上”的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公民为本位的运作逻辑,倚重公共治理网络的作用,强调社会福祉的价值优先性。前者基本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认同社会管理规律相对于各类社会主体的客观外在性,以及社会秩序生成的外力作用机制,其在实务界较为普遍;而后者则认同社会管理的主体互动和相互建构,强调秩序的内生性和自组织性,基本上属于行政学的社会建构思维,其在学术界则有较多的拥趸。本文的基本主张就是促使实务部门从决定论的逻辑实证思维转向主体论的社会建构思维。正如全钟燮所言,以技术-工具理性为支撑的传统行政,体现的是单向度管理、职业家支配、物化的官僚制、安抚公民以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特征。它只适应于一种稳定的环境,在高度复杂和快速变迁的社会里,其制度结构就丧失了回应和创新的能力[5]3-5。面对转型期不断涌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类管理思维显然于事无补,而且还会不断制造新的问题。例如,有些地方过于重视公安、司法、综治、信访等部门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高压维稳”作为行动取向,结果导致越“维稳”越“不稳”。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政府部门的警觉。
第二,构建城乡社区治理网络。从本原意义上讲,社会管理体现的是共同体横向维度上的互动关系,它是以共同体意志自治和行为自组织为特征的;如若涉及纵向维度上的权力关系,则属于政治控制和政治管理的范畴。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广大城乡建构各个利益相关者和行动主体密切互动的理性行动场域,通过网络化的治理方式,解决地域共同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重心。这实际上就是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问题。对于社区和社区治理,应当从国际学术界通行的规范意义上去理解,而不能实用主义地界定为城市居委会辖区及其活动。英国行政学者克拉克和斯图尔特(Michael Clarke和John Stewart)认为,广义的社区治理是指社区与国家和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互动方式,它并不排斥政府或国家的作用,但否认政府机构作为社区的唯一权力中心;其他公共组织、社团和私人机构在合作协商与公众认可的基础上,都可能成为社区的权力机构,涉及社区公共事务的各个机构和组织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资源交换关系;同时,无论政府机构还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都需要遵循或遵守相同的“善治”规则[6]。可以说,在政府部门指导、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建设社区公民论坛(如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会议、邻里会议、业主代表会议等形式),对社区治理与发展问题进行交互式辩论和交流,学习倾听、对话、尊重、宽容、相互体认、妥协和理性博弈,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资格,这对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推进重点环节制度创新。从目前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来看,属于公共政策系统“输出端”的事项比较多,如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公私伙伴关系、一门式办公、服务承诺制等,处于政策流程的“下游”;而对政策流程“上游”和政策系统“输入端”的创新,诸如基层治理、服务和社会政策运行中的利益表达、利益汇集、决策听证、政策质询与监督等,尚显稀少和粗疏。因此,加强政(界)学(界)合作,对社会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展开有次序的研究,研究透某一方面问题就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以推进社会管理的民主化,是十分必要的。例如,迄今中国尚未有一部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结社法》或《社团法》,而只有《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这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更无保障新闻和出版表达权利方面的法律,致使公民社会和公民治理长期处于生长羸弱和不确定状态,窒息了社会建设的活力和社会管理的生机。这种状况应竭力加以改变。再如,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民主议事、监督机制的建设,公民参与层次的提升,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诉求表达等改革议题,目前各地实践中形式性意义往往大于实质性意义,有忽悠和糊弄老百姓之嫌,也需要尽快加以改变。在这方面有关地方及其领导人的远见及魄力常常起着很突出的作用,有关方面或力量如能协同推进相关地方立法,其对社会管理、建设与发展将善莫大焉。
第四,重塑基层社会服务机制。从学术分析的角度可以把“管理”与“服务”分开,但在实践中二者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很难分开。一种行为从施动方的角度看可能是管理,从受动方的角度看可能也是服务,反之亦然。既然社会管理的重心在基层,那么在基层治理中施行“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就是正确的路向选择。从社会建构思维的角度看,创新基层社会服务机制也就是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为了把这一问题说清楚,需要在学理上将“社会服务”与“公共服务”稍加辨析。
一般说来,“社会服务”是指针对社会成员所发生的具体困难和问题而开展的帮助、扶助或支持等活动,例如针对灾民的心理危机干预和生活救助等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类活动具有人格化、行动指向的特定性和具体性等特点,是因人而异、因人的不同困难而不同的,服务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是同时完成的。而“公共服务”则具有非人格化、非排他性、受益人的非特定性等特点,例如市政设施就为所有人群提供同质性的服务。如果说公共服务着眼于整体人口福祉的提升(不具有身份的指向性和特定性),则社会服务一般聚焦较为微观的问题和项目,强调弱势人群具体需求的满足和困难问题的解决。后者显然需要在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治理网络中才能实现。就社会服务机制创新而言,应当充分顾及如下几个方面:1)社会服务界定或决策机制的下移。与私人服务的个体化和市场化决策机制不同,社会服务的决策是一种集体选择。但现在这种选择或界定的层面过高(往往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基层社区和利益相关人反倒没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在社会服务中,服务对象并不单纯是顾客,他们还是利益表达与评定的公民,同时也是服务的协作生产者,必须从这样“三位一体”的复合视角来看待社会服务决策参与机制的建设问题。2)社会服务资源的动员和催化。社会服务涉及多元主体和多种资源,除了政府资源,还有各类志愿者和社会财力、物力等。而社会资源是需要动员(这里不是行政动员的涵义)和激活的,资源动员机制的建设对于基层社会服务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方面好的经验及做法应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3)社会服务生产与传递组织的建设。具体生产和传递社会服务的是运作于基层的、各式各类的、功能性的服务组织。从国际经验来看,那些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民间组织是社会服务行动的主体。对此,党和政府应当有前瞻性的眼光,着力培养社会工作者人才,扶持和培育体制外服务组织,指导和帮助其加强能力建设,使之在社会服务中逐步担当重任。4)社会服务行动的组织与协调。围绕社会服务会存在各种各类的行动角色,为了使之有效和有序地开展活动,必要的组织协调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学生志愿者到社区开展社会服务就需要一定的信息引导、技能辅导和统筹协调,社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自治组织就应当在这方面发挥作用。5)社会服务监督评议机制的构建。在此方面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切实落实和保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与作用,使之能够代表和组织社区居民对各专业部门条线上的社会服务职能履行状况和服务质量等进行评议和监督,藉此将过去那种由街道及区职能派出机构考核评议社区的逻辑彻底颠倒回来,以确保基层社会服务之“公共性”的真正实现。
四、结语
执政党关于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命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和失衡的背景下提出的。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现代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建设与管理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课题与挑战。应当说,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是达致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但这种管理和创新必须是符合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形态的,即本文从马克思社会系统论所概括出的“秩序”和“福祉”的有机融合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包含性,“控制”功能和“服务”功能的辩证统一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优先性[7]。
本文以上述认识为起点而展开:1)在理论上,通过质疑主流行政学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将行政学最新发展之一的社会建构分析路径借鉴和引入到中国社会管理创新路向的思考之中,以求他山之石的攻玉之效。2)针对现实社会管理严重偏颇化的现象,主张由“自上而下”以行政为中心的管控逻辑转换到“自下而上”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公民为本位的治理逻辑,强调社会福祉相对于社会秩序的价值优先性。3)从本原的意义上,将社会管理所体现的共同体的横向互动关系,与政治控制和政治管理所体现的纵向权力关系相区分,主张在广大城乡应着力建构各个利益相关者和行动主体密切互动的理性行动场域(社区治理网络),切实实现社会管理重心下移。4)鉴于各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多数停留在公共政策系统“输出端”或曰政策流程的“下游”(如合同外包、公私伙伴关系、一门式办公、服务承诺制等),而对政策流程“上游”和政策系统“输入端”的创新(如利益表达、利益汇集、决策听证、政策质询与监督等)则实质性的努力不够,本文提出了推进重点环节制度创新的主张,并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5)从学理上区分了“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以此为基点具体分析了社会服务在界定或决策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源动员机制、服务递送机制和监督评议机制等方面的重塑策略,希冀为相关的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1]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苗正, 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
[2]何增科.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M].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4.
[3]何增科.中国社会管理改革路线图[M].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9: 46.
[4]吴琼恩.行政学[M].第四版.台北: 三民书局, 2011:序言
[5]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 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前言.
[6]高鉴国, 高泰姆·亚达马.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M]//田玉荣, 主编.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0.
[7]顾华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4(2): 58-68.
Thinking on the Innovation Direction of China’s Social Management:Based on the Thinking Way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LI Cheng-wei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Strengthening social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chieving a steady and harmony society.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ies of social system, defining the basic meaning and value of modern social management.It also analyzes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 research on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 and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Based on the thinking way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ways of China’s social management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direc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3
A
1008-8105(2012)04-0026-06
2012-05-19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结项成果(06BaKD0025).
李程伟(1965-)男,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编辑 范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