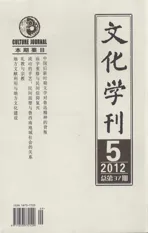庙宇重修与民间信仰复兴
2012-03-20吴世旭
吴世旭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庙宇是宗教建筑的统称,和所有的建筑一样,它并非仅仅是一个物质空间,而是涵纳了特定人、事、物的地方,不同的是,庙宇所涵纳的是与宗教活动紧密相关的人、事、物。虽然建筑的物质形式构成了庙宇的直观体现,但宗教的文化符号和气息才是其真正的特质所在,也就是说,庙宇在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宗教活动使人与超自然存在相互沟通的地方。所谓民间庙宇是指供奉民间信仰中特定神祇的庙宇,诸如土地庙、火神庙、关帝庙、观音庙等。民间庙宇是相对于制度性宗教中孔庙、佛寺、道观而言的,然而,杨庆堃所做的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之分在中国社会中并不明显,[1]明清以来尤其如此,很多民间庙宇供奉的神明虽然出自制度性宗教,但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民间化了,比如关帝庙和观音庙。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民间庙宇和其他中国传统建筑一样,在建筑材料上以土木为主,在建筑思想上则“不求原物长存”。[2]民间庙宇的建筑特征使其必然面对着周期性重修的问题,但是,除了物质特性之外,特定的信仰观念才是左右庙宇重修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民间庙宇的社会生命旺盛与否,取决于其间供奉的神祇是否灵验,这在帝国时代尤其明显。一座庙宇中的神祇越是灵验,就会吸引越多的信众,甚至得到官府的重视而获得加封,对其重修也因此而有更多的保障,很多著名民间庙宇的重修碑记对此都有所记述。可以说,庙宇是其所供奉的神祇灵验与否的一个判断标准,因为“祠庙对于神祇的作用,就像房屋对于人类一样,因此人们认为居住条件的好坏不仅影响着神祇的福气,还影响神祇的威灵”。[3]所以韩森(Valerie Hansen)认为在人神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关系,为神祇修建庙宇是为了使神祇更好地显灵。由此看来,一座庙宇的破败意味着其中的神祇不能持续地显灵,相反,不断得到重修的民间庙宇则意味着其中的神祇能够长期保持灵验。
民间庙宇的建筑特征与民众的信仰观念使灵验的民间庙宇周期性地得到重修,但是,除了自然毁损之外,民间庙宇在中国历史上也经常会因为兵燹之灾或政治运动而遭到毁损。民国以来,中国各地的民间庙宇便是因为诸如“反迷信”、“破四旧”等政治与社会运动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庙宇的重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上述民间灵验观念的一种延续,使这种延续成为可能的是民国以来摧毁民间庙宇背后的社会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所改观,与之相伴的是民间信仰的复兴。表面上来看,新时期的庙宇重修似乎是民间信仰复兴的直接后果,并因此成为后者的物质表征。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很多当代学者都把理论目光集中到民间信仰的复兴上。国内的文化工作者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迷信”的死灰复燃是由于新时期意识形态教育的松懈造成的,[4]美国汉学界比较常见的观点则认为,汉人社会中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传统文化与仪式的复兴是由于官方的策略性改造引起的。[5]这两种解释看似不同,实则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来看待问题,侧重于从国家政策的层面自上而下地审视民间信仰的复兴,从而忽视了民间信仰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王铭铭对此提出了批评,并认为民间传统的重建与民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民间信仰成为发展的象征资本而被加以改造。[6]以自下而上的眼光取代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解释民间信仰的复兴,提示我们民间信仰有其自身运行的逻辑,并且与政治、社会、经济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在承认官方政策直接造成了民间信仰“沉渣泛起”的前提下,如何以社会的整体观来省思社会变迁过程中民间信仰复兴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也就是说,民间信仰的复兴并非简单地与国家政策相关,而是与更根本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有着内在的关联。对这种关联关系的探讨,民间庙宇的重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能直接地体现民间信仰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因为民间庙宇重修伴随着不同文化因素和社会力量的延续与互动,由此成为推动民间信仰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国以来诸如“反迷信”、“破四旧”等社会思潮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策性 “包容”大体上呈现出一种官方主导下的历时性变化,这是当代民间庙宇重修的一个基本背景。但是,在传统中国,这两种官方态度却是共时性存在的,“封建政府对民间的宗教式活动采用的是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为了避免民间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发展,对民间的祭祀活动实行排斥的政策;另一方面,为了创造自己的象征并使之为民间接受,有时选择性地对民间象征加以提倡”。[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员认为对民间信仰活动加以规范化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从民间的角度来看,官方的规范并不一定会造成自身信仰活动空间的压缩,至少官方对特定神祇与庙宇加封遵循了“灵验”原则,而民间也是基于这一原则展开自己的信仰活动的,甚至可以借助官方的态度来扩大民间信仰的影响。民间庙宇及其神明越灵验越容易得到官方的加封,后者又反过来确证了前者的灵验,因此,受到加封的民间庙宇也会香火旺盛。
民间信仰在传统中国的生存环境,从民国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间信仰活动的空间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因为对新的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使民间信仰成为落后的象征,而这与民族国家的社会建设是不相匹配的。但是,民族国家对民间庙宇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与传统国家有着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把具有特定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民间庙宇视为文物,这与传统国家对民间庙宇的加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选择的标准已经不再是灵验与否了。尽管如此,民间庙宇在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浪潮中所拥有的生存空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那些在民间社会中有着广泛信众的神祇与庙宇已经随着一波波的“破除迷信”浪潮而销声匿迹;而从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地方到作为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文物,那些幸存下来的民间庙宇实际上已经不再与信众发生直接的联系了,其社会生命伴随着新的社会秩序的营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调整,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越来越多的民间庙宇也得到了重修,但是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较传统中国更为错综复杂的多重关系。一方面,传统国家中民间信仰活动的生存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很多社会与文化因素也参与了进来,从而使民间庙宇的重修在具备了可能条件的同时,又融入到了新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并因此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化面貌。
最为常见的是那些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祇与庙宇,比如村落中的土地庙。作为中国分布最广的庙宇,土地庙虽然体量很小,但却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具有保佑一个村落的风调雨顺的功能,而且是凝聚村落共同体的象征符号。土地庙在乡村生活中的象征意义与中国民间信仰的社会性紧密相关,武雅士(Arthur Wolf)认为汉人的民间信仰存在着一个神、鬼、祖先的象征体系,其社会根源则是中国农民的社会经历,表达的是农民对社会进行的分类,其中神是对向他们收税并规范他们行为的官员的隐喻表达。[8]尽管土地神在民间神明系统中地位最低,但却作为一村之主,象征性地掌管着一个村落的总体事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庙的重修是乡土社会由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向下弥漫造成绝对个体主义泛滥转向村落的共同体意识复苏的象征表达,而一座村落土地庙的重修通常需要全体村民的捐资,因此,村落土地庙的重修本身就是一个提升村落共同体凝聚力的过程。在乡村的民俗生活中,土地庙的仪式功能因地域的差异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是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得到恢复与加强的文化表达。在北方乡村的生活中,村民通常在年终岁尾之际到土地庙燃香祭拜以求来年五谷丰登,在葬礼中最重要的 “报庙”仪式则更明显地体现出了村落共同体的力量。
如果说诸如土地庙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庙宇的重修,是社会重建的象征表达,那么诸如观音庙等区域性庙宇的重修,则既有灵验遗产枯木逢春又有经济与文化等力量的因素。区域性庙宇超越村落而存在,它们因其供奉的神明的功能差异而在区域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于信众而言,这些庙宇是他们祈福禳灾、求神问卜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人们进入到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强,同时机遇与风险共存的社会环境之中,生活中逐渐增多的不确定性,则使人们重新对传统中国的灵验遗产产生了需求。以沈阳的观音寺为例,这座寺庙本来是乡村社会中的一个区域性庙宇,“文革”期间曾经遭到破坏,一度湮没无闻,后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进一步没落。20世纪90年代,一位企业家出资对观音寺进行了重修,并在原寺前加以扩建。该企业家在生活极度落魄的时候得到了一位高僧的点化,重新振作之后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选择观音寺加以重修扩建,并请来僧人主持庙务、接待香客,观音寺的香火因此逐渐旺盛。这位企业家的命运转折得益于高僧点化,当她把回报投入到观音寺的重修中时,其个人经历的传奇也渗入其中,不仅为当地人们祭拜观音提供了建筑场所,而且也赋予了这座庙宇以更多的灵验色彩。观音寺重修的经过与传统时代庙宇灵验的“故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说是对灵验传统的一种当代延续。
但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仅仅是民间庙宇重修的基本因素,而基层社会对发展的追求常常会借助这种因素,通过把曾被视为 “迷信”的民间信仰改造为民间文化而达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辽西的青岩寺为例,其中供奉的歪脖老母因其灵验而在东北享有盛誉,在传统时代香火极为旺盛,“文革”期间的“破四旧”使其遭受严重破坏,歪脖老母塑像也被推落山崖。1984年,一位村民将神像请回庙中,从而使祭拜歪脖老母的信仰活动逐渐得到恢复。当地政府认识到这是一个发展地方经济的契机,开拓出了一条以民间信仰活动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的祭拜活动被改造成了“祈福文化”,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文化资本,青岩寺也因此而得到了大规模的重修与扩建。经济力量对民间庙宇重修的渗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文化的力量,这与民间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紧密相关,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
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庙宇的重修虽然与民间信仰的复兴直接相关,但其深层的根源却是社会性的。从功能与象征的角度来看,民间庙宇本身便具有社会性,一方面,它为信众提供了一个人神交换沟通的场所,使不同角色的信众拥有了一个互动交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庙中供奉的神明则是对现实社会的结构关系的象征表达,并因其灵验与否而吸引大量的信众或无人问津。也就是说民间庙宇因为吸纳了特定的人、事、物而具有了社会生命,这种社会生命的延续与否取决于庙中所供神明灵验与否。民间庙宇的建筑特征与其社会生命的结合,使灵验的庙宇必然会经历不断的重修,以维持其社会性的功能与象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庙宇的重修,在根本上是由其社会生命所决定的,特定民间庙宇正是因为其中的神明在信众看来是灵验的,才获得了重修的基本要件,而因官方态度的改变造成的民间信仰复兴不过是为民间庙宇的重修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已,甚至得益于民间庙宇的重修。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民间庙宇不可避免地处于流动的历史进程之中,并面临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考验与冲击,从而使其社会性融入了更多的生命因子。不同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使民间庙宇的存在与延续如同人生的历程一样,在经历各种生活体验的同时被赋予了不同的生命色彩。在传统中国,官方对民间信仰的矛盾态度,使民间庙宇或者得到加封,其中的信仰活动因此而被列入祀典;或者沦落为淫祠,其中的信仰活动因此而不被官方认可。但不管怎样,政治力量渗入民间庙宇的社会生命之中是不言而喻的。民国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潮使民间庙宇的社会生命几近枯竭,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再度赋予了其生命的力量,而经济与文化因素的渗入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生命的本色,民间庙宇的信仰功能与象征相形之下得到弱化,经济功能与文化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强化。尽管如此,民间任然可以借助这个过程为民间信仰活动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庙宇的重修与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伴,但后者却并非是其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民间庙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命本色与变化才是其得到重修的深层原因所在,并通过庙宇重修反过来推动了民间信仰的复兴。
[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2.
[2]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韩森.变浅至深: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54.
[4]周英.封建迷信与群众文化[J].群众文化,1988,(1).
[5]Helen Siu.Recyciling tradition[A].Perry Link.Unofficial China[M].Westview Press,1989.
[6][7]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53.
[8]Arthur Wolf.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