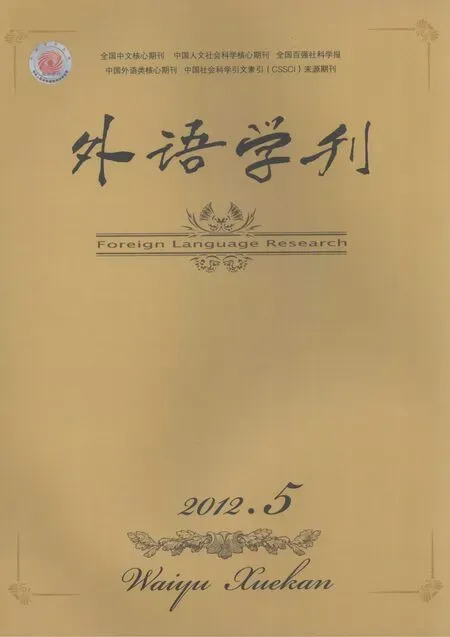从索绪尔的言语到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语言的在与是*
2012-03-19冯文敬
冯文敬
(蚌埠学院,蚌埠 233000)
〇引进与诠释
从索绪尔的言语到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语言的在与是*
冯文敬
(蚌埠学院,蚌埠 233000)
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建立在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上,但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对立在哈贝马斯的人与人的交往中已发展为一元统一,即语言与言语在人的交往中交织在一起,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与索绪尔一样,哈贝马斯的理论同样具有语言本体论思想。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可以揭示出,语言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本体;语言活动是人在自己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其本质是交往;语言本体的“在与是”通过语言交往过程实现,同样通过语言交往同人与人的世界相联系。
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本体论语言哲学;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二是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本体论语言哲学指“与分析性语言哲学对应,把语言视为在者/是者,探讨语言如何在如何是,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包括人生活的外在物理世界)的科学”(李洪儒 2011:3)。该学派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欧洲大陆的一些哲学流派,如结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普遍语用学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可以从新的角度阐释语言本体及其“如何在如何是”,阐释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1 语言与言语:二元对立还是一元统一
桑德拉·哈里斯认为,“普遍语用学理论都企图确立互动交往的根本和内在规则”(Harris 1995: 117)。如果从广义上说,语用学是语言使用的研究,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或形式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则寻求在必要的抽象层次上定义这些规则,排除不同主题、语境甚至文化。格莱斯的合作原则是普遍语用学的一种尝试,但却没有将其理论上升到社会和政治层面,而哈贝马斯将语言研究置于社会行为理论中,提供格莱斯所缺失的普遍语用学的社会和政治维度,将语言交往行为与社会现实的重要方面联系起来。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建立在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区分基础上。“语言是人类代代相传的符号系统,包括词法、句法和词汇。它潜存于特定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意识中,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社会性产物……言语则是说话人说出或者理解的全部具体内容。”(李洪儒 2010 :18)据此区分,索绪尔建议设立分别研究语言和言语的两门不同的语言学,前者是主要的,后者则是次要的。这种二元对立思想和二元对立范畴的区分成为索绪尔给后人留下的“疑难”(利科 1988:372-375)。哈贝马斯则认为,语言的形式语用研究与形式语义分析同样可能,而且同等重要。形式语用学的目标是要系统重建有能力主体的直觉性语言知识,有能力言说者对自己语言所拥有的直觉性规则意识(Habermas 1998:2)。哈贝马斯的思路与乔姆斯基有某些相似:“类似于乔姆斯基对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的区分”(Commings 2007:199)。言语行为理论对言语的要素单位(话语)主题化的态度类似于语言学对语言的单位(句子)主题化的态度。重建性语言分析的目标在于对这样一类规则的清晰描述:有能力言说者必须遵从这些规则,以便构造语法性句子,并用一种可接受的方式言说他们。言语行为理论与语言学共同担负这项任务。“语言学是从每一个成年言说者都拥有某种内在的重建性知识(其中,他的构造语句的语言学规则资质
普遍语用学认为,一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活动只能在下述条件下进行:参与者在其言语行为中使用可领会的句子时,需要通过某种可接受的方式同时提出3项有效性要求:(1)对一个被陈述的陈述性内容或被提及的陈述性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它要求真实性(validity claim of truth);(2)对规范(或价值)——在一个给定的关联域中,这些规范或价值将证明一个施行式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为正当——他要求正确性或适宜性(validity of rightness);(3)对被表达的意向,它要求真诚性(validity of truthfulness)。依据3个有效性要求,在对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分类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将言语行为划分为3个基本类型:记述式言语行为(constative speech act)、调节式言语行为(regulative speech act)和表现式言语行为(expressive speech act)。在此交往过程中,语法性句子通过普遍有效性要求被嵌入与现实的3种关系中,并由此承担卡尔·毕勒(Karl Buhler)在语言功能图式中提出的语言的3种语用学功能:呈示事实,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表达言说者自身的主体性。这样,语言就可以作为相互关联的3种世界的媒介物而被设想,即对每个成功的言语行为来讲,都存在下列3重关系:话语与(1)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2)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的人际关系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3)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在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交往者使用语言进入具体的语言交往过程,使人与人的外在物理世界、内在世界和社会世界联系起来。可见,虽然哈贝马斯在概念上仍然遵循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元区分,但在他的交往模型中,语言与言语已经统一为一个整体。
2 语言本体的本质:在与是
在古代和近代哲学中,语言只是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即语言的工具论思想。而在现代哲学中,语言被看成人的存在方式,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所谓本体论或存在论,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就是讨论to on hen on(所是之为所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陈嘉映 2003:37)。蒯因和卡尔纳普都主张我们有不同的语言系统,这些语言系统的本体论地位相同:“语言行为在性质上不同于草履虫对营养液的反应,除了在‘以言行事’这种特定的情况中,我们不是用语词对环境作出反应,而是在语词的层面上反应”(陈嘉映 2003:271)。借用比克顿的话说,语言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表征体系,而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手段或技巧。哈贝马斯提到,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继承的狄尔泰和胡塞尔的传统中,主体间性中达成的言语理解具有本体论的特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把理解看作是人类此在的基本特征;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中则认为,理解是历史生活的基本特征……我不想对这个观点展开系统的论述,但想肯定一点,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社会科学基础的方法论讨论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理解必须被看作不是一种特殊的对于社会世界、社会科学的记载方法,而是通过社会成员进行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人类社会的本体论条件”(哈贝马斯 2004:107)。哈贝马斯所构建的交往模型首先承认语言本体的存在,即语法性语句的存在,通过语言本体的使用,人与世界在交往中发生关联,“交往行为概念中所出现的是另外一个语言媒介前提,它所反映的是行为者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哈贝马斯 2004:94)。也就是说,语言成为独立存在的实在,不依附于任何实在,而是一种“处于人与世界之间,属于多元世界中的一元”(李洪儒 2008:2)。
3 语言活动的本质:交往——人在人的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哈贝马斯把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结构划分为认知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工具理性(teleological rationality)和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分别对应着3种语言使用样态:认知性应用、工具性应用和交往性应用。其中,语言的交往性应用依赖于交际情景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对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是语言应用的原初状态,其他社会行为,如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策略行为等,则是附属行为,“以沟通为取向的语言应用是一种原始形态,间接沟通(让人理解或迫使理解)处于寄生状态”(哈贝马斯 2004:275)。所以,以语言本体为中心的语言活动本质上由交往互动双方的交往行为组成,也就是说,语言本体的“如何在如何是”其实通过沟通行为(交往行为)实现。“沟通是人类语言的终极目的。语言与沟通之间的关系尽管不能比作手段与目的,但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使用交往命题的意义,我们也就可以对沟通作出解释。语言概念和沟通概念可以相互阐释。”(哈贝马斯 2004:275)可见,哈贝马斯反对语言工具论,语言这种本体并不是沟通交往的工具,而是与沟通(交往)互相阐释、不可分离。即语言活动的本质就是交往,是人在人的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因为没有语言交往,人就不成其为人。而语言意义的解释和理解都必须在主体间性的交往中实现,“意义理解与对物理对象的感知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它要求与表达的主体建立起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意义理解是一种交往经验,因而不能从唯我论角度加以贯彻。理解任何一种符号表达基本上都要求参与到一个沟通过程中去”(哈贝马斯 2004:112)。
温奇认为,所谓“语言”,就是语言构成的世界观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中蕴藏着文化知识,依靠文化知识,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又来分析各自的世界。每一种文化都用它的语言建立起与现实的联系。”(哈贝马斯 2004:57)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探讨语言自身问题时,如果不把生活世界概念纳入考虑范围,就不会真正解决问题,找到答案的原因。如前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成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独立存在的人与人的世界联系的媒介,言语者和听众在沟通过程中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其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语境。这样,与人相关的生活世界划分为3个部分: 客观世界(外在自然),意指成年主体能够(尽管仅仅是间接地)感知、能够操纵并在现实中客观化了的那一部分;社会世界,意味着成年主体可以在某种非遵从性态度中加以理解的——作为一个交往行为中的人、一个交往系统的参与者而理解的——现实中前符号化结构的那一部分,合法的人际关系就隶属于此,例如,制度、传统、文化价值等等;主观世界,即内在自然,是全部欲望、感觉、意向等等。关于内在自然,我们认为,哈贝马斯所说的“全部欲望、感觉、意向”在具体交往过程中是某个个人的,而上升到宏观层面应该是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内在世界,一种通过交往达成共识的主体间性的世界,并且与整个人类共同体组成的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紧密相连。可见,这3个世界都体现人的因素,或者可以说“人的世界”划分为3个世界。而人在人的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就是以沟通交往为本质的语言活动。通过语言交往,人与人的世界统一起来,“交往行为最终依赖的是具体的语境,而这些语境本身又是互动参与者的生活世界的片段。依靠维特根斯坦对背景知识的分析,生活世界概念可以成为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哈贝马斯 2004:266)。
4 语言本体的“如何在如何是”:语言交往过程
4.1 交往目标
哈贝马斯把语言交往的目标区分为达成一致(agreement)或共识(consensus)和达成理解(understanding)。只有当交际者能以同样的理由接受一个有效性时,交际参与者关于一个存在事实才能达成一致,以此为目标的交往行为称为强交往行为。而在一方交际者看到另一方交际者在给定语境中对于他所宣称的意图有好的理由,交际双方关于说话人意向的严肃性的相互理解就可达到,以此为目标的交往行为称为弱交往行为。
但有些交往行为并不是单一类型。如警察询问互动,是以达成理解为目标的弱交往行为,即警察关于被询问人意向的严肃性仅仅达成理解而非一致,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一致只有当警察与被询问人以同样的理由接受一个有效性时才能达到。而警察在单次询问过程中,互动双方只能就部分事实达成一致,要通过后续调查,才能最终确定整个事实,所以在调查期间,询问笔录中的“事实”的一部分真实性是悬置的,只能达成理解。所以,此时的交际目标在整体上是达成理解,而部分上就某些事实是达成一致或共识,即交际目标应该是一个从达成理解到达成一致或共识的连续体,即交际者期待的交际成功程度是一个连续体。而达成一致或共识应该进一步区分为达成弱共识(agreement or consensus in weak sense)和达成强共识(agreement or consensus in strong sense)。以达成弱共识为目标的是介于弱交往行为和强交往行为之间的交往行为,如警察询问互动。所以,弱共识也可称为一致理解(agreed understanding)。
4.2 语言交往过程
“语言是一个具有自己组成单位及其运作规则的特殊存在,其核心要素是创造、发展、运作(使用)语言本体的关键要素——人,包括说话人(speaker)、受话人(hearer)和他者(others)。”(李洪儒 2010:22)哈贝马斯的交往模型正是从说话人、受话人角度对语言本体的“如何在如何是”,即应用过程的全面阐释,但他没有把语言的运用过程(沟通过程)当作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传递信息的客观主义观念,而是面向“一种关于互动的形式语用学概念,这种互动发生在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并以沟通行为作为中介”(哈贝马斯 2004:263-264)。可见,这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互动模式。
同语用学其他交际模式如斯波伯与威尔森的明示-推理模式比较,哈贝马斯的交际模式对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字面意义如何从语言层面通过交际进入生活世界层面产生出最终说话人意义和听话人意义的微观推理过程语焉不详,但是哈贝马斯不仅关注听话人对说话人话语的理解问题,而且关注听话人对话语的反应:接受或拒绝有效性要求(交际成功或失败的深层原因),将语言交际上升到宏观社会规范层面。他对语言交往的描写从语言本身到实际交际过程都提出有效性要求,意义理解在交际双方(有时还有他者)的主体间性中实现,交往不是一个单向过程,而是双方不断提出、批判、论证有效性要求而最终达成理解或共识的动态过程,而此过程也正是语言本体“在与是”的实现过程。
5 结束语
从索绪尔的言语到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语言与言语在交往行为中得到统一。从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出发,可以阐释语言本体及其“如何在如何是”。也可以从新的角度阐释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本体;语言活动的本质是交往,人与人的世界通过语言交往联系起来,即语言活动是人在自我世界中的存在方式;语言本体“如何在、如何是”通过语言交往过程实现。语言与人同在。
陈嘉映. 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利 科. 哲学主要趋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李洪儒. 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研究——站在流派的交叉点上[D]. 黑龙江大学博士后工作报告, 2008.
李洪儒. 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J]. 外语学刊, 2010(6).
李洪儒.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J]. 外语学刊, 2011(6).
潘文国. 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J]. 外语学刊, 2008(2).
Habermas, J.OnthePragmaticsofCommunication[M]. 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8.
Commings, L.Pragmatics:AMultidisciplinaryPerspective[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Harris, S. Pragmatics and Power[J].JournalofPragmatics, 1995(23).
【责任编辑李洪儒】
FromSaussure’sParoletoHabermas’sCommunication:theBeingofLanguage
Feng Wen-jing
(Bengbu College, Bengbu 233000, China)
Habermas’s Universal Pragmatics is based on Saussure’s binary division between langue and parole, but Saussure’s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langue and parole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one unary unity, that is, langue and parole interwind and become an indivisible unity in the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of human beings. Just as Saussure, Habermas’s theory also has a feature of language ontology. Based on Habermas’s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we hold that language is a kind of independent beings, and linguistic activity, whose nature is communication, is the way of living of human beings in our world. Through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the being of language beings is realized, and human beings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with our world.
Habermas; Universal Pragmatics;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089
A
1000-0100(2012)05-0016-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主观意义研究”(10BYY099)和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整合性研究”(10JJD740004)的阶段性成果。
2012-03-31
编者按:目前,学术界受英语国家主流学者观念的影响,一般认为,语言哲学是广义分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包括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中用分析方法分析语言的部分。其实,这是误读。本刊有充分根据认为,语言哲学不仅应该包括分析性语言哲学,而且应该包括以语言为对象、以人及人的世界为学科目的的所有学说、学派。冯文敬和李会民的文章虽然短小,甚至难免简单之嫌,但是昭示我们:索绪尔、哈贝马斯和洪堡特等人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同样巨大,值得并且应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