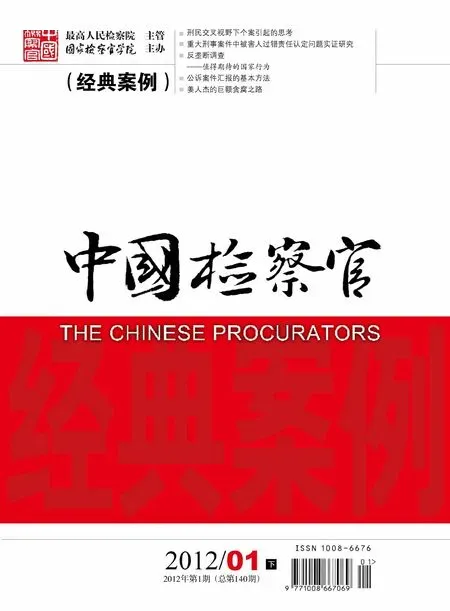论行贿罪构成要件之“不正当利益”
2012-01-29朱晓玉
文◎朱晓玉
论行贿罪构成要件之“不正当利益”
文◎朱晓玉*
本文案例启示:行贿罪“不正当利益”的界定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不确定利益说虽然暂时解决了实践中适用法律的困难,但未能从根源上剖析“不正当利益”在贿赂行为中的性质。行贿行为本身就具有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应作否定性评价,并应受刑罚惩罚,利益的正当与否可以作为量刑考量而不应作为定罪依据。
我国行贿构成犯罪涉及的罪名包括第164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389条行贿罪、第391条对单位行贿罪、第393条单位行贿罪。这四个行贿犯罪无一例外地都把 “为谋求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显然单纯行贿行为、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行贿的行为都不是犯罪,排除在刑法的规制范围之外。其中该要件主要涉及的罪名,就是第389条的行贿罪。如何界定“不正当利益”成为争议的焦点。
一、有关“不正当利益”界定的观点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手段不正当说。该说主张评判利益正当与否的着眼点在行为人实现利益的手段,即认为只要采取行贿手段谋取利益,都可以认定为“不正当利益”。而无需考虑利益本身是否合法。
2.非法利益说。该说强调认定“不正当利益”的唯一准则就是法律,认为只有国家明令禁止获取的利益才是不正当利益。[1]这种观点源于1985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解答》),其中规定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谋取“非法利益”。
3.不确定利益说。认为不正当利益包括两类:非法利益和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的不确定利益。不确定利益是指按照法律、法规、政策等规定,符合条件的任何人采取合法正当的手段都可能获得,但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2]
4.利益独立性说。该说认为“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只能从利益本身的性质角度进行考察,“不正当利益”除了非法利益外,还包括根据国家政策、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不应当取得的利益。[3]
5.受贿人是否违背职务说。该说认为“不正当利益”应从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否违背职务的要求加以限定。[4]
上述五种观点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都存在一些弊端。手段不正当说否定了利益本身的独立性,使“不正当利益”失去作为行贿罪构成要件的意义。非法利益说把行贿的打击面缩小,不符合社会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利益独立性说同样把打击面缩小,因为国家政策、国务院各部门规章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些未来得及制定法律法规的领域,采利益独立性说无疑会放纵犯罪。受贿人是否违背职务说最大的弊端,在于将行贿的对向犯的行为作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依据,有客观归罪的嫌疑。不确定利益说具有一些较为成熟的论证,认为“不正当利益”有两种类型:非法利益和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的“不确定利益”,后者包括利益的不确定性和手段的不正当性两个要件。[5]也是目前的通说以及实践中采用的观点,但是“手段”能否作为利益正当与否的一个判断标准,值得商榷。
二、“不正当利益”的相关司法解释及辨析
“两高”于1999年3月14日《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立案标准》)附则部分做出了与两高《通知》相同的解释。2008年11月20日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九条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根据《通知》和《立案标准》,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实际上指的就是非法利益;第二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实际指最终获取的利益本身符合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的规定,但行贿人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为其提供利益的手段却违反了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的规定,简言之,行贿人获取的利益合法,但受贿人帮助行贿人获取利益的手段是违法的。前者是利益本身非法,后者是谋取利益的手段违法,或称程序性不正当利益。[6]
可见,“不正当利益”是指非法利益或者受贿人通过职务上的违法行为,使行贿人获取的利益两种情况。《通知》和《立案标准》采纳了非法利益说和受贿人是否违背职务说两种学说。表面上看,该解释似乎解决了“不正当利益”的界定问题,却存在理论上解释不通,实践中操作困难的问题。首先,该司法解释有可能把受贿人的行为也纳入到行贿罪构成与否的考量中,从而导致客观归罪。譬如行贿人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采取违法行为为其谋取利益,如果行贿人所谋取的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采用非法手段和合法手段都可以为其谋得。此时行贿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受贿人,而不取决于行贿人本身,有客观归罪之嫌。其次,行贿人通过行贿获取非法利益在实践中日益趋少,现实中更常见的是行贿人利用受贿人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获取利益。例如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在审理一起合同争议案过程中,收受原告贿赂,做出终审判决,同时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案中,行贿人向主审法官行贿,目的是为了使判决向己方倾斜,但受贿人的职务行为无需采用非法手段。这种国家工作人员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在政府采购、税务、工商、行业管理等各种领域大量存在。
《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知》和《立案标准》的缺陷。一是非法利益范畴的扩大,这里的“法”不局限于国家政策、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谋取违反规章、政策的利益也属于不正当利益;二是进一步完善程序性不正当利益,要求违反规章、政策、行业规范谋取利益的也纳入到不正当利益的范畴。三是规定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也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招标投标、政府采购中为谋取竞争优势而行贿的,利用的便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但如前所述,这种自由裁量在各种领域大量存在,《意见》限定为商业活动,不利于打击其他领域此类行贿行为。
三、如何看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
无论是对“不正当利益”予以界定的五种学说还是相关司法解释,都不能尽善尽美地解决问题,这客观上导致了司法认定的困难、实践中的做法不一、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有人提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应当予以废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是否应当删除的争论,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什么样的行贿行为应当犯罪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刑法应当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
目前在反贪部门侦查过程中涉及的行贿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A是国家工作人员,B因与A所在的部门有业务往来,长期保持与A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包括吃饭,洗浴,逢年过节送贵重礼品、购物卡、几千或者几万元人民币。B行为的出发点是A有职权,希望A的职权对自己业务能产生有利或者不阻滞的影响,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或者说谋利事项。
2.A是国家工作人员,B给A送财物,是希望A能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其谋取非法利益。
3.A是国家工作人员,B给A送财物,是希望A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给予B特殊待遇,在竞争中排挤竞争对手,获取优势地位,或者希望A滥用职权、违背职责,为其谋取利益。
4.A是国家工作人员,B给A送财物,是为了促使A依法行使职权,使B能获得其应得利益。
上述第4种类型,在我国刑法中是绝对不构成犯罪的,另外三种类型,第2种构成犯罪没有争议,第1和第3种类型在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但处理结果不尽相同。第1种类型,其实属于单纯行贿行为,我国刑法对单纯行贿没有规制,仅认定为违纪,但司法实践中对累计数额较大的往往会作为第3种类型处理。第3种类型,实践中采用不确定利益说,作为不正当利益的情形之一来处理。不确定利益说认为,利益分为非法利益、合法利益和不确定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有自由裁量权、行贿人有可能获取的利益为不确定利益,采取行贿手段获取不确定利益就是谋取不正当利益。司法实践对上述行贿行为的处理方式是否合法合情合理,有待商榷。
有学者通过比较法的分析,认为我国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实际上扮演着德日刑法中职务要件的作用以反映权钱交易的特征,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利益是否能得以实现,而是职务或职权与财物形成了对价关系,因此利益要件替代职务要件是不合理的。[7]笔者对此深表认同。欧陆法系国家,包括香港、台湾的刑事立法例中,均将公职人员的受贿罪分成普通受贿罪(单纯受贿罪)和加重受贿罪(违背职务的受贿罪),行贿罪也比照受贿罪,分为普通行贿罪(单纯行贿罪)和加重行贿罪(违背职务的行贿罪)。而我国刑法贿赂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只是要件之一,构成犯罪须满足利益要件。就行贿而言,主观上必须有“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实际上,贿赂犯罪损害了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公正性,破坏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公正性与正确性的一种信赖,长此以往,将导致国家威信的丧失,从这个角度分析,将“利益”作为构成要件是不恰当的。只要是行贿,就具有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危害性,谋取利益的正当与否并不能减轻或者免除这种危害性。实践中对第1和第3种类型行贿行为的处理,实际上体现了司法工作人员、社会大众对此类行贿行为的否定性态度。
我国对行贿行为的刑事政策,一直颇受诟病。一是由于利益要件上的差异,相比对向犯的受贿罪,行贿构成犯罪的要少得多,贿赂犯罪的打击重受贿轻行贿;二是由于行贿罪的处罚相对较轻,许多行贿人最后免于刑事处罚或者被判处缓刑。这使得行贿成本低、风险小、利润高,以至于一些人有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行贿。一旦社会形成这种病态思维方式,对整个反腐败事业必定形成巨大的阻滞,因此,对“不正当利益”要件须慎重看待。
第一,通过将行贿行为犯罪化,明确行贿行为侵蚀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上述4类行贿行为,刑法都应当持否定性评价,作为犯罪处理,具体可以采取类似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对不同类型的行贿行为加以区分。有人也许认为,受公职人员刁难、勒索,为得到正确利益被迫行贿的行贿人是无辜的,因此而受刑法追究显然不妥。但事实上对此类行贿行为的放纵,助长的是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权力寻租的风气,破坏的是整个公权力运作的公平公正廉洁秩序,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
第二,不能简单删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行为有轻重之分,罪责也应有轻重之别。对各类行贿行为的犯罪化,并非“一刀切”,行贿是否为谋取利益、谋取什么利益、行贿数额大小等在刑罚上应当有轻重之差。一方面,这是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贿行为,考虑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由于行受贿往往是“一对一”的场合,主要定罪依据是行贿人、受贿人的供述,书证、物证较少。侦查机关为突破受贿案件,给予行贿人一定的“政策”,从刑罚裁量的角度,就是将行贿人的坦白从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有利于受贿案件的侦破。
综上所述,“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界定颇费周折并导致司法认定困难,同时,行贿行为本身就具有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危害性,谋取利益的正当与否并不能减轻或者免除这种危害性。因此,从行为的本身进行刑法上的评价,应该认定行贿本身就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惩罚,利益的正当与否可以作为量刑考量而不应作为定罪依据。
注释:
[1]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2]于志刚、鞠佳佳:《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界定”》,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 17期。
[3]赵秉志:《商业贿赂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与修改》,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
[3]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0页。
[5]于志刚:《贿赂犯罪中的‘谋取’新解——基于‘不确定利益’理论的分析》,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6]朱孝清:《斡旋受贿的几个问题》,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7]徐启明、李卫国:《论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10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