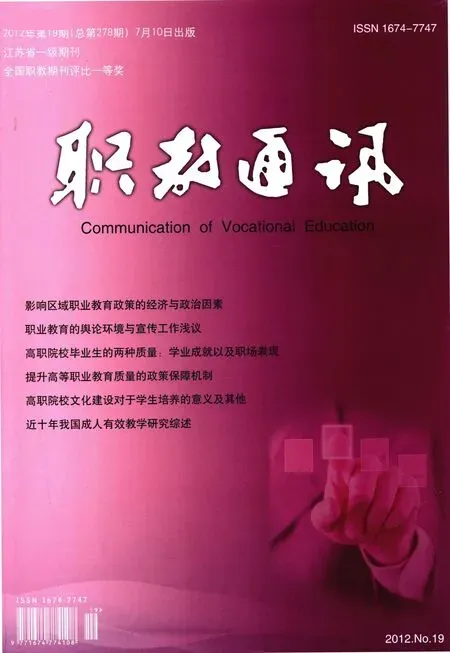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对于学生培养的意义及其他
2012-01-28刘猛
刘猛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对于学生培养的意义及其他
刘猛
高职院校要培育自己的品牌或特色,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加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有利于确立培养和谐之人的总目标,有利于保障学生个体持续的创新力,还有利于拓展人类文化传播的深广度。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创新能力
高职院校作为一种类型的育人机构,要培育自己的品牌或特色,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近些年来,尤其是2006年国家启动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实施之后,文化建设与质量提高、制度创新一道已经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三大主旋律。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文化软实力”,可以为高职院校办学提供持久而强劲的深层动力。那么,对高职院校来说,文化建设存在的具体价值或意义何在?本文借鉴前人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试图从院校的培养目标、学生的个性发展、人类的文化传播三个层面进行一些探索与思考。
一、加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有利于确立培养和谐之人的总目标
高职院校文化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经过自身努力、外部影响、历史积淀而逐步形成的独特的东西,它主要凝聚在学校所拥有的理念、制度、管理、行为、校风、教风、学风等深厚底蕴之中,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和综合力量。我国教育学者袁贵仁曾说过:“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1]文化育人的关键是学校自身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力的形成。继承文化、整理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是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一切教育机构得以存在的永恒理由。
现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职业岗位操作能力,而是从业素质的全面提升,包括职业技能、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创业能力等。这里所谓的从业素质全面提升就是包括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众多教育家都曾强调的身心全面发展的和谐之人。如爱因斯坦就认为,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专家。因为仅仅“用专业知识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的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青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2]我国著名学者徐葆耕对教育中科技专业性与人文通识性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他认为,就两个极端而言,孤立的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可能会造就两种畸形人,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技术奢谈人文的“边缘人”。也就是说,职业学校培养的人应当是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平衡发展的人。人文素质教育并不是一种新的教育类型,而是一种教育理念,它与职业教育并不是矛盾的,因为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人才培养与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同,关键不在于手头的功夫和感觉,而在知识和技能的结合上,也就是知识技能型人才,但是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人们却往往把职业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看作是相互冲突的,这是因为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人们对于知识和教育的功能的理解局限于短期的“有用性”上,而这种“有用性”的内涵又是非常狭隘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在人们看重学历文凭的时候,“有用性”就是考试可能考到的、考试大纲中规定的;在人们关注职业教育的时候,“有用性”就是实际的操作技能、知识、经验,再加上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中规定的考试要点。对于教育和学习采取的这种非常实用主义乃至急功近利态度,忽视学生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几十年来我们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今天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部分地从教育这种根本的失误中找到原因。
高职院校要实现爱因斯坦所说培养和谐之人的教育目标,就必须从最核心的课程文化结构层面上积极推进自身的文化建设。具体地说,这种课程文化结构应当是技术类课程、科学类课程及人文类课程三者的有机结合。其实,这一观点早在近百年前就由英国著名教育家怀特海提出来了。在一篇题为《技术教育及其与科学和文学的关系》的著名讲演文章中,怀特海认为,要谈及(职业)技术教育,首先必须明确它应当具有的理想。我们在自己的脑子里设计出我们期望达到的最完美的典型之前,就投入讨论(职业)技术教育可望取得的目标是不现实的。他借用萧伯纳一剧作中的主人公神父之口表达了(职业)技术教育的理想,即“那是一个国家,其中工作就是娱乐,娱乐就是生活”。怀特海之所以提出这种技术教育的理想是基于对西方(或欧洲)柏拉图式教育传统的批判。柏拉图式的教育在内容上偏重于较为抽象的数学和审美的文科,它传授的是思想的杰作、充满想象力的文学杰作和艺术的杰作,而在方法上则强调自由讨论,它是一种需要悠闲的贵族式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虽然“对欧洲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它促进了艺术;它培养了那种代表科学之源的无偏见的求知精神;它使精神面对世俗物质力的影响时保持了高贵的尊严,那是一种思想自由的尊严”,但“其有害的一面就在于,它完全忽视了技术教育作为理想人完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忽视来自两种极其糟糕的对立,即精神与身体的对立,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对立”。其实,按照一般人的常识或用现实的态度来看,愉快的精神活动或进取心不仅科学家和雇主需要,对一个工人来说也需要。因为“一个疲倦而厌烦的工人,不管他有多么熟练的技能,难道他会生产出大量一流的产品?他会限定自己的生产,对工作敷衍了事,善于逃避检查;他不容易使自己适应新的方法;他会成为众人不满的目标,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所谓新想法,对职业环境的实际工作缺乏体谅理解”[3]。怀特海进而认为,只能将(职业)技术教育、科学教育和文学(人文)教育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学习者达到智力和性格的最佳平衡,实现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目的。从怀特海的深刻提醒中,我们不难看出: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尤其是课程文化建设)只有坚持“既兼顾整体,又有所侧重”方针才能有助于实现学校教育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所谓“兼顾整体”,就是实践性的(职业)技术教育、理论性的科学教育、意义性的人文教育一齐抓,“又有所侧重”就是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否则,就会出现后来另一位西方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那种尴尬或荒谬,即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只是服务于某些目的的专业工人,他们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4]。
二、加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有利于保障学生个体持续的创新力
文化赋予人的生存以意义。高职院校文化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精神摇篮。按马克思的说法,每个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存在,其所体现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却不会千篇一律,彼此雷同。如果说前面探讨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有利于培养和谐之人是从一般或总体意义上而言的话,那么它还必须更进一步落实到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具体或个体意义上才算真正得以实现。这二者应当说是完全统一的。正如教育家杜威表达的那样,“我们假定教育目的在于使个人能够继续他们的教育,或者说,学习的目的和报酬是持续不断的生长能力。”[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巴黎)于1974年11月19日通过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议(修订方案)》中,在“与整个教育过程有关的职业技术教育目标”部分专门提及:“根据个人的需要和志愿,职业技术教育应该:(1)使个性尤其是精神和人的价值、理解力、判断力、批判思考精神及表达能力得到和谐发展;(2)培养思想方法、实践能力和必要的态度,从而使个人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3)提高个人的决策能力,并且使之具有为积极而又明智地参与社会生活和集体工作所必要的品质,以及在工作和集体中履行其职责所必要的品质。”[6]可以看出,这份发表于四十多前年的国际教育文件所倡导的职业技术教育使命是:对学习者个体独立而自由的生命意志充分尊重与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培养和发展其终身受用的、具有一定社会性的良好品质。对我国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来说,这应当具有相当的警示意义和借鉴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中盛行是“家(国)本位”的思想,而在当今我国学校文化中又较多强调“集体”,忽视个人;强调统一,忽视差异。这往往不利学生个体的健康发展。而“谋个性之发展”应是高职院校学校文化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观点的前后变化中看出相当多的意味来。我们知道,黄炎培在1917年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至1930年,他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大辞书》撰写的“职业教育”词条中,此种论述未有变化,并且给“职业教育”定义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一方获得生活之供给与乐趣,一方尽其对群之义务”。而在1934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公订后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认为“职业教育之定义,是为
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与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而其目的: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7]前后论述的明显变化在于增加并突出了“谋个性之发展”。这观念变化的产生既有中国社会在五四之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也有教育系统内部自古以来就有的“因材施教”教育原则的制约。
“因材施教”是文化育人的成功秘笈。仍以黄炎培的看法为例,他1945年曾在《关于职业指导——如何办理职业指导序》一文中写道:“余幼读古籍,有悟于因材施教之合理,有十余龄从弟,能运其天才,自动修整已坏之计时钟,乃导之使习机械,终有献于时。而我友甲,习蚕桑,不安所业,投身新闻界;友乙,习纺织,学成而不屑所为,则创为法政学校;友丙,亦习纺织,不安所业,投身政治既而研佛学,之数人者,最后或有成或无成,一皆不悦所学,相反地使余益感所习不依其才性之非。”[7]可见职业教育只有“使人人依其个性”才不枉为“受到真正的教育”。不能不说的是,从孔子到黄炎培都有“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但因主要受制于大一统或集权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的教育(不只是职业教育)长期以来难以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创新性人才不容易出得来。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曾说过,“人们悲叹中国人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处处受到跨国公司掣肘。如果不走出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吞噬个人的阴影,不确立张扬个性、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观念和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治。”[8]可见,高职院校文化建设要想有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特别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是集体本位,美国文化是个人本位,并在肯定自己的同时,对对方则多有否定(近乎于对“自私自利”式道德的唾弃)。教育学界也习惯于这么看。其实,美国教育中突出的“个人”,基于尊重“个人自由”的思想,早在1938年美国总统发表了《美国民主的教育目的》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目标:自我实现的目标、人际关系的目标、经济效率的目标和公民责任的目标。相比而言,我们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培育却较少为教育所关注。鲁迅先生在大半个世纪前曾说大量国人是“个体的怯懦与集群的自大”。真是没有比这概括更到位的国民性批判了,而这种情况至今我们难道还少见吗?因此,我们今日的学校教育无疑应当倡导培养真正有个体担当勇气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维持独立人格的条件下保持创新的持续动力。在一定意义上,高职院校更应如此。因为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必须在科技创新上勇于弄潮,才能为自己的更好发展赢得空间,赢得未来。
三、加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有利于拓展人类文化传播的深广度
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它深度地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一种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活动,促使人成其为“类”,因而与人类文明休戚相关。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说到底,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的差异性、社会性和符号性使文化传播“势所必然”并成为可能。威尔伯·施拉姆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及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这三位学者的论断[9]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教育与文化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就是有目的地传播文化的社会活动。文化传播为教育提供了存在基础和意义,教育给文化传播以发展契机和生机活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通过包括学校教育等途径得以实现的文化传播,“已成为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关键性要素”。[10]按照人类学的解释,学校教育中文化传播实现的方式不外是对“先天”母文化的“濡化”和对“外来”异文化的“涵化”。濡化(enculturation)表示在特定文化中个体或群体继承和延续传统的过程。而涵化(acculturation)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或接受,或适应,或抗拒,这三者是文化涵化时有可能出现的典型形态。简单地说,文化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传播过程,而文化涵化则是发生在异文化之间横向的传播过程。我国教育学者郑金洲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濡化与涵化都是必需的。涵化使受教育者接受不属于本团体、社区的生活方式、价值习俗,既拓宽了其视野,又激发了其创造力,进而为文化变迁提供了动力;濡化使受教育者适应本团体、社区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观念,促成了其社会化。如果只有濡化,就可能使受教育者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甚至抱残守缺;如果只有涵化,就有可能使受教育者失却传统,忘记根本,甚至造成人格上的分裂。”[11]
那么如何实现濡化与涵化的有机统一呢?我们认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应当体现两方面的努力:(1)学校文化应当抵达自身所处社会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从而提升学习者对所属文化传统的学习与适应能力。文化传统大体包括价值体系、知识经验、思维方式和语言符号四个部分。其中又可分为包括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深层结构和包括知识经验和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它们融汇于教育过程之中,制约着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同样,教育也以相对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传播。一般来说,知识经验与语言符号属于显性文化,可以很明确地进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体现于学校的“课程表”中,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课堂教学活动加以传递,从而成为“显性课程”;而价值体系及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属于隐性文化,它们是文化构成的基础,隐于文化事实与文化现象之后,是文化中之精深微妙者,只能主要通过非正规的组织加以传播,从而成为“隐性课程”。“在一种水平上,学校、学院和大学是相似的,在另一种水平上,它们又是不同的,而且每种机构都有其特定的文化——一套带有方向性的信仰、假设、价值观和传统。正是这些文化,在同等水平上把这种机构与其他教育机构区别开来。有些文化是在公共场所体现出来的,在大众场合,大家拥有相同的目的和承诺,在(显性)课程经验之外,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严密的思维。”[12]这表明,学校文化的构成状态对课程规划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实现学习者文化濡化的“核心地带”。(2)学校文化要敢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多元视角,从而激活自己对所属文化传统的反思与超越能力。西摩·费希认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而“儿童自出生之日起,就打上了民族中心主义的烙印,深信本民族、本国人民、本国语言及生活方式不仅迥异于其他的文化,而且总是优越于其他的文化。置身于特定文化中的个体对上述观点深信不疑,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是如何影响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只有理解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情境是如何影响其他文化情境中的行为和事件,我们才能够在日渐多元化的世界中获得双重视域。”为此,我们就必须了解他国的文化背景,在面对外国文化时,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化。也可以说“,不了解他国的文化也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这是因为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够找到文化之间的异同。我们观察别人文化的镜子既是一扇窗户,也是一面镜子,它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方式真实地反映出来”。[12]因此,高职院校文化建设要有利于实现文化传播,就应当在濡化和涵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形成学习者对文化态度的“双重视域”甚至“多重视域”,才能更好地将人类社会丰富的文化遗产推陈出新。
文化是最亲和的名片,文化有最迷人的力量。只有文化建设到位,我们的高职院校才是青年学子寻求安身立命之法的育人之所;只有文化建设到位,我们的高职院校才能在服务社会发展经济上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只有文化建设到位,我们的高职院校才有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厚底气。这时,高职院校的文化力,是院校和师生个人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和支持力,也是院校之间竞争的核心力和生产力。
[1]袁贵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推进大学文化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2(11).
[2]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10.
[3]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76-104.
[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50.
[5]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06.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的演变:趋势与问题的比较研究[M].张人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内部资料).
[7]成思危.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文萃[M].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6:28,22,215,187.
[8]袁伟时.抗战:文明的进展与中国的反思[J].中国新闻周刊,2005(30).
[9]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0.
[10]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人民出版社, 2003:8.
[11]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5.
[12]费雷斯特·W·帕克、格伦·哈斯.课程规划——当代之取向[M].谢登斌,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59-68,87-94.
Abstract:Abstract: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if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intends to form its own features o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ill help set harmonious education as its general objective, guarantee continual originality in student as individuals, deepen and broaden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originality
[责任编辑 金莲顺]
The Signific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Campus Cult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Students Development
Liu Meng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2011年度项目“社会资本与职业院校发展研究”(项目编号:B-b/2011/03/027)作者简介:刘猛,男,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职业技术教育。
G718
A
1674-7747(2012)19-0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