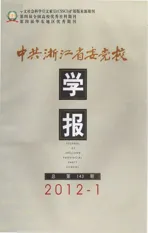学术与政治之间——新中国法理学独立品格的艰难形塑
2012-01-28蒋海松
□ 蒋海松
知史可明理,鉴往方知今。反思建国以来我国法理学的发展有着独特意义。①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文显、黄文艺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法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姜明安:《中国法学三十年(1978-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等等。论文如张文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陈金钊:《“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现代中国法学的开端本与政治情势相关,之后虽然主题频繁变换,但主要并不是法学理论自身逻辑演进的结果,而是出于对政治决策等法学外部问题的一种回应,更多是一种政治话语。因此,大多学者直接以我国经济、政治等事件的发生作为法理学不同阶段的标志。②如张文显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法理学的分期对应于政治进程。参见张文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这种“外部视角”确乎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但直接将政治事件当作法学发展标志,可能会遮蔽法理学的“独立性”。我们既需要探讨这些事件的影响,也要看到法理学对这些事件的论证方式或批判维度,注意到中国法学在政治框架限度里有了相当发展的事实,进而探寻法理学在对政治话语的追随和演绎之后所蕴含的自身发展与生成逻辑,体察其独立品格的艰难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外结合的双重视角”,借用思想家韦伯一本演讲集《学术与政治》①[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书名,中国法理学也是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夹缝中艰难成长的。
一、1949年—1978年:在虚无中涅槃
自19世纪30年代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传到我国之后,曾出现蓬勃发展之势。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度有所进展。1952年全国掀起“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运动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对法理学发展有所推动。50年代初,以俄为师,法理学学科沿用了苏联法理学的名称《国家与法的理论》,苏联译著对当时我国法理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此阶段也进行了有关法的本质、法治和人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和国家政策的关系、关于法的消亡等问题讨论,推动了法理学的发展。②孙国华:《关于如何编写〈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科书〉的几个问题》,《政法研究》,1963年第1期。
但在一次次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影响下,其发展历尽曲折,一度倒退乃至全面停滞。法理学依附于政治学说,法理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未得到树立。传统法理学基于革命思维的惯性作用和政治至上国家观的统摄,导致了作为主体的人彻底迷失,也导致了法理学母题被彻底遮蔽和整个法理学的中空化。③徐显明:《中国法理学的时代转型与精神进路》,《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而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逐渐扩大化,法理学研究一度成为禁区。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提出后,《国家与法的理论》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法制》。其主要内容为:“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对敌专政”。所有的部门法研究大都被政策研究所取代,法理学这一学科实际上已被取消。④康博:《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理学独立品格的形成》,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文革十年浩劫,法学在劫难免。高鸿钧先生曾用史诗一般沉痛的笔调哀悼这段历史:“一夜秋风,神州残花遍地;十年劫难,山河满目疮痍。法院门可罗雀,法典付之一炬,法学弃如弊屣,法治荡然无存。”⑤高鸿钧:《清华法治论衡》(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3页。
李步云总结了从建国到1978年法学研究严重遭受五个“主义”的危害:“一是法学教条主义……汇编、整理和解释思想导师尤其是革命的政治领袖的言论成了正宗的法学家的使命、职责,成了法学研究本身。二是法学经验主义,片面强调自身的国情,强调自己国家的立法与司法的实践经验,实际上是政治任务和使命在指挥着法学家门的头脑,轻视法律本身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理论和逻辑。三是法律虚无主义,认为法律可有可无……四是法律工具主义,漠视法律的伦理性价值,否定法律保障人权、约束权力的功能。五是法律实用主义,轻视法律的独立品格”。⑥李步云:《法理探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也有学者简要地总结为“政治性有余,科学性不足,阶级性强烈,真理性不够。”⑦李龙、汪习根:《风雨百年的中国法理学》,《跨世纪法理学回顾与展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这一阶段我国法理学还不具备学科自身存在的条件,更奢谈是否形成了“独立品格”。
黑格尔曾经感叹:“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⑧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张扬、范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14页。思想需要一个反思甚至否定的对象。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也是如此,1978年以来中国法理学独立品格的形成正是建立在这之前极左思想影响的历史进程的反思之上的。乱后思治,劫余议兴,法理学逐渐摆脱对政治学理论的依附,上演了一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大剧。
二、1978年-1988年:逐步苏醒
从1978年到1988年改革开放前十年的破冰之旅中,我国法理学也取得初步发展,突破了左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学术理念,树立了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这可称之为法理学“逐步苏醒”阶段,是新法理学的奠基与初创时期。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国家的航向,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也为中国法理学的“苏醒”提供了思想的先导。通过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还是法治”“政策和法律的关系”、“权利和义务基本范畴”等法理学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法理学逐渐摆脱了政治学的束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曾载于我国1954年宪法中,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反右派”思想的影响下遭到批判,在十年文革中销声匿迹。1978年1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7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又明确了此项原则。我国法理学界也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认为“平等”应该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对这一法治基本原则的讨论,反映了我国法理学界认识到要法治、不要人治,以及法律平等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性,反映了我国法理学对自身学科基本理论获得了正确的认识。
以1979年1月26日王礼明《人治与法治》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标志,学术界展开了“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一致认可了“法治”的重要性,对政治法制建设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法理学学科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在逐步苏醒的过程中,标志性事件是“权利和义务”这一法学基本范畴的确立。“礼”“刑”等构成中国古代法学的核心范畴。建国后照搬苏联法学,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成为中国法学的轴心。改革开放后,确立新法学的基本范畴、建构新的法学理论体系迫在眉睫。1988年在吉林长春召开了全国基本法学范畴研讨会。“权利本位论”、“义务本位论”和“权利义务一致论”这三种观点进行了激烈交锋,最后学界达成了基本共识: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核心和实质,是法学的基本范畴。这一观点的确立,彻底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学说的束缚和控制,重新找到了法学学科的基本范畴。“权利本位论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观点,也是一个有关法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也是法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视野”。①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这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于法的本体论范畴问题的讨论,如关于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权利意识以及人权等等。以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学基本范畴的崭新法学理论体系开始逐步建立起,法理学自身学科的独立地位得以确立,这可视为我国法理学已经“苏醒”的标志。
当然,受历史条件限制,这一时期法理学界学术论著颇显稀少,成果主要反映在编著教科书上。1981年,北京大学率先出版了新的法理学《法学基础理论》②陈守一、张宏生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首部“法理学”教材。1988年8月出版的万斌编著《法理学》教材,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第一本正式命名为“法理学”的教学用书。③付子堂主编:《法理学高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这一时期研究集中在有关法理学自身和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如法的社会性、法的价值、法的实现、法与权利、法与民主、法与平等、法制与改革、法制与物质文明、法律文化、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等,取得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思想先导作用下,我国法理学从历史沼泽中逐渐走了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法的概念和本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诸多重大基础性观点得以确立,树立了自身学科的独立性地位,对自身独立品格的形成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因此,在此意义上,这一时期我国法理学已经“逐渐苏醒”。但无论在内容、体系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还需要不断完善。
三、1989年-1998年:“不断觉醒”
1989年到1998年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十年。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1997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理论的形成,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我国法理学在确立了自身学科的独立地位之后,对“指导中国法制实践”这一法理学学科的使命有了清晰认识,“理论指导实践”的意识逐渐增强。其突出标志是依法治国相关理论的提出对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直接影响。同时,法理学学科发展迅速,研究领域不断开阔,承接上一阶段的逐渐苏醒,这一时期可称之为“不断觉醒”的阶段。
1992年可说是中国法理学的转折之年,讨论问题集中在市场经济与法治、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等方面,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文化、权利理论、法律移植、正义理论等专业领域都出现了一批颇富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张文显教授将1992年到1996年确定为法理学的“加快发展阶段”。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极大地激活了法理学研究和想象的空间。”①刘东升:《近30年法理学研究进路,1978—2008》,《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法学界紧紧围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代主题,集中研究了法治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法律移植、人权与法制等问题。基本上认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命题。与此相伴,法理学界在此时期开展了“现代法的精神”和“权利本位说”的系列讨论。这些都标志着法理学已开始“主动”地承担使命,为市场经济法制实践发展寻求“法理学”的解决之道。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一重要观点为此后“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之一。②早在1979年,李步云教授就发表了《论以法治国》一文。20世纪80年代初法理学界对“人治与法治”展开了大讨论,确立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共识。当然当初主张“法治论”的学者们主要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并未把“法制”和“法治”进行严格区分。80年代中后期“法制”和“法治”的含义辨析日渐引起注意。法理学界显然赋予了“法治”更多的法律价值理想。法治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学界对“法治”的理论认识为升华到“依法治国”的理论高度做了充分准备和铺垫。1996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出台,中间指出:中国21世纪的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法理学这一理论认识得到国家的认可,有学者表示这达到了“以不断重视和强化法制在国家和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特征的各量变阶段的极限。”③李步云、张志铭:《跨世纪的目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第21页注释。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党正式宣告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理论是我国法理学界最为杰出的学术贡献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人治”与“法治”大讨论、“法治”与“法制”讨论到1992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过程,是“中国建国以来50多年的实践走过‘法制——法治——以法治国——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方针——依法治国方略’这样一个理论认识过程。”④宋迎军:《法治与当代中国法理学》,《河北法学》,2001年第2期。可以说,“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法理学的理论深度和理论水平日趋成熟和完善,也标志着我国法理学由早期的“苏醒”步入到“觉醒”的过程。
这一时期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我国法理学的整体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提高。诸多全国性法理学会议召开体现了对当下法制实践的学科关怀,一系列法理学学术著作相继面世,法理学的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扩展和深化趋势。学界更集中认真地研究法理学领域中的独特问题,如法与利益、法的历史类型、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的价值、法的创制、法律体系、法律渊源、法律规范、法律行为等基本命题,法理学的专业性逐渐突出。可以说,我国法理学经过前一次“苏醒”,树立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后,在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指引下,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也更富有法理特色,不断尝试用法律来寻求治国之道。我国法理学完成了其迈向“独立品格”的“觉醒”过程。
四、1999年至今:趋向自觉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正式获得确认,成为法理学向深广领域全面发展的重要契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法治研究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主题。
从学科发展自身的角度而言,这期间最值得关注的是法理学对自身的发展开始进行自觉反思和批判,对未来的方向进行自觉思考,法理学学术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确定,这是法理学发展“趋向自觉”的阶段。从哲学上看,自觉与自发相对,有其独特意义,一般是指人们正确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后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有意识认识世界的意识行为。“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对自我发展进行充分反思,反思意识是自觉的最内在之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反思一生学术研究时,提出了“文化自觉论”。他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借用这个说法来概括自1998年以来的法理学发展阶段是贴切的。这一时期法理学学科独立学术品格逐渐形成,理论开放性不断增强,开始自觉对法学和法理学的自身发展进行了自我总结和反思批判,这以“法理学向何处去”、“法制现代化”、“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几场讨论最具典型。
1999年《法学研究》、《法商研究》编辑部联合在武汉召开了“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这种专门针对法理学自身发展的反思会议并不多见。主要讨论了四个议题:法理学现状分析、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法理学的承继、引进与创新、目前研究重点问题。②《“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研讨会纪要》,《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许多学者指出,法理学主要问题有:1、法理研究的泛政治化,缺乏批判精神。政策的不断变化决定着研究主题的不断更换。2、规范法学的缺位。法理学没有起到有指导部门法的作用。3、自身没有独立性,没有建立起自身的范畴体系。4、没有真正的学派、流派,没有形成学术交流的理性平台。③同上。会上用词之犀利,争论之激烈也为后来所罕见。这是我国法理学界对自身发展的一次深刻反思与自我批判。
有关“法制现代化”的讨论早在20世纪初清末修律时即已浮现,但之后沉寂了近半个世纪。20世纪90年代初,法理学界再次高度。如公丕祥指出:“伴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制也同样面临着一个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变革,这个转型,变革的过程,就是法制现代化的过程。”④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许多学者反思了“法制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向西方国家学习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制度和理论的全盘照抄。“法制现代化确实是从西方开始起步的,但并不能就此推出非西方社会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化过程的结论,更不能意味着西方论。”⑤公丕祥:《法制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法学》,1997年第1期。法制现代化的路径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外发型”道路、“内发型”道路和“内发型”和“外发型”相结合三种观点,也可相应称之为“移植论”、“本土论”和“混合论”。第三种思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法制现代化不但要通过法律移植、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进改革,还应该注重社会、民间的内部秩序的发展。与建国之后我国对“苏联法律”的移植相比,这次讨论显示出了高度“自觉”的批判精神。前一次“移植”基本上出于政治上的“被动”和全盘照抄,这一次的“移植”却充满了“担心被实践所抛弃”的警醒和忧虑;前一次仅仅在“制度”的层面亦步亦趋,对是否适应中国的“实践”置若罔闻,这一次不仅首先对“移植问题”本身是否合理进行了自觉的思考,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对法制现状和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反思,充分体现了自觉反思的学术品格。
1999年12月法理学界曾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了主题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研讨会。有学者评价“由于视野的开阔,参照系的不同,而认识到了我国法理学的诸多不足,意味着还需要加大对法律现象认识的深度。”⑥刘东升:《近30年法理学研究进路:1978——2008”》,《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2005年邓正来教授的长篇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发表并结集出版。⑦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邓文对中国法学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其主要理论模式“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都受到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支配,中国论者实则为中国的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图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中国法学或中国法学界在很大程度上既没有参与上述关涉社会秩序之性质或社会秩序之正当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也没有在中国法学的具体研究中对上述问题给予应有和足够的关注。”⑧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对此文的讨论和回应空前热烈,还出版有专门的评论集。⑨对此的专题评论集参见刘小平、蔡宏伟主编:《分析与批判:学术传承的方式——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些学者对此文批判的部分主要问题表示赞同,认为中国的法理学总体上处在“幼稚”的水平,中国法理学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方法等受国外尤其是西方法理学的影响,而中国“仅仅成为需要被处理的客体化材料和对象。”①赵树坤:“从空间意识形态藩篱中突围——法律理想图景的中西辩证”,《现代法学》,2006年9月。这确乎是我国法理学对自身历史发展过程的一次自觉的系统反省,也标志着法理学的自觉意识、反思意识、主体意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场争论中最重要的贡献是自觉反思西方法学话语,呼吁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呼吁创建具有主体地位的中国法理学,这是中国法理学自觉意识的一大展现。事实上,这一自觉意识有一个漫长的萌芽到发展的过程。
自19世纪中后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西方话语亦步亦趋的附庸。几十年后,这种状况并没获得根本性转变。汪晖认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②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这也可见之于中国法理学的现状。几乎所有的法理学话语,都是围绕着“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而展开的,并认为“西方-现代”这一极相对于“中国-传统”来说具有天然合理性。苏力教授一再直陈:“中国的法律人目前大多并没有这种真正的中国问题意识,他们发现的中国问题都是比照书本来的。……他们总是列举外国的做法,但是列举也不过是列举,不是论证”③苏力:《面对中国的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3期。。支振锋等提出中国法学和法治有不同于大部分英美、欧陆等西方国家的自身特征。今天的中国法学必须被放置在中国一百多年来大变革的背景之中和近当代以来中国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进行观察,考察它的基本规律与经验教训,汇通古今中西,从而对中国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及其发展所体现出来的优良治理机制及其背后的政法哲学的提炼,产生真正有世界贡献的“中国法理”。④支振锋:《“西法东渐”的思想史逻辑及其超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冯玉军认为亚洲法哲学研究的理论结节点在于重新解读现代法治的“历史”本体,后者主要是由一些西方历史哲学家(如维柯、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法学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梅因、萨维尼)在“西方中心论”的理念基础上所描述的“虚幻”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范式。它贯穿在现代法治理论的全部概念、原理和体系当中。当前,只有批判并超越此种带有鲜明霸权话语烙印的“历史观念”和“世界图景”,方可推进多元化的世界法律文明体系的健康发展,创立具有中国主体地位的法理学。⑤冯玉军:“‘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现实的启示”,《法学家》,2003年第4期。
在这一时期,召开的学术会议主题广泛,学术性大大增强,学界对新时代法理学使命的思考更加自觉、更加集中。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涌现出颇多对法理学发展30年回顾和反思的研究成果。⑥代表性论文如李龙、陈佑武:《中国法理学三十年创新的回顾》,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2期;陈金钊:《“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武建敏:《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理论诠释——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河北法学》2008年第9期;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著作如姜明安:《中国法学三十年(1978-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中国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等诸多学术期刊进行了专题研究。⑦罗豪才等:《法学发展三十年回顾与展望”笔谈》,《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6期。这些研究总结30年来我国法理学的成就和若干局限。学者们主张,在新时期,法理学应具备“自主性”,树立中国法理学的独立思考意识,关注中国的法制实践并为之贡献智慧,保持开放的学术品格,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这些研讨会和其他成果表明法理学界对在不断地关注中国当下政治社会实践的同时,对学科自身的理论发展有着独立地反思和自省,这也是法理学界从不断苏醒到趋向自觉的反映。
五、反思与超越:中国法理学的时代使命
至此,法理学自身的“独立品格”逐渐形成,进入到了理性自觉的新时期。有学者对法理学从1977年以来30年的成就归纳为十大转变:“意识形态之法理学转变为法律科学之法理学;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转变到法理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化、科学化;从法的唯阶级性转变到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从法功能的专政性转变到民主与法制、人权与法律相结合;从法的批判性转变到在“扬弃”前提肯定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从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论转变到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制(法治)经济论;从重政策轻法律转变到法律、政策并重,进而转变到治国主要依靠法律;从注释法学转变到实然法研究与应然法研究并重;从注重法的适用转变到法的适用与法的监督制约并重;从工具性法制价值分析转变到依法治国的法治论。总之,中国法理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体系,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要体现为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实践参与功能的加强、科研队伍阵容的增强、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对外学术交流的扩大。”①付子堂主编:《法理学高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本文将最后一个阶段定位为“趋向自觉”,而非认为其已经达到了自觉。在哲学上,理念是不断发展,不断超越的一个过程,法理学亦然。法理学虽然成就显著,但也存在着明显不足。诸如“左”的政治思维对法理学的影响依然较大,法理学对政治的依附性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法理学具有明显的经验论痕迹,学术争鸣缺乏真正的理论深度。②张文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法理学学科主体建设还不成熟,学科尚不完整。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经济学、法伦理学等交叉学科处于较低水平。学术研究独立意识不强,深入不够,法理学研究学术传统薄弱、规范不够,等等。③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
对这些内在缺陷的反思是自觉担当法理学时代使命的前提。可喜的是近年来这样的反思意见愈见增多。比如周永坤教授尖锐地指出,法理学需要八个方面实行变革,即从“规律学”走向“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的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主客体思维到主体际思维,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④周永坤:《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法理学的青春危机及其消解》,《法学》,2000年第3期。强世功认为我国当下法理学的主流思潮的思考逐渐淡化了“政治”和“国家”等这些法律的外部要素,应重新找回国家,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⑤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谢晖教授提出应充分重视规范研究、规范创新、多元化研究对于我国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及艰难性。⑥谢晖:《关注中国法学的多元化发展》,载付子堂主编:《法理学讲演录》(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徐显明一再倡导进行中国法理学的范式转换。认为法理学的使命在于为一个时代的法律生活建构一个深广的、一元化的理念世界,以之统摄、承载法律的有序运动。能够支撑一个时代法律生活的法理一定是与该时代的精神相契合的。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开放性的市场经济、理性的法治政治、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要求中国法理学要实现从革命到建设、从斗争到和谐、从政本到人本的精神转向。现代法理学在本质上应是如何本于人建构制度、又如何在制度中关怀人、在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的学问。⑦徐显明:《中国法理学的时代转型与精神进路》,《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这些反思意见对法理学的发展弥足珍贵。
《周易·系辞》有云:“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稽古鉴今,彰往察来,方能阐明幽深之理。总结建国以来法理学发展这段历史也是为了更好辨明法理,展望未来。法理学应抓住时代机遇,肩负起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教授提出,法理学曾担当为法学界披荆斩棘、遮风挡雨,进行法学启蒙等特殊任务。⑧郭道晖:《法理学的定位与使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法理学应继续保持这种使命。德国法学家魏德士曾有言:“研究法律和从事法律工作总是一种也要承担政治与道德责任的行为。”⑨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这更是每一个法理学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