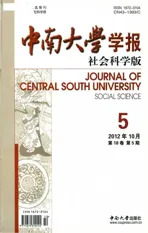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2012-01-21孙宝
孙宝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川南充,637009)
魏晋辞赋的体式类型、题材内容较两汉时期日渐向深细化发展,但在思想主旨、审美趣向等精神层面却呈现出强固的思想惯性,汉赋中高扬的儒家政教观也在魏晋辞赋中得以保留和推进,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一定影响。魏晋辞赋中的儒家政教观大致具有四方面内涵:一是继承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政治观,强化辞赋的宣教功能,既效法汉代骋辞大赋,又从细密取象、征实叙事、布局精严等角度寻求突破;二是发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教观,强调辞赋的博物功能与知识性价值,言咏主题不仅涉及动植物、昆虫、乐器、文具、酒、药、生活物什、天地、四季、山水、云雨等具象事物,更涉及“文”“意”“读书”“谈”、书法用笔等抽象活动,其中固然不乏玄、释思想浸染之作,但许多仍秉持儒家博物观、比德观;三是继承汉人将赋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观点,发挥辞赋政治颂扬的基本功用,又注重个体反省、劝诫的道德化主题,有些能跳出寓刺于美的创作模式而通篇为讽,并强调对个体生命意识、情感意蕴、道义准则、批判精神的抒发,体现出儒家的悲悯情怀与济世之思;四是继承汉人赋须雅正典则的文艺观,确立辞赋“丽则”的审美旨趣,反对劝百讽一的过度雕润,强调“丽”与“则”的有机统一,又从儒家“三不朽”观念出发抬升辞章的社会价值,并以辞赋作为个体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笔者试将儒家政教观分为王道一统观、比德观、教化观三个范畴,分别探讨它们对魏晋赋格建构的深远影响。
一、儒家王道一统观与魏晋都邑赋、礼制赋典重宏阔的气格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是汉代都邑赋发展的极轨,对魏晋以来杨修、卞兰、缪袭《许昌宫赋》、何桢《许都赋》、刘劭《赵都赋》、刘桢《鲁都赋》、徐干《齐都赋》、吴质《魏都赋》、文立《蜀都赋》、傅玄《正都赋》、左思《齐都赋》、《三都赋》、曹毗《魏都赋》、《扬都赋》、王廙《洛都赋》、庾阐《扬都赋》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孙绰径称:“《三都》、《二京》,五经鼓吹。”[1](260)正可看出魏晋士人以辞赋为经学副翼的文艺倾向,这自然没有跳出儒家政教观的范畴。魏晋都邑赋继承汉赋鼓吹国力、追求统一的主旨。《三都赋》称:“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於吴会。”[2](109)正见其维护晋室一统的政治心态。另如王廙《洛都赋》津津乐道洛阳四方辐辏的繁华安乐,也反衬出推尊中原的情结。王廙在司马睿登基之际献《中兴赋》、《白兔赋》,其《白兔赋》云:“曰皇大晋,祖宗重光。固坤厚以为基兮,廓乾维以为纲;方将朝服济江,传檄旧国;反梓宫於旧茔兮,奉圣帝乎洛阳;建中兴之遐祚兮,与二仪乎比长。”[3](1571)此赋又流露出他反梓中原的一统观。
所谓魏晋礼制赋,是指在魏晋时期开始注重五礼制度建设的背景下,以除丧礼之外的吉、嘉、军、宾等四礼为讴歌主题的赋作——丧礼主题则多以诔、铭、哀策、碑等文体样式呈现。吉礼赋、嘉礼赋、宾礼赋的题材一般包括释奠、皇室婚冠、藉田、节庆宴飨、祥瑞等内容,各项礼制确立过程往往经由学官博士、礼官、勋戚乃至帝王多方反复商议,多遵从六经论断、前代仪礼,以宣扬仁德、武功、教化为指归。如傅玄《元会赋》所歌颂的元会礼就经过了详密的经学论证。《晋书•礼志下》载:“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4](649)这自然赋予此类赋作雍容典雅的气质。魏晋其他以朝仪、节日、婚庆为题材的赋作还有很多,如曹植《感婚赋》、王沈《正会赋》、《宴嘉宾赋》、傅玄《朝会赋》、《辟雍乡饮酒赋》、张华《感婚赋》、夏侯湛、褚爽《禊赋》、阮瞻《上巳会赋》、嵇含《祖赋》、《娱蜡赋》、成公绥《洛禊赋》、《延宾赋》、张协《洛禊赋》、郭璞《南郊赋》等,其主旨与傅玄《元会赋》大体一致。至于魏晋时期大量存在的歌颂瑞应、鼓吹帝德的祥瑞赋,亦与上述节庆、婚仪等赋类相映成趣而大同小异。藉田礼也是魏晋嘉礼赋的重要题材。耕藉之礼源出先秦,《礼记•乐记》、《月令》、《祭义》、《诗经•周颂•载芟》等均有详细记载。魏晋时期,早在建安十九年、二十一年,曹操就亲耕于邺东,此后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五年正月、六年春、晋武帝太康六年、泰始中、前凉张骏建兴十二年、后赵石虎永和三年均举行过藉田礼。此外,熊远还在东晋立国之初建议恢复藉田礼,“时议美之”。[4](1885)魏晋以藉田为主题的赋作有曹植、缪袭、潘岳《藉田赋》、闵鸿《亲蚕赋》、杨泉《蚕赋》等。藉田礼以劝农兴教为主旨,一如缪袭《许昌宫赋序》说:“上既躬耕帝藉,发趾乎千亩,以帅先万国,乃命群牧守相,述职班教,顺阳宣化。”[5](85)缪袭《藉田赋》亦当由此而作。与之相应,一些围绕劝农、悯农主题的“感雨赋”也相继兴起,如王粲、应瑒《愁霖赋》,曹丕、曹植、傅玄、陆云《喜霁赋》《愁霖赋》,缪袭《喜霁赋》,傅咸《喜雨赋》《患雨赋》,成公绥《阴霖赋》《时雨赋》,潘尼《苦雨赋》,阮修《患雨赋》等。魏晋士人重视雨水丰歉,是其农本意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无疑可看成魏晋“藉田赋”的一个衍生赋类。征行校猎是魏晋军礼赋的重要题材,如曹丕《述征赋》、《浮淮赋》、《校猎赋》、曹植《东征赋》就分别叙述了建安之十三年、十四年、十九年南征荆、吴的战争场景,尤其曹丕《校猎赋》将部伍严整、寻猎威猛、斩获丰厚、颁赐有度的校猎过程完整呈现出来,藻丽辞丰,叙事井然,气势恢弘,弘扬了尚武主题。两晋期间此类题材的赋作也不少见,如夏侯湛《梁田赋》《猎兔赋》《缴弹赋》,夏侯淳《驰射赋》,潘岳《射雉赋》,陆云《南征赋》,卢谌《观猎赋》,曹毗《马射赋》等。虽然上述不乏“猎兔”、“射雉”等游嬉主题,但大致发扬了以猎兴武的主旨。以陆云《南征赋》为例,其继承二曹的宏阔赋风,为晋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张目:“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称乱,凌逼乘舆,天子蒙尘于外。自秋徂冬,大将军敷命群后,同恤社稷,乃身统三军,以谋国难。……於是美义征之举,壮师徒之盛,乃作《南征赋》以扬匡霸之勋云尔。”[5](329−330)毋论陆云的政治观正确与否,此赋正是基于尊王一统的忠义价值观而发。
魏晋都邑赋与礼制赋一方面继承汉赋弘扬上述儒家王道一统观念,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时代新意。其要有四:其一,以学问为辞的学术化倾向增强。《文心雕龙•神思》将《二京赋》与《三都赋》并提,指出:“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黄侃评述说:“案二文之迟,非尽由思力之缓,盖叙述都邑,理资实事,故太冲尝从方士问其方俗山川,是则其缓亦半由储学所致也。”[6](94)不只左思如此,潘岳《西征赋》在西行的过程中凭吊遗城故址,追念秦汉兴衰,典事云密,史论纵横,颇见出其史略史识,这说明魏晋述行赋也具有以史为赋的学术化特征。当然,从扬雄、刘歆、班彪、班固、崔骃、张衡等人已开启了这种趋势,到魏晋时期又进一步深化,历史、文化、哲思与礼仪制度等因素已成为辞赋的重要构成。其二,以经论、政论为支撑,赋作成为赋家经学意识、政治主张的传播载体。曹植同时作有《藉田论》和《藉田赋》,潘岳《藉田赋序》首先将“藉田”提升到礼乐教化的高度来看待,均可看出两者经学意识在赋中的渗透。江统曾作《函谷关赋》,以桀、纣等恃险亡国的例子指出统驭边疆在于遵循圣典、推行仁化,这正是其《徙戎论》批判晋室不能有效绥抚西北民族的文学化表述,换言之《徙戎论》才是《函谷关赋》的核心所在。其三,颂体成为魏晋嘉礼赋的一大分支。如曹植《皇太子生颂》《冬至献袜颂》、左芬《武帝纳皇后颂》《杨皇后登祚颂》《德柔颂》等,此类均无批判而以赞美为主调,体现了魏晋辞赋美刺相分的趋势。其四,民俗化、生活化色彩日显。如嵇含《祖赋序》就系统探讨“祖”作为祭祀路神的礼仪活动的缘起及应用:“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俯叹壮观,乃述而赋之。”[5](372)其赋已佚,但将祖礼作为天子、庶人共通的礼仪加以揭示,其民俗化的趣味可以想见。
二、儒家比德观与魏晋咏物赋渊雅平和、激越悲悯的气格
儒家比德观主要体现在魏晋咏物赋中,其体现方式大致为两种:其一,以天人合一理论为核心,将人或物与天地自然之德相比附。如成公绥《天地赋》以天地为题材,强调赋“分理赋物”的认知和再现功能,实质是对人自身智性的赞美。他认为人在顺应天道、“敬天而事”的前提下,才能概观万物、以一统万。[5](204)钟会《菊花赋》也说:“菊有五美焉:黄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业。”[5](67)亦将天地之德、君子之性赋予菊花。傅玄善于将日常事物赋予天人和合的色彩,使它们呈现出天然灵性和仁智之性,如《琵琶赋》的“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5](158)《筝赋序》的“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体合法度,节究衣乐。斯乃仁智之器”;[5](159)《紫华赋》的“下无物以借喻,上取象于朝霞”;[5](162)《走狗赋》的“应天人之景晖,顺仪象而近处。凭水木之和气,炼金精以自辅。……感恩养而怀德兮,愿致用于后田”等。[5](176−177)上述“琵琶”、“筝”、“走狗”等意象已脱离了物态表象和实用价值功能,而焕发出儒家仁德的象征意义。其二,以具体事物与儒家君子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相比拟,赋予物象以深刻的人格内涵或批判意识。以物咏德的赋作多为正面的颂扬。如王劭之《春花赋》、左芬《松柏赋》、傅玄《橘赋》、成公绥《鸿雁赋》、《乌赋》、江逌《竹赋》,就分别将春花、松柏、橘、鸿雁、乌鸦、竹赋予光美、正直、进取、孝慈、凌霜有节等德性,尤其《乌赋》“嗟斯乌之克孝兮,心识养而知慕。同蓼莪之报德兮,怀凯风之至素。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句,[5](220)又表达了作者对于乌鸦孝慈之性的向慕之情,体现出将乌鸦人格化后再将其象征化、理想化的思路。
宋俞文豹《吹剑录》说:“诗惟颂德,咏物难工,盖欲指实也。”[7](1231)这就指出了咏物作品在征实和宣教之间如何平衡而不失美感的问题。魏晋咏物赋通常刻画所咏对象的外貌及习性,继而抓住它与儒家道德观念、人格理想相符的一面,或引经典为证,或直接进行颂扬,从而呈现出前实后虚、先文后质、花萼相辉的效果。以文具赋为例,傅玄《砚赋》说:“设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仪。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加采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玄。”[5](156)就将砚台的形制、质地与天地之德、刚柔之性比附。王羲之《用笔赋》亦在笔势形态中蕴涵德性,先描摹笔走龙蛇、气势纵横的情景,又回到其“毗助王猷”、赏玩忘忧的实用功能上来。[5](389)成公绥《弃故笔赋》更倾向于揭示笔的实用与教化功能:“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注玉度于七经,训河洛之谶纬。”[5](217)此赋充分肯定了笔宣扬圣人思想、传播经谟大旨的重要价值。
魏晋咏物赋的比德观也具有新的时代内涵。首先,运用儒家比德逻辑借物喻人,继而对“背德”现象提出批判,此类赋作的批判性超越汉代。如曹植《橘赋》就借橘树由南入北水土不服喻指怀才不遇之情,其《蝙蝠赋》针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的“奸气”而极尽讽刺。[5](61)再如傅巽《蚊赋》说:“水与草其渐茹,育兹孽而蚊。嘴咮锐于秋毫,刺锯利于芒锥。无胎卵而化孕生,博物翼而能飞。肇孟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众繁炽而无数,动群声而成雷。肆惨毒于有生,乃飧肤体以疗饥。妨农功于南亩,废女工于杼机。”[5](83)关于蚊子的描写,较早见于扬雄《法言•渊骞》:“血国三千,使捋疏,饮水,褐博,没齿无愁也。”[8](460)傅巽在扬雄的基础上,对蚊子从生长环境、存在时节、造成恶果都进行了详尽描绘,并对不劳而获、敲骨吸髓者的丑恶品质加以抨击。另如傅咸《青蝇赋》、鲁褒《钱神论》、左思《白发赋》等,均是愤激慷慨之作。尤其左思《白发赋》“发肤至昵,尚不克终。聊用拟辞,比之《国风》”句,[5](366)说明其以“白发”为喻正是自觉继承《国风》讽怨传统的体现。
其次,将玄、佛义理引入儒家比德观,从而使赋作呈现玄儒交融的色彩。王彪之《水赋》以《老子》“上善莫若水”为旨归,对水无心动静而具有导流百川的力量予以赞叹,又对其“不凝滞于方圆”、以柔克刚的随顺之性表示钦服。[5](386)这就扩充了《论语•雍也》“知者乐水”、《孟子•离娄下》“仲尼极称于水”的哲理内涵。孙楚、王彪之、郭璞、江逌均有《井赋》,其以《周易•井卦》为依据,对井这一实物在旱季发挥的作用予以赞赏。尤其江逌《井赋》既注重井的卦义阐发,又注重井的实用功能。其“先王借象以辨义,君子拟淡以自绥。神龙来蟠以育鳞,列仙一漱而云飞”句,[5](471)集中体现了他以井喻君子之德的意识,但这种意识也深深烙上仙道飞升的意蕴。魏晋乐器赋也具有玄儒交融的特色,如成公绥《啸赋》塑造了“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的“逸群公子”形象,[5](211)其以老庄人生理念为依托,借长啸表达逍遥神游的生命境界,同时又传达了移风化俗、贬抑郑卫之音的心志。东晋僧人支昙谛有《赴火蛾赋》,其序云:“悉达有言曰:愚人忘身,如蛾投火。诚哉斯言,信而有征。”[5](545)知其以释迦摩尼训诫为宗而作此赋。魏晋时期还有一些以抽象事物为对象的赋作,如陆机《文赋》、庾顗《意赋》、杨泉《赞善赋》、《养性赋》、仲长敖《覈性赋》、谢尚《谈赋》、束晳《读书赋》、祖台之《荀子耳赋》等。上述赋作涉及文学创作、精神意识、善恶情性、清谈、读书、荀子治学等主题,既有儒家劝教的敦厚,又有老庄机辩的玄远,从思想内涵层面而言远比汉赋更为丰富,赋格意蕴也更趋多元而渊厚。
最后,除了将所咏对象与儒家德义观念比附外,还蕴涵了深厚的生命意识,注重抒发个体价值、独立人格、忧患意识等主题。在世事艰危人心叵测的情势下,以物自比以寄托生命忧思,是魏晋咏物赋的重要主题。如曹植《鹦鹉赋》“常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永哀呜以报德,庶终来而不疲”句,[5](54)就以鹦鹉为喻,表达了寄身笼中、仰人鼻息的感慨。另如曹植《离缴雁赋》、张华《鹪鹩赋》、傅咸《叩头虫赋》、沈充《鹅赋》、梅陶《鵩鸟赋》,也均抒发了变乱无常的生命意识。不容否认,为驱除忧患,魏晋赋家多倾心于庄老之学,从而催生出东晋以来“赋乃漆园之义疏”的现象。[9](1710)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忽略儒学价值观对魏晋士人安身立命的抚慰作用。如挚虞《思游赋》说:“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祐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先陈处世不遇之难,遂弃彝伦,轻举远游,以极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故作《思游赋》。”[5](422)由上不难看出他秉持《论语•颜渊》子夏所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古训,以此赋规劝世人向“正”返“义”的目的。曹摅在永嘉之乱期间作《述志赋》,亦高扬“慕浮云以抗操,耽箪食以自娱”的儒家富贵观与修养观。[5](473)嵇含在八王之乱期间作《白首赋》说:“壮志衄于芜途,忠贞抗于棘路;睹将衰而有川上之感,观趣舍而抱慷慨之叹。”[5](372)从中不难看出其以孔子惜时观抒发功业无成的感慨。谢万《游春赋》说:“咏新服之璀璨,想舞雩之遗尘。抚鸣琴而怀古,登修台而乐春。”[5](438)其中也流露出谢万对《论语•先进》浴沂舞雩的场景的向往。
三、儒家人伦教化观与魏晋言志赋醇和闲逸的气格
魏晋士人异常推重孝亲意识,并在赋中大力宣扬。如曹植《慰子赋》以“空室”、“床帏”等旧物,[3](1125)寄托丧子之痛;又以仰首昊天、彻夜难眠,有效地衬托出这种痛楚之深。曹植《叙愁赋》为感念兄妹分离之作,此赋借二妹的口吻,说出她们侍奉君王的恩宠亦不及远离双亲的哀伤,也隐含着曹植对这种政治联姻的无奈情绪。曹植表现对亲故眷恋主题的,还有《怀亲赋》《离思赋》《释思赋》等。其《释思赋》“彼朋友之离别,犹求思乎白驹。况同之义绝,重背亲而为疏。乐鸳鸯之同池,羡比翼之共林。亮根异其何戚,痛别干之伤心”等句,[3](1123−1124)即借《诗经•小雅•白驹》表现对出养于人的兄弟的依依不舍之情。潘岳也有大量表现伦理孝思的赋作。其《闲居赋》说:“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上述宣扬了为孝辞仕的观念。赋中着重描写天伦之乐的安适与从容:“席长筵,列孙子柳垂廕,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10](70−72)不管他在抒发田园安居的心志,还是描摹园居自然景物,都投射了浓厚的孝亲意识和伦理情感,继而又转化为赋中安乐祥和、淡雅沉静的风格气象。
除人伦孝思之外,儒家用舍行藏、砥砺廉节、安贫乐道等人生观念在魏晋言志赋中也有明确体现。曹植《潜志赋》说:“潜大道以游志,希往昔之遐烈。矫贞亮以作矢,当苑囿乎呈艺。驱仁义以为禽,必信忠而后发。退隐身以灭迹,进出世而取容。且摧刚而和谋,接处肃以静恭。亮知荣而守辱,匪天路以为通。”[3](1126)此赋固然有道家蠖略潜藏的因素,更体现了儒家枉尺直寻、见几而作的处世原则。郄正亦是其例,其“性澹於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依则先儒,假文见意,号曰《释讥》,其文继於崔骃《达旨》”。[11](1034)可见,《释讥》取则汉赋以释愤懑的复古倾向。陶渊明亦将儒家进取与批判意识贯穿于赋作中,其《感士不遇赋》以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为蓝本,除了抒发个人际遇不顺的愤慨外,更表达了对真善的向往和对硗薄风俗的批判。他强调仁善,追求“傲然以称情”的品格,[12](255)主张“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12](256)这些均可看出,他以圣人遗训为法,以忠孝、仁义、德善为宗的价值判断标准。他结合自身“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的处境,又结合张释之、冯唐、庞共、贾谊、董仲舒、伯夷、颜回等人的遭际,提出“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的修身主张,[12](256)其融合了《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与《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等观念,体现出对仁善道德人格的追求。最后他总结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緼袍之为耻。”[12](256−257)可知,他追求的独立人格中儒学意蕴甚厚。正如孙人龙《陶公诗评注》所说:“公一生贞志不休,安道苦节,其本领见于此语。虽感士不遇,而归于固穷笃志。读其文,真可使驰竞情遣,鄙吝意祛,所谓有助于风教,岂不信哉!”[12](260)另外,陶渊明《闲情赋序》称:“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可知正是弘扬风教之作。宋人吴处厚评价说:“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13](81−83)宋人王观国则直接指出《闲情赋》的政教功用说:“熟味此赋,辞意宛雅,伤已之不遇,寄情于所愿,其爱君忧国之心,惓惓不忘,盖文之雄丽者也。此赋每寄情于所愿者,若曰‘我愿立于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谲谏者也。昭明责以无讽谏,则误矣。”[14](225−226)当然,王氏观点纯粹运用美人比德、比贤说对《闲情赋》进行儒家教义化的改造,有其牵强的一面,但也指明了陶赋所寄寓的儒学风概。
需要指出的是,魏晋言志赋在表达向慕儒家理想人格与表白自我心志的过程中,往往以征引儒家经典作为重要手段。如王粲《登楼赋》“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句,[15](655)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与《周易•井卦》九三爻辞“井渫不食,为我心侧”;“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句,[15](655)化自《周易•丰卦》上六爻辞“闚其户,阒其无人”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駪駪征夫,每怀靡及”。潘岳也多喜用《周易》,如其《西征赋》“无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专。陷乱逆以受戮,匪祸降之自天。孔随时以行藏,蘧与国而舒卷。苟蔽微以缪章,患过辟之未远”句,[5](265)化自《周易•系辞下》“危者,安其位者也”与《诗经•大雅•瞻卬》“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周易•随卦》彖辞“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卫灵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其《闲居赋序》“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脩辞立诚以居业”句,[5](279)化自《周易•系辞上》“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周易•乾卦》九三爻辞“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诚所以居业也”。可以说,《周易》在魏晋辞赋中,既发挥立论支撑的理论资源的作用,也由自身所具有的关于人伦日用、进退语默、见微知著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语言魅力,使这些作品具有了含蓄简约而韵味丰厚的特点。
总之,魏晋儒学治学方式呈现脱略门户、综治群经的兼宗化趋势,加之玄、释理论体系、思辨方式的冲击,因此经史兼通、玄儒并治日渐成为魏晋文士普遍的知识素养,这是儒家政教观在玄学语境下不断向辞赋渗透的思想前提。魏晋辞赋在儒学政教观的既定模式和强固的思想惯性下,呈现出典重宏阔、渊雅平和、激越悲悯、宏美明辨、醇和闲逸等气格,即使东晋玄言赋渐兴,其审美性、艺术性价值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当然,魏晋辞赋始终进行着脱离儒学思想惯性的努力,寄情庄老的玄言赋是其表现,脱略德教观念的自然化书写也是其例证。如曹毗《涉江赋》《观涛赋》、伏滔《望涛赋》等着力表现江海自然物态的宏阔奔涌,它们本身就能够引起人们崇高敬畏的审美情感,并不需要德教感化或思辨申发,这种自然化的纯文学写实倾向在晋宋之际以山水诗的样式集中凸现出来。此时魏晋辞赋在庄老、孔儒均“告退”的趋势下轻装上阵,又开始了新时期的历史嬗变。
[1]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六[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3][清]严可均辑《全晋文》[M].北京: 中华书局,1958.
[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5]韩格平主编《全魏晋赋校注》[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6]黄侃撰、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7]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8]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M].北京: 中华书局,1987.
[9][梁]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0]董志广校注《潘岳集校注(修订版)》[M].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11][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卷四十二[M].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2]杨勇校笺《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3][宋]吴处厚著、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八[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4][宋]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卷八[M].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5]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