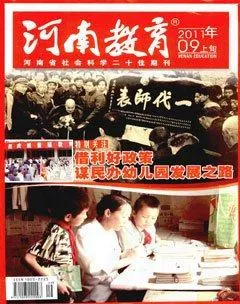新课改走了有多远
2011-12-31周大平
河南教育·基教版 2011年9期
编者按:
2001年秋季启动并逐步推进至今的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在民间被称做“新课改”。回顾过往10年并评价它的得失,在今天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分别由当年参与制订数学和语文课程标准的两位学者担任受访嘉宾。记者力求把他们对课程改革的宝贵感悟,尽可能到位地展现在这两篇回顾中。
“一个政府对学校课程的重视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高度。实际上,一个社会教育系统运行的课程形态,就是这个国家未成年人生活、生存、成长的基本状态;一所学校对学生施加的任何影响都是通过学校的课程制度来实现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刘坚教授,日前在回顾新课程改革10年历程时如是说。
曲折推进的历程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群怀揣梦想的教育人在起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下称《课改纲要》)时,就把凝聚广大教育工作者共识的“为了每位学生发展,为了中华民族振兴”的理想追求确定为这一轮课程改革的基调。
今天看来,这份经国务院颁发的《课改纲要》字里行间充满人文情怀,通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描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期望达到的6个具体目标:强调学生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要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课程内容要关注学生的兴趣和经验,精选他们终身学习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发挥课程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据刘坚回忆,10年前《课改纲要》的所有设计者都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上千年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推动课改蓝图付诸实践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解决新课程理念与现行教育制度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学校,特别是广大师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一轮课程改革不是一次改良,而是一场变革,因此不可能一步到位。”刘坚提供的一份份滚动发展的图表清晰地描绘出本轮新课改的轨迹: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由最初物色有意愿参与的县区加入,逐步发展到以省为单位确定各自实施新课程的实验区的持续推进步伐,直至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全部进入了新课改。高中阶段则从2004年4个省先行实施新课程后,便以年均三四个省份进入的步伐缓缓推进。迄今除广西外,其余31个省级行政区的高中都开始了新课程的实施。
几乎所有认真实施新课改的校长、教师,都经历了“激动兴奋、艰难摸索、或困惑苦恼或分享反思、或徘徊不前或坚定不移”的复杂心路历程。实验初期,教师们很快就产生了“不知课堂上怎么做”的焦虑,因为绝大多数教师的教学经验与教学智慧是“传道授业解惑”,强调的是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教学能力;而新课改却期望教师能够在与学生的平等对话中,和学生一起共同经历知识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还学生学习的主动权,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体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历程。这的确是说易行难!
“课程改革需要理想与热情,更需要耐心与信念。这项涉及千家万户的社会变革,无论事前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设计得多么完美,改革的过程都一定充满迷茫与崎岖。”刘坚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学生在2003年和2004年陆续进入新课改后,很快引发了学术界对课程改革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将新课程置于一个窘境,甚至有多位数学家院士向国务院直言“要立即停止新课标实验”,认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曾有几个省市不同岗位的教育官员形象地说:“前几年我们刚刚迈出一条腿,由于听到学术界强大的质疑声却没有有力的回应,就把迈出的那条腿又收了回来。”
刘坚认为,2004年《中国教师报》刊登的一名一线教师的言论很能代表当时新课程的处境。该教师如是说:“最近颇有一些对新课改的非议,其中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新课改使教学质量下降了,基础教学不扎实了。于是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纷纷下令恢复统考,一些学校也竞相打道回府,教学涛声依旧,练习题重又铺天盖地而来……”
评价的迥异视角
“新加坡的中小学课程,每3年一次小调整,6年一次大改动,这是通过法律规定的。”刘坚说,放眼国际,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以6~10年为一轮的课程发展周期,在这些国家有专门的机构、专业化的团队、专项的经费,用于支撑研究课程基本理论,追踪国际前沿动态,分析课程实施现状,援助一线学校教师。这一切都有赖于足够的经费支持和必要的制度保障。
其实,在对新课改持续多年的是是非非的评价过程中,不乏相关的研究数据充当佐证。2005年,以某省为单位(含14个地市的121个区县)的大样本统计显示,来自课改实验区的小学数学、语文和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的考试成绩都好于非实验区的学生;2007年,刘坚到宁夏一所回族学生占56%的乡村小学听四年级的数学课,在师生互动的课堂上,孩子们有板有眼地交流着对一个数学问题的不同看法,乃至下课后还拉着教师要论个高低。此情景让当时在场的复旦大学附中校长由衷地感叹:“这些孩子比上海孩子似乎更有发展潜能。”
同期,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试图探讨内地小学生学习状况,透视新课改的成效与问题。这个团队分别在河南郑州的一个实验区和一个非实验区,获得了2000多名学生在2005~2008年间的连续测试数据。对比结果表明,课改组学生与非课改组学生在对数学的基本理解与计算能力方面均有较好的表现,平均正确率都超过了80%;而在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方面,课改组学生则明显胜出一筹。项目团队在分析了180节课堂录像后发现,实施新课程的教师更倾向于引导学生做数学,学生更有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表达欲望,更善于将数学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并主动提出问题。
中国的课程改革还引起了国际教育界的关注。2007年,对国际数学教育有着巨大影响的全美数学教师联合会的年会上报告了一项研究成果,项目的牵头人曾是“美国2061计划”数学委员会两主席之一。他的两个博士生帮他在中国做了测试,选用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的17道数学试题,测试在中国的四个地区同时进行,选取每个地区的两所城市初中及两所农村初中做样本。结果,课改组学生的总成绩及各分项知识和能力维度的得分,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同龄人的成绩。
然而,刘坚认为“以纸笔成绩论英雄”会把新课改引向歧途。他追问道,党中央、国务院10多年前决定推进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十多年如一日努力实施新课程,难道都是为了让学生得到更高的分数?中国的基础教育如果放在国际背景下,缺的是“好奇心和求知欲、质疑与批判性思考、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以及基本的公民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刘坚引述20年前国内一位数学家“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的忠告,这位数学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曾经用大刀长矛对付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还在用算得快又准、记得多又牢对付信息时代的计算器和计算机!”
刘坚还提及杭州西湖小学一名特级教师2006年发表的一项“新课程下的小学生做传统的数学题正确率在88.3%以上”的研究结论,以及这位老师对传统数学题所作的透彻分析:“这样烦琐的题目,不依靠时间加汗水的题海战术,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的一次正确率不会高于85%,因为他们的随机错误率较高。现在他们的正确率超过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