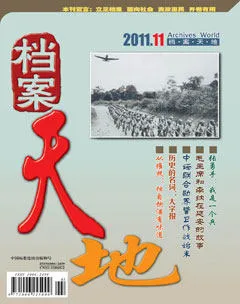我是一个兵
2011-12-31张勇手
档案天地 2011年11期



编者按:
张勇手,原名张永寿,电影演员、导演。山西汾阳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学习,不久被选送到文工团。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文工团团员。
1957年应邀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睥故事片《黑山阻击战》中饰演角色。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军文工团分队长、队长,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导演。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8年后相继在《英雄虎胆》、《县委书记》、《海鹰》、《赤峰号》、《林海雪原》、《奇袭》等片中饰演主要角色。1974年后任导演。导演的影片有《祁连山的回声》等。
崭新的电影生涯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很幸运地来到部队,又在部队里面长大成人。1957年,我们从朝鲜回到国内,那个时候八一厂要拍电影,到我们部队去找演员。那次他们给我拍了一些照片,我试了一遍戏后他们就走了。这对我而言是个很偶然的插曲,我也没在意这个事。这之前我和电影的经历就是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在解放战争的路上,在西北的时候看了一个《沙漠苦战记》,此片讲的是十月革命时期一支红军在西伯利亚沙漠中遭遇白匪马队袭击的故事。另一部是我从朝鲜回来以后,看得第一部中国的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看过这么两部电影,所以对电影的了解几乎没有,电影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我还以为就像我们演话剧一样,一下就下来了。突然间给我送来个剧本,说让我去《最后一个冬天》里面演一个连长。最开始连长是主角,后来剧本七改八改的就改成军长是主角了。我也还在里面演连长,他们通知我到北京去试镜头,我说那好吧,咱们听命令。
到了北京,我连八一厂在哪都不知道,北京我从来也没去过。到了北京我叫了个三轮车,人家给我送到八一厂。进了八一厂大门后,有一个人领我去见了一个导演,叫刘沛然。河北深县人,他就是老《南征北战》里演连长的那个演员。
他身材挺壮,比我长12岁,今年已经89了,他是导演。我就敬个军礼,说我是奉命前来八一试镜头的。刘沛然坐在那,看看我说,行了,你回去拿行李去吧。我二话没说,敬完礼转身,北京一天没呆,就直接回到火车站,换张票我就回南京了。当时我爱人已经怀孕了,我赶快把她给安排一下,把她送上火车回成都老家去。
我把她送走了以后,把家里面收拾一下,到北京来,这是我拍的第一个电影。就这样算是进了电影圈。拍了一年的《最后一个冬天》,最后改名叫《黑山阻击战》,表现的是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期间,我不断地往返于南京、北京和东北之间。拍完后,我就赶回部队文工团。当我在温州练习演出前的工作时,不小心把腰带弄断了,就急忙赶回招待所去买腰带。就在这时,我又接到八一厂的紧急通知,要我回北京补镜头,我连任务都没有完成,什么事也没办就又回北京了。在补镜头过程当中,严寄洲导演又给了我一个剧本《英雄虎胆》,让我演耿浩参谋。我说不敢答应你,因为我现在是被借到《黑山阻击战》摄制组的,我完成这个任务就回去了。
这部戏拍完以后,严寄洲导演积极向八一厂领导建议把我调到八一厂做一名专职的电影演员。在《英雄虎胆》片中标注演职员表时,严导把我的名字“永寿”改成了更具有军人气质和时代感的“勇手”。就这样,我从第一部影片《黑山阻击战》中的“张永寿”变成了第二部片子《英雄虎胆》的“张勇手”,并把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我正式调到八一厂,在剧团安家了。所以我有两个恩人,第一个就是刘沛然,他就这么一句话,嗯,行了,你回去拿行礼去吧,就定了我进八一团这个圈,就进了电影圈。第二个是严寄洲导演,因为他,我才能来到八一厂。
我妻子也一块调来了,她是搞唱歌的,八一场那时还没有乐团什么的,于是改行做了电影化妆。
我这一生当中,应该说呆过两个单位:一生当兵;演了一辈子兵。演一辈子兵是从士兵到将军,几乎每一个级别都有。除了排长,我演过班长、连长、营长、团级干部、师长、旅长、军长、司令、政委。我是当了一辈子兵,而且是从士兵到将军。生活当中我是兵,荧幕形象里面我演的也是兵。
我的“高产”年代
1958年,刚拍完《英雄虎胆》的严寄洲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海军某鱼雷舰艇在南海某海域英勇阻击敌舰,以小艇斗大舰,在任务完成后因掩护战友的快艇撤退,被敌舰击沉,海军战士游了7天7夜,终于游回了祖国大陆,非常感人。作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片,严寄洲接受了拍摄《海鹰》的任务。可能是因为严导认为我身上具有直率、坦荡和军人的气质,他指定我在片中扮演水手长李雄。因为这是个海军生活的题材,我和全体剧组人员一起,到海军鱼雷快艇上与海军战士同吃同住,体验了真实的舰艇生活,晕船、暴晒、水土不服、海浪冲击等等都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好在我有在部队长期生活战斗的经历,也曾经接触过很多类似李雄这样的胸怀宽广的指战员,对角色还是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比较顺利地缩短了与角色的距离,将这个人物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
1960年,是我演艺生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主演了八一厂的两部重点影片,并且放映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一部是描写东北剿匪的《林海雪原》,另一部是反映抗美援朝对敌作战的《奇袭》。这两部片子拍摄之前,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八一厂根据上级指示,厂里的演职人员清一色地穿便服,粮食定量也按照当地老百姓的标准执行,这对于我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来说怎么够吃?好在时隔不久,厂里又给我特批了两斤黄豆、一斤鸭肉,算是给我额外开的“小灶”。当我们摄制组赶往长白山外景地的时候,那里的白雪已经开始融化了,剧组不得不再寻雪景,一些重头戏还得靠人工布景。由于生活气候的不适应,我身上虽然穿着羊皮大衣,但在那样的环境里,还是觉得冰冷刺骨。结束外景地回到北京,已是盛夏。根据剧情的需要,还要在内景点火烘烤。我和演员们依旧穿上羊皮大衣,围坐在炭火旁,其滋味可想而知啊。《奇袭》虽然是反映朝鲜战争的情节,但是整部影片并没有在朝鲜实地拍摄,其外景地选择在浙江奉化,因为那个地方的地貌很像战争,又赶上那个季节,因为在北方已经焦黄了,那个地方还是葱绿的。我当时28斤的粮食定量远远不够,每天还要起早贪黑地拍摄。我在影片里扮演一个智勇双全的侦察连连长,我调动了自己曾在朝鲜战场的亲身经历,使人物的内在气质和外在特征相结合。其中那个跳车的情节,我觉得是很精彩的。我一次完成,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我看好了地形,摄影机一开机,啪,一下跳下去,摄影师都惊魂未定啊,拍成了。
这个《奇袭》救了八一厂,也救了我们。后来谢晋导演都说,那时候《奇袭》是代表作。全国广大观众都很喜欢《奇袭》,尤其是上山下乡那批人,现在见到我就像是那铁杆儿粉丝,在哪儿碰到都要照相的。
这些年中,我很幸运地参加了一些电影的拍摄,扮演了一些角色,《赤峰号》、《林海雪原》、《奇袭》、《英雄虎胆》、《海鹰》和《打击侵略者》等为观众们熟知。当时,我和本厂的王心刚、上影厂的冯喆、长影的庞学勤还曾被观众们称呼为电影界的“四大英俊小生”。
在“文革”大浪中漂浮
1965年,总政治部在全军开始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在一次学习会议讨论中,我坦率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分为二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不是也能适用在对毛主席的学习上。这下可惨了,原本正常的学习讨论,却被上级认为有重大的思想政治问题。保卫部为此成立了专案组,专程跑到我的山西老家和原来所在部队进行调查。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些事,这还是后来政治部的人跟我说,我到你们勇手家乡去了三次你知道吗?调查的结果都评价很好,而且在朝鲜战场上还立过两次功。现在想起来,多亏了我的出身,否则的话,后来我不定什么样子呢。一是没查出什么可联系上的依据,而是后来“文革”愈演愈烈,整个社会形势乱了,对我的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期间,正好赶上江青要抓文艺界事情,她还要抓军队的戏,要抓军队的电影。于是乎,她就要重拍《万水千山》。这件事提出来后,他们就在全国物色演员,一批一批人选送到江青那里。江青看了以后说你们怎么回事?怎么找得都是些丑八怪啊?她随后问,王心刚、张勇手他们在干什么?她可能看了我演的的《奇袭》和《海鹰》,对我印象比较深。旁边的人说他们犯了错误,江青说什么错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没杀人也没放火,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出来工作?就这样逼着他们解放了我们。
我们到《万水千山》摄影组去报到,像罪人一样进到摄影组去,算是戴罪立功了,感觉是这样。虽然我们的表现很好,但这部《万水千山》却时运不济,拍了一半又停了,什么原因到现在也不知道。此时,江青又看中了另外一个重拍的题材——《南征北战》,我又被选进这个剧组,饰演高营长的角色。
这个期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革委会集合,也不知道什么事,到那以后上了车就给拉走了。一直拉着我们到了东方宾馆的“样板戏”摄制组,我一看还有好多芭蕾舞团的人都在这呢,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然后又上车,把我们大家拉到了钓鱼台,进了什么楼我也不知道,黑灯瞎火的。后来到了一个大走廊,里面有一个长桌子摆在这。江青坐在最头上的位置,那个地方有电铃,她有事就按电铃招呼警卫人员出来。她的一侧坐的是政治局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另一侧坐着我们去的这些人,我坐在离江青对面最远的一个地方。说着说着,江青就突然说这个张勇手,你怎么坐那么远啊?过来过来。她座位旁边还空着个位置。我敢不坐那去吗?我就坐那了,很不自在,但非坐那不可。江青的讲话后来又说到了我,她说我看你这个人还有点童心,怎么样?你拍部儿童片吧。亚丁(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你给他找一个好的编剧,让他们到学校去好好生活一段时间,给他拍一个儿童片,好不好?陈亚丁说好,回去马上安排。接下来江青又问我说你是坐车去还是骑马去啊?我说我们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汽车去。江青满意地说那很好。
后来的事情就得按照她的意思办,我就到西四北小学,中关村小学生活,在那天天上班。可是,深入生活之后,我却碰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儿童题材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可能是由于军人出身的缘故,我对儿童题材很不熟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最终就也没弄出个什么结果来。但是,有了江青的一番话,我回到厂里就调到导演组了,原来38斤的粮食反倒减成了28斤。我跟厂里的领导还说不对啊,没经过我同意你们就给我调导演组去了。那时候就是这样,世事难料,事事不由己。
无意中成为了“伯乐”
1975年,江青又心血来潮想把1959年由王心刚、王晓棠主演的《海鹰》重拍一下,江青发了话就得落实啊。所以,八一厂决定让我负责成立摄制组重拍《海鹰》。
相隔十多年之后的重拍,我和王心刚那拨人显然年纪都偏大了,需要找一些年轻人,但是他们决定要我来担当主演的角色,王晓棠演的那个角色还要找年轻人。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于是乎就到处散开去找,我也专程跑到成都军区。到了成都军区以后,见到了成都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他说我们这个军区很可怜,没什么人才,但是有一个人你倒是可以看看,她会唱样板儿戏,还会洋琴什么的,她叫刘晓庆。我说那叫我看看吧。部长告诉我她年纪不大,但是她现在在重庆十三军慰问呢。
因为我的任务很急,我想尽快去尽快回,所以我就找到了成都军区的副司令,也就是我的老军长。老军长说没有问题,这个军区我可以给你调动飞机,送你到十三军区,办完事以后在机场等着你,然后你再回到成都来,这行不行?我说行,于是乎我就这样到了重庆。
到了十三军马上就去看刘晓庆,当时刘晓庆刚洗完头,正在梳头。我说你梳你的头,我就噼哩啪啦前后左右给她照了像,然后就走了。到了北京把照片洗出来给大家一看,大家说这姑娘不行。我说不不不,这孩子有个特点——大脑门,我拍摄技术不行,要不这样,咱们跟成都军区商量一下,打个电报请他们让刘晓庆到八一厂来试个镜头。刘晓庆到北京一试镜头,妥了,就是她了。
还有一个被我挖掘出来的人就是唐国强。当时要拍一个叫《西沙之战》的片子,后来叫《南海风云》,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在物色演员的过程中,听说了青岛市话剧团有个叫唐国强的演员不错,我就决定去看看。
当时唐国强正在济南演出,一看我就说这个小伙子可以,就定了他来演《南海风云》的男主角于化龙。刘晓庆可以演那个妹妹嘛,但是仔细想她感觉比唐国强大,所以这个时候八一厂正好同时拍的《南海长城》中缺一个甜女。李俊导演跟陈亚丁部长说把刘晓庆调到我们组来演甜女,让他找一个女孩儿演小妹妹,于是我就把刘晓庆给调到《南海长城》去演甜女了,我又找了洪学敏来演的这个唐国强的妹妹。这样,两个摄制组就同时到了海南岛拍摄。
刘晓庆和唐国强就是这样踏入电影行当。他们越来越红,被广大观众所熟知。两位演员成名后也都没有忘记我,唐国强总跟人说,张勇手才是我真正的老师。刘晓庆在一次过生日的场合,她跟大家边介绍边说:这是我的母亲,没有我的妈妈就没有我刘晓庆。第二个人就介绍我,没有张勇手就没有我刘晓庆的今天。
我这一辈子这样算起来,应该说一是在电影界演了几个军人角色,拍了几部军人的电影,还参加了一些电视剧的演出。再一个就是我发现了两、三个人,做了几回“伯乐”。
我的普通一生
1993年的时候,可能是拍戏累了一点,突然之间一下就得了两种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糖尿病。本来很丰满的很胖的人,一下子瘦成人干了。我感觉患病的原因与高原生活有很大关系,《祁连山的回声》、《彩色的夜》和《沉默的冰山》都是在高原上摄制完成的。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休息,我的身体得到恢复,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接拍一些影视作品,比如《彭德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执导的影片。不过,这时候我已临近离休年龄,我将一纸离休申请交予领导,开始了崭新的离休生活。
离休生活并没有使我感到丝毫的寂寞,很多朋友前来找我,有的还是急茬的,说张老师快帮个忙吧,有个角色您来最合适。这当中有电影,也有电视剧。另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是公益活动,都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开车去郊外钓鱼,但我不会吃我自己钓上来的鱼,我舍不得。我喜欢钓鱼就是为享受钓鱼过程中静与动的关系。我性子急,钓鱼能使我静下来,可以磨砺我的性格。退休后有好的戏我也去拍,不知是与我们当年拍戏风气不同还是什么原因,老爱发火,发过后我又很后悔,可就是控制不好,钓鱼使我改变很多。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我与老伴享受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最初在怀柔的山里置了块地,自己建了房子,每年的夏天就去那里住。院子里种有梨树、枣树、李子树、石榴树等果树,到了秋天,树上结满了果实,让我们享受着丰收的喜悦。我属狗,特别喜欢狗,所以还养了两条大狗,我们每天去爬山、去钓鱼,真是世外桃园的生活啊!就这样在那里住了七八年,后来年龄大了,孩子们不放心,不让我们去住了,狗我们也送人了。不过现在我们住的家里也养满了各种花,有阳光花房。
我这一生,我认为是很幸运的。至于说到我做的事情,那也无需过多地去渲染。人的贡献有大小,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重要的是能做多少做多少,要尽己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