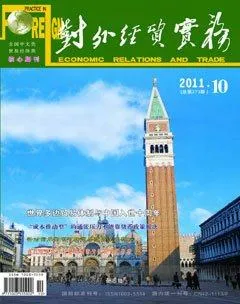我国“入世”十
2011-12-29蔡德林
对外经贸实务 2011年10期
今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在这十年中,我国平稳度过了过渡期,初步实现了在观念上和制度上的一系列转型和与国际接轨。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十年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也给我国经济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障碍,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新问题。这一方面表明,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在体制上和结构上存在诸多问题,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
一、理性看待“中国模式”
2004年5月,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所谓“中国模式”,从此名声大振。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这使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再次受到热炒,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拯救世界”。 英国《卫报》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了“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但在2009年接受媒体专访时他却宣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在国内,由于我国加入WTO的表现,尤其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部分媒体和理论界也开始热衷于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与宣传。似乎“中国模式”已具备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相提并论或互补的重要价值,不仅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对西方发达国家也将具有划时代的启发意义。面对 “中国模式”存在与否,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从此,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如果用客观、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总结这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用一种“模式”来概括,恐怕为时尚早。因为,模式是一种比较固定的发展方式,并经过历史的检验,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和推广价值。但任何模式都不可能像电脑操作那样,复制、粘贴即告完成。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公认的模式,但在不同国家,又会衍生出不同的“次一级模式”。像数学公式那样的模式是不存在的。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不同制度的选择、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国家,也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繁荣与发展。但至今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可以借鉴的所谓“模式”。如上世纪30年代,西方正在经历经济大萧条,而此时苏联的经济却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开始怀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而推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在上世纪末,伴随日本与韩国的崛起,国际上又开始热议“东亚模式”。亚洲式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推崇。等到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走向衰退,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模式黯然失色。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不能脱离原有的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没有成功的先例。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尚未达到“对岸”时就形成一种所谓的“模式”,明显不符合逻辑。西方人炒作所谓“中国模式”,并不是对“中国模式”的认可和欣赏,而是以“中国模式”的名义,“捧杀”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9年两次G20峰会上屡被提及的“G2”概念,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中美共治”时代。按照西方的逻辑,既然中国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应该对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其实质就是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因此,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对中国减排的承诺表示“赞赏”。如果我们失去警觉,陶醉在西方人的“热捧”之中,按照连我们自己都认为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去发展,其结果就会丧失改革与发展的良机,甚至前功尽弃。
二、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济转型正式拉开序幕。为加快市场化改革,与国际接轨,我们在市场化初期便申请加入WTO。这反映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对融入国际社会的期待。由于在国际上未能确立市场经济地位,我国是以“非市场经济成员”的身份加入WTO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因此规定了一些“特殊”的不利条款,尤其是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致使我国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并被一些国家“特保”。
回顾我国加入WTO的10年,初期的改革,不仅决心大,而且动力足。正因为如此,我们搭载着国际化的列车,利用WTO的“红利”,把我国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享受着世界工厂、最大出口国、外汇储备第一、中国崛起、G2等一系列美誉。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早已被抛到了脑后,是否需要继续改革也遭到质疑。若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轮胎特保案”的发生,似乎还不能冷静下来反思,我们自身是否出现了问题。
其实,我国改革的基本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正如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的,我国经济的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种认识从上到下应当说都是清楚的。问题在于,当短期的发展机遇来临时,我们会更看重眼前的利益,甚至会盲目乐观,热衷于“中国模式”,将原本应当改革的难题一推再推,以至于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不难想象,以现有的发展方式和我们的比较优势,环境与资源的过度透支,能够持续多久。类似于重商主义的无限度出口和美元的积累可否持续;不以内需为主,而把经济命门系于国外,甚至某一国家是否存在巨大危险。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仅需理性与常识。
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伴随经济成就的取得,我国改革的速度明显放缓,改革的动力在丧失。我国的改革是由政府推动,政府主导的。包括路径的选择、利益结构的调整、政策的制定、进程的控制等。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同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是不能回避的。以改革主导者为中心,遵循由易到难,由外到内的改革路线图,如今的改革已经改到了“难处”,改到了改革者的“家门口”。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率先实行改革领域的群体已经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并期盼着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来实现共同富裕,共享改革成果;而未改革、或未彻底改革领域的群体则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这就使今天改革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有压力,无动力,而不继续改革又不能寻求更大发展。
我们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甚至更高,相关法律制度也已基本建立。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这种认识是一种浅薄的自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僵化思维惯性的典型反映。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不反映在有形的市场上,而体现在潜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平等、自由、权利、责任、自律等法治和道德精神。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中的乱象丛生,集中表现为有市无序。因此,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不能量化的,更不能用GDP去衡量。我国目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应当从本质上去寻找原因,就事论事,只能是疲于应付,按下葫芦浮起瓢。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建市场易,立制度难,树精神更难。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成就,并不体现在近一二百年里。没有从中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等,不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不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彻底改造与升华,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而我国历史上始终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过程,等级制、特权思想、官本位、潜规则等根植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先天缺乏市场经济中的观念要素,对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认识和理解相当肤浅。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捷径的探索是有限度的,也是有危险的。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浮躁与盲目乐观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
三、走出对国际市场的“路径依赖”
加入WTO是我国政府智慧的选择,不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经济难以快速起飞,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但国际市场不是无限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也都是暂时的。如果不加节制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全力走向国际市场,不仅有悖于WTO的宗旨,也不利于本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更不能持续。WTO规则如果不能让每一个成员获得“红利”,就会走向他的反面。
据工信部的数据,2010年我国工业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6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4.6%,1990年是16.1%,2000年是20.8%,2007年是37.5%。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开始有所降低,但仍居高不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德国的出口占GDP比重(39.9%)高于中国(37.5%)。至于其他国家,美国8.4%,日本16.3%,英国15.7%,法国21.6%,意大利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