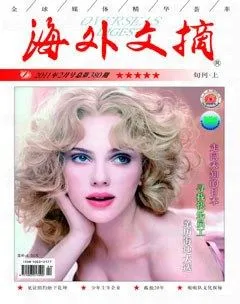“零一代”
2011-12-29本.马歇尔
海外文摘 2011年2期
他们年纪轻轻,熟悉高科技,爱旅游,爱上网;他们视身外之物如粪土,不在乎自己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工作;他们是“零一代”,正为21世纪的生活打造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模式。
每两个月,杰西卡·唐和妹妹就会从马盖特的家来到伦敦购物。 但与妹妹最终“拎着大大小小的包”不同,在逛遍整条牛津街后,唐会独自一人走开,去领略这座城市的魅力。唐是英国目前不断增加的特殊年轻群体“零一代”的一员,他们认为,拥有的东西越少,能实现的目标反而更多。
“与大多数朋友相比,我的衣橱只有她们的1/4大。”19岁的唐穿着简单干净的短裤和白色的无袖上衣,她说话激情四射,但思想深刻。“每种类型的鞋我只会买一双,一双旅游鞋、一双高跟鞋……”唐对物质缺乏兴趣,在她利兹大学的宿舍里,除了几本课本、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苹果手机,别的什么也没有。
你想要的东西总是比实际所需来得多,只要抛弃无关紧要的东西,你会发现,生活竟然越来越好。
唐在小时候就见证了消费主义的枯燥无趣。“35年前,我父母就移居到了英格兰,”她说,“他们从越南过来的,所以一穷二白,只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爸爸是工厂的工人,整天缝制衣服,但是他慢慢爬了上去。现在,他给很富有的人定做背心。”唐还记得父母努力打拼,只为了过上好日子。他们从小公寓搬进了大房子,从普通车换成名车,可等最后买到手了,却又看上另外一辆更高档的。“他们总有目标,从不满足于现状。”
唐在中学时就刻苦学习,同时还有两份晚上的兼职——一份是在电影院,还有一份是在快餐店。就在那个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不愿意和父母一样。“我很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很多事情都没法做到,连大学都上不了。但我只是觉得,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5点并不是为了物质享受。”
唐真正想做的事情是旅游,如果你闲不住的话,就不应该被任何地方或者身外之物缠住,这是极简主义生活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不太愿意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住房贷款和安全、长期的工作合同好比凤毛麟角。这样做有好也有坏,他们可以更自由,会花掉手中的钱去见识这个世界。
凯利·萨顿23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软件工程师。他在德国学习了4年,回家后发现走之前留下的物品竟然有10大箱之多。“我基本记不得这些箱子里都放了什么,”他说,“我恍然大悟,如果都记不得有什么东西,或许就不该留着。”于是他上网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卖掉或送人。现在,萨顿住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他只有一个小衣柜,以及许多最新的移动硬盘。萨顿说,多亏了数字技术,一书架的书、CD和DVD的内容都可以储存在一个硬盘上。因为萨顿没有花钱花时间把自己的住处弄成“挂满装饰品的圣地”,所以闲暇的时候,他不怎么待在那里。萨顿更喜欢出去和朋友聚会,看电影,去野餐,去派对。结果,他成了“更懂交际、更快乐的人”。他并非选择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其实,他对比较昂贵的衣服也有兴趣:“我只有4条裤子,几件衬衫。我认为,与其花300美元买10件衬衫,还不如花同样的钱买3件,买太多东西是很荒谬的。”
他会不会尤为怀念哪样物品呢?“我曾一时冲动把自己最心爱的几样东西打成一包,寄给多伦多的一个家伙了。一开始我肠子都悔青了,心想‘哦,天哪,我还是想要那些东西的。’但那种感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怀念。”
普及极简主义的关键是科技的进步。这股极简风潮的流行,恰逢数字下载、流媒体服务、云计算等等科技的兴起——这一点绝非巧合。因为用户可以在网上储存文档,从而把网络转变为一个储存空间,不仅容量无限,且随时可用。很多年轻人因此长时间泡在网上,对物质的需求和占有欲几乎为零。
赫敏·韦尤为如此。韦今年26岁,她经营着一家名为newspepper.com的网站,为网络媒体提供视频。她的办公地点就是她经常去的一家咖啡馆,办公用具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可比在伦敦闹市租下一张办公桌便宜多了。我们见面时,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裙子上缝了一个大口袋,专门用来放iPad。科技就是她的生命。除了瑜伽,她说不出任何一个与电脑无关的爱好。“我在网络上的身份和我在网络上的言行,都比我真实的身份重要。”她说,“我通过Facebook和Twitter与人交流就可以挣到钱。”
韦在伦敦与人合租着一间小公寓,她的室友正准备搬家去美国,为了运一大摞DVD和唱片,就花了许多钱。“对我来说,这种做法简直不可思议。”韦说,如果是她,她会把唱片放到eBay上去卖掉。她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列出了自己的喜爱音乐列表。“这就和请朋友到家里来喝杯茶、看自己收藏的唱片是一样的。在网上列出来,虽然没有和朋友面对面,但也是一种分享的体验。为了编好这份列表,我花了很长时间。虽然它不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意味着我对它没有感情。”她有没有对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产生深切的感情呢?“我祖母的一枚戒指,她已经去世了。”
阿莱克·法莫是一名21岁的学生,主修设计。他只有1双鞋,1双靴子,4件T恤,3件衬衫,3件毛衣。他深爱极简主义:“东西越少,效率越高,生活越轻松。”这样一来,作为一名学生,他能常常更换租屋。“我可以早上打包,挂在自行车后面,然后骑着车走天涯,”他说,“虽然我从没这样做过,但我的确有能力这样无忧无虑,这种感觉真好。”
极简主义者会有一种自我提升的成就感。分析自己要买的东西合不合算,自己的开支是否合理,这个过程会使你同时关注所需和所有,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会日益结合起来。法莫承认,要以这种方式生活,最难克服的就是对某些物品难以割舍的情感。他喜欢旧书的香气,尤其是几本有关设计的珍藏本,他不太愿意把这几本书转换成电子版本。
“这个过程迫使你扔掉具有特殊情感的物品,因此最终留下来的最具特殊意义。我是那种会保留前任女友东西的人,”他解释说,“比如,你整理出自己的东西,按照情感强烈依次舍弃。一开始你有100件,最后你会发现只要5件就能概括生命里的一段友谊或一段感情。”
极简主义并不是僵硬死板的教条,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会被其所吸引,这也说明了极简主义的无穷魅力。唐说:“我马上要去日本完成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如果我有好多依恋的物品,那肯定很难打包。但现在,我只需带上快乐,跟着我踏遍天涯。”
[译自英国《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