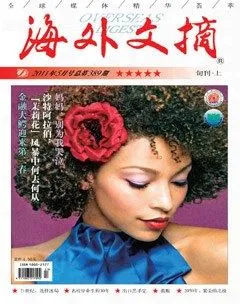80后留美学生日记
2011-12-29徐潼
海外文摘 2011年5期
在大洋的另一端——美国俄亥俄州,漂泊在外的留学生正经历着一场美国文化与教育的洗礼,同时他们也深深思念着祖国的亲人。让我们跟随作者的日记一起感受美国留学生活的苦与乐吧。
2010.9.23
中秋节那天是我在美国的开学日。那月亮,在哪儿都是圆的。
今天是我导师的课,热闹非凡。三十几号人围大圈做游戏:某个人提一道诸如“谁爱吃巧克力”的问题,其他人以往前走最多5步的动作作答。走5步就是狂爱吃,走零步就是不爱吃。下一个问题将由走零步之中的任意一人提出。
第一个问题来自我导师:谁爱吃冰激凌?大家瞬间做哈喇子兜不住状,“我!我!”挤到大圈中央。
下一题由我这位零步者来出,犹豫了0.1秒后我发问:谁喜欢讨论星座?霎时,冰激凌的狂热场面无影无踪。我自己抢先走到大圈中心,另有四五个女孩儿加一个男孩也跟过来。意外收获是,我导师竟左摇右摆地往前迈了3步说:“呃,我也有点儿信。”一脸孩子气。
“我是水瓶座。”导师举手。
“我双子。”我紧接。
“巨蟹,巨蟹,巨蟹……”巨蟹女们击掌。
一堂课下来,我很庆幸能有这样的导师,他的课太赞了!
下课后赶去和上海的镜如兄一起吃鸡翅,这可是我们在中国就已经约好的!
饭后一个人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不小心看见幽蓝天空中,透亮的圆月淡定地挂于薄云之间,好轻。
一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好轻。
2010.9.25
秋天你好。
昨天下午的课叫做学科整合方法,意在研究如何整合“艺术学科”于其他课程,即把艺术形式融合到各门中小学课程中。我们跑到学校艺术中心的地下小剧院去上课。两个导师,加上一位“艺术家”嘉宾。
嘉宾把作品用幻灯展示给我们:室内植物——生存于纯天然的自给自足系统;鱼屎肥料——为盆栽提供养分;泥土里的蚯蚓和昆虫——用多声道扩音的方式,让参观者聆听其一举一动,等等。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自己都不懂。
对于她为什么要专注于植物、鱼屎、昆虫,并称其为艺术,把这些人们想都不愿多想、更别提观察的玩意儿举到大家眼前,逼着同学看个够,我毫无共鸣,感觉莫名其妙。无法抑制的不耐一股股泛上来,我看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小宇宙,无力融于它,也无力融它。然而,且不说她作品之意义,她所叙述的每一个创作和建造过程,却令我敬佩。她并非专业工程师、电子技术员、视/音频处理设备发烧友,只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但她行动起来,将奇思妙想付诸实践,不断学习,不断失败又再次试验,不断求助于专业人士,直到整个设计的实现。这个过程,不正是“艺术整合”吗?
一个学生(他本人已教书多年)总结说,孩子很容易反感阅读和写作,因为它无聊、太虚。而这样一个基于兴趣的动手动脑过程,促使大家自发地查阅参考书、记录数据或制作过程——恰恰自然而然地将阅读和写作融于其中。我十分赞同,并深受启发。
哥伦布最近很热,怪怪的热。连早晚都不冷。刚才房东跟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热。明天开始,真正的秋天会来。2010的尾巴,我欣然迎接你。
2010.10.2
北京的父老乡亲,你们好吗?给大家请安。我很好,请各位放心。
昨天在网上先碰见我爸,问他是不是要上班,他说国庆了,上什么班。接着,QQ上有当年幼儿园的梦梦酱同学加我,“尘世”几句,我随口又问,你在上班吗?她说国庆啦,放假啦。最后跟小雅闲聊,她说稍后下线,追问原因,答:回家过节!
今天傍晚的课,是在艺术中心的地下小剧场听讲座,一个教育领域的“艺术家”主讲。
他给听众放了个视频: 流动的水面不知是浮着还是悬着一张僵硬的地毯一动不动。音轨是水边的环境:青蛙、昆虫、风和树,很轻飘。这个视频的题目是:地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展开讨论:第一个问题,你看见了什么?第二个问题,从你看见的东西,想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想到了它,你疑惑什么?第四个问题,总体上,你感觉到什么?逐层深入,越展越开。我说水面让我想到了家乡;艺术家先生问:你哪儿人?答:北京,没水。而后一同学说,他想知道这景色拍于何方。艺术家先生答:北京。全场爆笑。
整个讨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多数美国发言者的终极发散,趋于积极——不同文化可以融于同一天地,无论种族、性别、价值观云云。我和身边的台湾姑娘,看到的却是相对压抑的暗面——地毯想要逃离陈规,拥抱自然,而它终究无法随水遨游,向往并失望。这时艺术家先生看了看表:“咱们的讨论已经进行了55分钟。”不可思议,授课转瞬即逝,却沉沉甸甸。
2010.10.24
尼尔大街和八街十字路口,每个街角都有深浅棕黄的房屋。树开始变化,一棵就有三色。汽车发动机的轰隆起伏,不知远近。前天月亮还在这里,明天就去了那里,像生蛋黄,本有形,却不抵空气的挤压,瘪了这里,鼓了那里。窗外行人的闲谈寒暄,跟胡同没两样,分不清语言。人到底有多相像。迎面而来的微笑,是无数个温暖沉浸的瞬间。侧脸斜眼的苍白,是少数的惊醒瞬间。在这片越来越不陌生的土地上,我还会留下多少脚印。什么时候,鞋底的泥土,会随我重返它的新家,我的老家,那片或许将令我不再熟悉的土地。一个人躲在空旷凌乱的房间里,像一种自我软禁。虽不敢说自由必生于自我解放,但自我解放或可驶向自由。解放非放任,是责任。比起实义动词“放”,它更接近于“收与放”的结合。对于该做却没做的事情,若有本事想出1000个理由给明天去做,便有本事想出2000个理由、干出3000件除它以外的事而导致明天没有做。因此,做事情,不要想,去做。逃避事情,没有理由,等于死。想,就是制约,就是偷走全部时间的恶贼。在尼尔大街和八街的东北角,我想了太多,做了太少。冬天就要来,尊敬的“思前想后”小姐,请冬眠。勇敢的“解放”先生,请起床。
2010.12.28
圣诞历险记,地点:易家
圣诞前夜,家里没活动,众人早睡;只剩易爸、易弟、易和我,晃在餐厅游手好闲。
易弟的大儿子,3岁的盖盖,可爱的不行。他每句话的开头语必是:你猜怎么着。你猜怎么着,我屋子里有电影,你要看吗?你猜怎么着,我屋子里有玩具总动员的玩偶,你要玩吗?你猜怎么着,这个东西可以让声音重生——易爸送给易的圣诞礼物之一,一个吉他功放。易二哥是四兄弟中最拽者,我行我素全不在乎,不讨好不迎合,除了酷还是酷。有幸接受到他的访问,关于中国三五题。问: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答:没有,我们计划生育,所以视堂表亲如同兄弟姐妹。问:原来如此。那中国现在对同性恋话题是什么态度啊?答:自从超女之后,同性恋比率激增。年轻人对此基本表示理解,上一辈还是够呛。哦……他点头。采访告一段落。而后易又同二哥连唱带弹几小曲,易弟也加入——三兄弟气场之强大,难以言表。终于,易大哥捧着水杯倚上门框,对弟弟们的自我陶醉淡定观望。这是什么?这是家。
圣诞当天,圣诞树下的礼物堆眼看就要爆炸。于是,拆封的战斗一炮打响。一件一件又一件。你们是有多少东西要送啊……我的老天!尤其是孩子,大小盒子拆也拆不完。
回哥伦布的路上,我想起易爸说过的话。他向大家提到曾经教我玩儿扑克的一个插曲。他知道,对于初学者,挑战皆来自对于扑克排序重组的记忆。我们早习惯于视A为最大牌,不料想有天J也能出头。规则变了,境遇变了,曾经最强大的因素也在变。人生的大游戏里,或许我们都不免面对这一变局。你从未太过重视的人、事物,在新的背景、新的方向、新的希望中,升为首要;你从前总也放不下的人、事、物,终于退居后线。重整自我,是当下的你,改变历史的起点。于是,你决定你的未来。
仍在回哥城的路上,易有些许失落,出于对家的眷恋不舍。我能理解,那是惟一的起点加终点。我们都知道,无论你走多远,走到哪儿,如果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那就是家。不管你有多挫败、多孤独、多恨,如果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疗伤,那就是家。家,是最好的返程。但在此之前,要先学习和经历另一样东西,即离开。
所以,就让我们好好体验当下的一切。
2010,再见!
美国俄亥俄州 哥伦布
(本文作者徐潼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早期儿童教育研究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