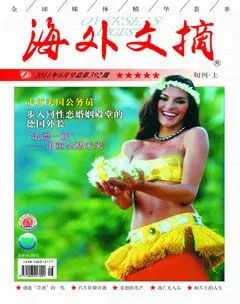我眼中的叙利亚
2011-12-29刘辰
海外文摘 2011年6期
和大部分国人一样,我一直认为阿拉伯民族是一个精力过盛的民族。新闻报道中从未间断的巴以冲突、叙以冲突、黎以冲突,还有中东各国内部的宗教和党派斗争似乎都在向世人宣告,中东这片土地永远充斥着纷争。然而,一次真实的中东之旅却使我对中东的感情由排斥变成了热爱、沉醉,直到现在的无尽回忆和思念。或许有些地方我们一辈子都未曾想到会去亲身感受,但在叙利亚这个神奇国度,《一千零一夜》中的传奇仍然在这片迷人的土地上发生,并将延续千年。
大饼与糖茶——热情点燃生活
2008年10月,我作为一名政府交换生前往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当我们一行辗转颠簸抵达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拖着疲惫的身子,拉拽着每人近30公斤的行李等候前往市区的巴士时,在机场外贩卖当地食品的一位叙利亚大叔给我们送来了本地特色的大饼和甜茶,热情地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向我们说着“朋友”、“欢迎”,将我们旅途中的劳累顿时驱散得一干二净。
大饼在阿拉伯国家可谓是一大标志。叙利亚政府甚至有一项“大饼补助”,为困难户免费提供大饼以满足生活基本需要。除此之外,叙利亚人还把大饼当成“塑料袋”,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大饼简单地包裹起来,着实令人惊叹。
叙利亚的茶更是颠覆了我们中国人对茶的传统理解和认识。当地人毫不吝惜地往茶里加糖,无论是什么茶,经过叙利亚人的加工,都成了极甜的糖水,不过搭配上叙利亚极富盛名的点心和坚果,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叙利亚的经济正在经历一个由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她不像海湾阿拉伯国家那样,坐拥宝贵的石油资源,加上这些年美国残酷的制裁和封锁,叙利亚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老百姓生活水平也没有什么提升。物资匮乏、物价上涨以及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一直困扰着叙利亚人。尽管如此,叙利亚人热情好客的天性不变,简单朴素的生活造就的是一个个朴实真诚的灵魂。当我们一行人在叙利亚的哈勒坡、哈马、拉塔基亚等城市旅行时,总能听见当地人热情地问候——“李小龙”、“成龙”,这些中国功夫巨星的名字成了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的代号。
不得不说“中国制造”在叙利亚有着巨大市场和人气,小至儿童玩具,大至马路上的豪华巴士、工地的先进机械设备,都来自中国。当地的商人也说,中国的商品质量不错,价格要比同类的日韩、欧美产品便宜得多,非常适合叙利亚的市场需求。另外,音像店里越来越多的被译成阿拉伯语的中国电影、电视剧也已成为叙利亚百姓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中国功夫,中国的戏曲、书法也在叙利亚颇受欢迎。大马士革大学的许多叙利亚人都参加了学校的中国书法社团,学习中文,研习书法,还时不时给我们哼上几曲地道的中国古典小曲儿。想必这就是朴实无华的叙利亚人心中那份中国情结吧。
宗教与文明:包容、和谐、繁荣
抵达叙利亚的第一个星期五,我们终于见识到了伊斯兰教聚礼日的壮观景象。我们正在寝室准备午餐时,远处的宣礼塔传来了宣礼员高亢的声音,敦促穆斯林到清真寺进行礼拜。我们看到宿舍楼下杂货店的老板有条不紊地把礼拜毯铺在地上,跪坐下来,虔诚地念诵着礼拜词,对着麦加朝拜。而此时正要去买东西的外国留学生则会礼貌地候在店门外,敬畏地注视着店内神圣的宗教仪式。沿途的商铺上至店主老板,下至清洁工,无不放下手中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伊斯兰教“五功”之一。有时在清晨四五点,我们还沉浸在睡梦中,宣礼塔就已经在召唤虔诚的教徒们进行大净、小净。我们乘车行驶在大马士革至邻国黎巴嫩的公路上时,路旁甚至有停下车、跪在道路两旁做礼拜的司机。叙利亚人对宗教的忠诚和热爱让我们敬佩,我相信,不论现实中有着何种苦难,人生道路何等崎岖,心中的信仰总会是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
来到叙利亚之前,我曾以为这里的人们对于伊斯兰教的热爱乃至狂热使得他们不会轻易接受其他宗教思想,也不会允许其他文明在这里发展与繁荣。但是,就在叙利亚美丽的海滨城市拉塔基亚的基督区,我的相机记录下了一张和谐的宗教图景——基督教堂的十字架和伊斯兰清真寺的星月标志和谐地出现在一幅图景当中,交相辉映。
不论是在大学校园,还是在繁华的街上,衣着时尚的女子总是能引起我们的好奇,因为我们原本以为阿拉伯女人都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门。其实不然,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基督教等宗教的吸收与融合,叙利亚社会已经抛弃了一些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和法令,给予了人们更大的世俗自由。谨慎、保守、浪漫、开放,我想这些矛盾的完美融合也只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才看得到吧。
叙利亚地处西亚沙姆地区,连通东西,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更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相辉映的大舞台。西方芭蕾和传统阿拉伯舞曲的完美融合、节奏鲜明的阿拉伯式摇滚、别具一格的阿拉伯说唱,这些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西化现象,倒不如说是一种宽广的文化包容心态。正是这种包容与开放,使得叙利亚这片土地保留了数不尽的文化遗产和古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如果这世界有天堂,那么这天堂必然是在大马士革。我曾经在倭玛亚清真寺门前结识过一位参加过两次中东战争的老兵,他告诉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同时记载着五个以上文明的发展史,那这个地方只能是叙利亚。的确,没有人能够完整无缺地讲述这里的古老、悠久的过去,也没有人能够预料这个东西合璧的地方未来会走向哪里。叙利亚的宗教与文明如同这位老兵一样,逐渐老去但光芒却日渐灿烂,也像这里的百姓一样,低调朴实地生活着,从不向他人炫耀自己无尽的历史财富。
夹缝中生存:宽容、倔强、勇敢
我在大马士革大学文学院有一位名叫哈马德的朋友,他在学校攻读近代西方文学,而他的知识面远不只局限于文学领域。他曾给我详细地讲述历史上阿拉伯文明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当我们谈到以色列这一话题时,我的朋友告诉我,如今的叙利亚人想到的不是血债血偿,不是无休止的争端和报复,他们只是想要一个正式的道歉。
宽容并不等同于妥协与退让。我们在叙利亚留学那年的冬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阿拉伯平民伤亡。那段日子里,每天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叙利亚人前往大马士革的阿萨德广场进行游行抗议活动,有时甚至能看到一队队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参加到抗议的人流中。
在叙利亚有着这样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没有叙利亚,中东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就足见叙利亚在中东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我们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血腥冲突、恐怖袭击根本与叙利亚没有什么关系。叙利亚人过着的是一种舒适、恬静的生活——做礼拜、一大家子一起招呼客人、三五个好友围坐在一起吸水烟聊天,这才是真正的叙利亚生活。叙利亚人渴望和平,并身体力行地维护和平。在大马士革居住着许多欧美人,他们也并未像我们当中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饱受当地叙利亚人的指责和排斥,参加美国人的大party也已成为当地年轻人津津乐道的活动。政治分歧并不能否定一个国家,更不能否定一个民族。叙利亚人是与世无争的,他们的生活可以永远是简单的食物、朴素的衣着和自由的作息时间。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完成你的宗教仪式,也可以用一天来徜徉在地中海边,享受不逊于迈阿密的海滨美景,你更可以漫步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与迎面走来的老友自由地交谈,哪怕整个对话只有一些寒暄客套之词,也会让叙利亚人感到幸福与快乐。这就是叙利亚人,有着游牧民族的倔强和勇敢,但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对和平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