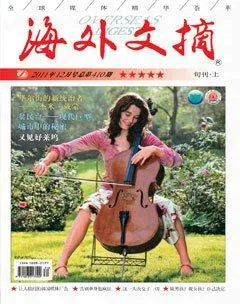贫民窟
2011-12-29保罗.马森郭静超
海外文摘 2011年12期
世界上,有10亿人以贫民窟为家。尽管社会上层的富人想要清理掉这些有碍观瞻的贫民区,但是,居住在其中的人却表现出异常坚定的信念——绝不离开。
走进21世纪最典型的贫民窟
一条蜿蜒绵长的河流,河水污浊,岸边漂着各种颜色的塑料垃圾袋;河岸两旁,林立着参差不齐的简陋窝棚,一眼望去,垃圾、破罐、碎木块、洗衣污水、零散布料、老鼠和一群孩子便一股脑地冲进你的视野中。这里就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的贫民区——圣米格尔的埃斯特罗地区——马尼拉富人与穷人间不宣而战的前沿阵地。人们从摇摇欲坠、咯吱乱响的门后出来,行走在狭窄的过道上,远处,清真寺的圆顶清晰可见,它的那边,就是大城市的摩天大楼。
一个社区负责人梅纳自愿当我的导游,但也只不过是50来米的距离,因为她说,再深入下去,就无法保证我的安全。我们走到一个梯子底部,埃斯特罗贫民区的神秘面纱就此揭开:一个长长的隧道,一米多宽,黑暗中偶尔几个裸露的灯泡散发出微弱的灯光,宛如一个老式的煤窑,快要散架的托梁,几道昏暗的光线,地上几滩不明液体(我希望是水)。就是这样的隧道,通向着6000多人的家门。
我们敲了敲第一扇半掩着的家门,主人奥立弗匆忙穿上衣服惊异地走出来,他身后的4个孩子正吃着冰淇淋。两米半见方的屋子是这一家六口全部的居住空间,包含所有家当:一台电视、一个灯泡、一个床垫以及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他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10多年,当被问及为何来这里时,奥利弗说:“因为贫穷,只有来这儿才更容易找到工作,我现在每天挣400比索(约60元人民币),可以让孩子去上学,满足他们的每日三餐。”志愿导游梅纳插话说:“他们很幸福。”
在这里,要想避免与别人摩肩擦踵,几乎要踮着脚尖前行;在这里,要想上厕所,就不可避免地排队等待;在这里,夫妻的亲热地点与孩子只有咫尺的距离,还要冒着20个其他家庭听到的风险——这里就是21世纪贫民窟的典型代表。全球1/7的人口——10亿人——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到2050年,该数字可能达到30亿。贫民区是现代巨型城市的肮脏秘密,是20年来毫无束缚的市场作用以及人类无限贪婪、冷漠的隐秘恶果。
拆,还是不拆?
因为这个地方一直备受谴责,所以梅纳不断在我耳边重复着她的口头禅:“我们是幸福的,这里有社会凝聚力,我们组织性强,这里也干净。”菲律宾总统已经决定清理马尼拉的贫民区,把50万人赶回农村去。这一决定迎合了大商人和政客们的需求,因为如果要在马尼拉重新安置这些人,所建住宅的费用将高达国家预算的1/3。
如果要迁移,埃斯特罗的贫民区居民则首当其冲。但居民们却态度坚决:要想让我们走,先打败我们!梅纳说:“我们会设置路障,实在不行就奋起反抗,我们会抵制清除这里,以斗争来捍卫社区,我们在这里很幸福。”就在不久前,另一个贫民窟的居民就展开了一场捍卫家园的战斗,造成6名警察及大量居民受伤。更不幸的是,他们的家园被焚毁殆尽。
严格按法律来讲,这些民众应受到支持。2003年,联合国在其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报告《贫民窟的挑战》中,显示了对旧有贫民窟清除政策的转变和排斥,并承认这些非正规住宅区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正面影响。贫民窟接纳了新增的城市移民,因为人口稠密,所以用地更加有效,其中包含了多元文化,也给衣衫褴褛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多机会。
联合国人居署的穆罕默德·哈迪姆说:“10年前,我们梦想着有朝一日城市没有贫民窟,但是现在,处理的方法发生了改变,人们看到了积极的因素,所以不是清除它们,而是不断改善和规范土地所有权。”
经营非营利组织以帮助建造人性化建筑的卡梅伦·辛克莱形容道:“贫民窟就像是适应力强的城市动物,像有益的寄生虫,有些寄生虫攻击人体所以需要清除,但是这些非正规住宅却是与城市和谐共处的寄生虫,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就可以。”
辛克莱的组织还帮助改善了在巴西、肯尼亚和南非的贫民窟设施,他认为现代城市的设计不仅要容忍贫民窟的存在,还要从中学习甚至效仿它们。“老实说,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其缺点恰恰是低收入阶层无法在市中心居住的窘境,不得不通勤两个半小时去工作,使得他们总是在路上。”
颠覆陈腐印象
菲律宾建筑师帕拉佛克斯拥有一份拯救贫民窟的热忱,他想重建圣米格尔埃斯特罗区,在原地用新材料逐步清理、逐步安置——每个区域有10平方米的面积,底层用于日常用品零售或者存放三轮车,楼上则将空间延展到地面过道之上,就像贫民窟居民自己建造的房子一样。帕拉佛克斯说:“贫民窟的居民是居住和工作空间设计方面的专家,他们很擅长将仅有的空间混搭运用,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学习。”
可是,对政府来说,这却是一个太过烧钱的设计,全部重建的费用相当于菲律宾GDP的30%。但据推测,这个数额也相当于每年因贪污而损失的国家财富数量。他将这里看作一个实验田,如果可行,就将推广到每个滨河贫民窟,所以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与马尼拉穷人共事的诺韦尔托认为,精英阶层正以自我欺骗的方式来对待贫民窟清除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贫民窟居民对于城市的作用:有了他们,有人为你开车,有人打扫房间,有人帮你看店,如果他们都从城市中被赶走,城市就会死亡。”
知识和梦想
正值星期六的晚上,一个全副武装的结实的家伙,手持棍棒、链枷和手电筒四处巡视。原来,他是圣米格尔埃斯特罗的志愿警察。于是,我们调头走向小巷对面,到了一座不足一米宽的小桥,上面有个男子蹲在烧烤炉旁,烤炉冒出的烟笼罩着桥,走上去才知道是在桥上,桥下是一条水渠,约两米宽。河边的住宅如此紧密,从楼上的卧室窗户伸出手来就可以和邻居握手了。
随后,我们低头弯腰进入隧道,因为高度实在不容许人直起身来,过了一个扑克游戏摊,遇到一只流浪鸡,然后走进一个杂货店。22岁的女孩艾格尼丝经营着这个店铺,出售着和其他贫民窟商店一模一样的商品:袋装洗发用品、海飞丝洗发水、菲律宾版的万宝路香烟、打火机、卫生巾以及口香糖。这是她父母帮助成立的商店,收入用来交学费。我问她:“你学什么专业?”“企业管理,我有一个学位,我还在一个大公司上白班,在市场部做资料输入。”“你在这里生活?”“是的,我在这里出生的。”
后来,我们见到了志愿导游梅纳的儿子,他正在发奋学习。走过桥,一阵熟练敲击键盘的声音传过来,原来那是一家网吧,胶合板搭成的小屋里挤着9台电脑。有人在上脸谱网站,有人玩在线扑克,一个女孩正在编写简历,另一个女孩正沉醉于劲舞游戏,并在游戏和自己的黑莓手机间来回变换任务。她也是一个大学生,学习企业管理。
在这100来米的距离中,我遇到了3位大学毕业生、一个志愿警察,当我渐渐习惯这里的烟雾、儿童的哭闹和欢笑、鸡群和有限得可怜的空间时,我了解了贫民区,这里并非很糟。梅纳告诉我:“其他地方有卖淫,而这里没有,我们喝点酒,偶尔吸毒,但都在可控范围内。我们大家互相照料,能看清任何发生的事,这是一个大家庭。志愿警察主要的工作就是警惕纵火犯,因为受到清除威胁的贫民区很容易被放火。”当我问梅纳为何如此有政治修养的时候,她回答,在马尼拉大学主修政治学专业。
贫民窟居民,不仅是这里的,还包括开罗、内罗毕、利马和拉巴斯的贫民窟居民,创造出的是那些想要清理贫民窟的独裁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有秩序的紧密联结的贫民窟,或者说是联合国所称的“希望的贫民窟”。
在全球层面上,人们的争论已经不是要多久拆除这些地方,而是我们能否满足那些在铁皮棚房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迅速增长的志向与抱负。经营非营利组织的辛克莱说:“那些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就可以根除贫民窟的想法实在是痴心妄想,因为你无法打败那些比你拥有更强发展模式的人。如果在这些非正规居住区强行为之,他们很可能会终结城市。当城市只剩中央商务区的那一天,游戏就结束了。”
[译自英国《新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