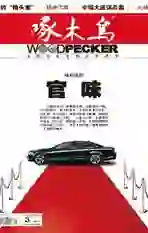茶马古驿那柯里
2011-12-29曾纪鑫
啄木鸟 2011年3期
那柯里位于云南省宁洱县同心乡。傣语“那柯里”,意指桥边肥沃的土地。从普洱市出发,沿昆曼公路(昆明—曼谷)北行约二十五公里,便是那柯里村。村头真的有桥,桥下山涧,流水潺潺。一棵造型逼真的“魁梧”榕树,伸出硕壮的树枝,一根粗粗铁链向上挂着树枝,向下连着一块造型别致、上书“连心桥”的石碑。树干居左,石碑立右,树枝横逸当空,三者构成一座长方形的“口”形大门。穿“门”而入,便是茶马古驿那柯里。
那柯里既为茶马古道上的一处驿站,自然与茶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这茶不是绿茶,也不是乌龙茶,而是风行一时的普洱茶。
作为世界三大主要饮料之一的茶叶,主要分为不发酵的绿茶,半发酵的乌龙茶,全发酵的红茶。其中绿茶又有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庐山云雾、信阳毛尖,乌龙茶有铁观音、黄金桂、武夷岩茶、白芽奇兰,红茶有闽红、祁红、滇红、粤红等之分。
普洱茶属全发酵茶,严格说来,也可纳入红茶系列,但它与普通红茶在制作工艺方面又有所不同,是一种后发酵茶——自然陈化发酵或人工渥堆发酵。因此,也有专家将普洱茶单独归为一类,与绿茶、乌龙茶、红茶并列。
茶是我的至爱,每日所饮多为绿茶。2003年从武汉调到厦门,自然也喝起当地的乌龙茶来,几个有名的品种都曾品过。这种称为“功夫茶”的半发酵茶饮,其茶具的精致、冲泡的复杂、品饮的讲究,虽颇费功夫,倒也有一股悠悠的茶韵直入心脾。而对红茶,则喝得极少,于普洱茶更是不甚了了。
大学同学袁升平毕业后经过一番辗转,最后回到了他的出生之地——云南思茅,也就是2007年改名的普洱市。一座城市因茶而更名,可见普洱茶的积淀之深、魅力之强与影响之巨。因为同学所置身的城市之故,对普洱茶就有了一份难得的亲切,虽有赶时髦之嫌,却也像模像样地品过几回。这种发酵后的熟茶,茶色红艳透亮,入口温和甘滑,饮后有一股醇厚绵长的舒坦,令人回味不已。
等到有机会来到普洱市,喜欢刨根究底的我,免不了要对普洱茶相关的一些物事,来一番“巡礼”,而茶马古道,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节:普洱茶之所以成为今日如此特性的茶饮,实与茶马古道密不可分。
“普洱茶”之名,早在1664年的《物理小识》一书中就已出现,但那时的普洱茶仅具地理意义,强调的只是原料所属地。“夏喝龙井,冬喝普洱。”当这种产于普洱的茶叶受到满清皇室推崇,成为中华名茶之后,需求量顿时大增。于是,普洱茶便通过漫长的茶马古道,送达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广大消费者手中。
云南多山,天远地偏,与外界的经贸交易、沟通联系主要依靠茶马古道。自唐朝就已兴起的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线路主要有三条——青藏线(也称唐蕃古道)、滇藏线与川藏线。茶马古道的运输范围主要包括云南、西藏、四川三大区域,可通往西安、北京、拉萨、广州、香港等地,向外延伸则可抵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等国。据有关资料统计,云南境内的茶马古道长达两千多公里,几乎贯穿省内所有地区。想想看,仅靠人背马驮,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径,不仅负重难行,充满艰辛坎坷,更得耗时费日。因此,云南境内的茶马古道,单程一般要走三四个月;而出了云南,还得继续颠簸前行;等到茶叶送交消费者手中之时,大半年时光已悄然逝去。
在茶马古道的运行途中,茶叶不得不经受气候、季节、环境的影响,太阳的曝晒、阴天的潮湿、雨水的浇淋自不可免,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乃至山地、高原、河谷等不同地形的变化,也不知不觉地影响着运行中的茶叶,改变着它们的品质。一个最奇妙的变化,就是发酵,由原来的生茶,经过自然发酵,变成了汤色红浓、陈香弥漫的熟茶——也就是广大消费者认可、流行的普洱茶。与绿茶不同的是,普洱茶越陈越好,经由时间的积淀,打磨出内在的力度、质量与品位,普洱茶方显其“英雄本色”。
当自然发酵的普洱茶供不应求,当交通工具改变、运行时间缩短、自然发酵无法完成之时,聪明的茶商自然会利用人工技术,加速其发酵过程。于是,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干仓陈化法、湿仓陈化法等传统制作工艺。尽管如此,普洱茶仍满足不了需求量日增的广大市场。直到1975年,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女士发明了现代人工渥堆技术,将发酵时间由传统工艺的十几年、几年缩短到四十五天左右,普洱茶由此进入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时期,长期存在的供需矛盾才得以解决。
在自然与加工、传统与现代、生茶与熟茶之间,茶马古道扮演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它是容器,是酵母,是普洱茶的一道关键“工序”。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马古道的“升华”,就不可能有普洱茶的声名远播,更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普洱熟茶。
为一睹茶马古道的风姿,我的目光,聚焦在了那柯里——
北上京城,南下缅甸、老挝,那柯里乃马帮必经之地。驿站于道光十年(公元1831年)由当地一位赵姓农民开设,一栋两层楼的庭院,便是当年的荣发马店,二楼一块匾额,书有“茶马古驿”四字。
“关山难越谁为主,萍水相逢我作东。”挂于荣发马店入口处的木刻对联如是写道。南来北往、络绎不绝的马帮经过一番艰难跋涉,来到这一专供休息调整的中转站,大有宾至如归之感。暮色苍茫中,马铃叮当、脚步杂沓、人声喧嚷,荣发马店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客人。伙计乃至店主顿时忙碌开来,给马喂水添加饲料,为客人准备可口饭菜,安顿他们休息。
行走在茶马古道的马帮,运送的茶叶、盐巴、毛皮、药材、布匹、器皿等货物相当贵重,有的甚至运送大量金银钱钞。巨额财富必然引起不法之徒的垂涎,因此,茶马古道不仅荆棘丛生、道路崎岖,还会有无数人为的险阻,盗贼横生,劫匪出没,无时无刻不威胁着马帮的安全,他们不得不武装自卫,时时警戒。据那柯里石碑记载,清光绪时期,这里便设兵六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有士兵把守,于是,马帮到了荣发马店,就可以好好放松放松,尝尝这儿的佳肴,喝喝驿站酒坊酿制的美酒,安心落意地睡上一觉了。
当然,这儿毕竟只是一处驿站,第二天不等天亮,他们就得起床,一番收拾,又得迈开脚步,匆匆启程,跨高山越激流,一步一步丈量漫漫古道,将货物送达目的地。正如立于马店庭园一块巨大的卵石上所写:“地为琵琶道作弦,听马蹄狂弹奏调;天是棋盘星当子,看仙指轻移出着。”
一批批马帮来了又走了,斗转星移,就在这样的迎来送往中,一百多年时光一晃而过。直到1954年,一条公路从那柯里经过,拖拉机、卡车、轿车逐渐取代传统运输工具,荣发马店也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它的终点。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重视,已然衰落的荣发马店,又焕发出新的魅力,凸显出另一种新的风采。“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这一意象蕴含着古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密码,而“古道西风”中的一处处驿站,则给骑着“瘦马”的“断肠人”以无限温情、动力与支撑。颇有意思的是,荣发马店接待的客人中,除了不同民族的国人,还有漂洋过海而来的西人。据说曾有一位美国女子,拿着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前来马店,寻找她祖父的足迹。原来,她祖父在荣发马店住过,照片所拍,便是当年情景。她在祖父遗物中发现这张珍贵照片后,便一路追寻着找到了这里。
从唐朝开始,普洱府(宁洱县)就因出产普洱茶与磨黑盐而成为商贾云集、马帮络绎的一处重镇。作为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出产地及中转集散地,如今,宁洱县的茶马古道只剩三处,而驿站犹存者,荣发马店恐怕算得上“仅此一家”了。
当年的荣发马店较大,可容纳一百匹马左右。如今的庭院,显然经过修葺,一楼房间摆放三排马帮使用的麻袋,麻袋装得鼓鼓囊囊的,里面也许是盐巴、布匹、毛皮、药材,但更多的该是制成茶饼、茶砖的普洱茶了。而整个驿站肯定经过一番刻意规划,且投资不菲。经过一番了解,事实果真如此,当地政府不仅修复了马店,还建造了寨门、洗马台、马跳石等十多个景观,并重新铺设、维修了近五公里的茶马古道,将那柯里打造成了一处别具风味的旅游景点。
傣语“那柯里”名不虚传,土地肥沃,靠近桥边。古驿站不大的地盘上,就架有三座桥梁——以铁索勾连、钢筋水泥作支撑的“连心桥”,有名为“风雨桥”的古老廊桥,还有一座以当地楠竹为材料的竹桥。走在三座不同的桥上,看山涧激越的水流,在拂面的清风中,仿佛吹来了一阵马蹄的杂沓、马铃的叮当与浓郁的茶香,在山谷间回荡不已。
据说那柯里原名“马哭里”。这里原本无桥,马帮越过山涧,马匹只有涉水而过。面对或清澈或浑浊的冰凉河水,马儿会情不自禁地落下伤心的泪水。经过一番周折,后来才修了一座二十多米长的廊桥。有了这座今天依然耸立着的“风雨桥”,马儿再也不必下涧涉水“哭鼻子”了,于是,谐音“那柯里”应运而生,一直留传至今。
过了山涧,马店对面是新近打造的相关景点,有马帮冲洗骡马的洗马台,有一座碾房,房内安有古磨,还有一座大水碾,一条跨越山涧的渡槽通达碾房底部,水流冲击,石碾转动,将供应马帮食用的稻谷、高粱、玉米等粮食作物脱粒碾碎。
碾房内,四周有供游客休憩的木制条椅,中间摆放桌子,桌上有煮熟的玉米、红薯,香气勾人,欲掏钱购买,一农家妇女说:“吃吧,都是自家地里种的,不收钱。”闻听此言,实在难以相信,这里的村民还保持着如此纯朴的好客古风!向南望去,但见几十家农户,一律的红砖青瓦房,顺山势错落有致地铺排开来。斥巨资打造后的那柯里不收门票,为的只是开发、保护古迹,不由得使我比对刚刚游览过的西双版纳,那里不仅被开发得没有半点古朴与神秘,且每到一处,门票昂贵堪称全国之最。追名逐利,已将不少风光迷人、文化深厚的景点改造得面目全非。
马蹄声早已远逝,而古风还在那柯里劲吹,传递着当年的侠义与豪放。那悠远绵长的古道,而今安在?于是,赶紧转到荣发马店背后的山坡,一条经过修复,近两米宽的茶马古道赫然映入眼帘。我们开始一级一级地攀爬,两旁是绿树翠竹,石头或石板铺就的路上,落满枯叶。鸟儿的啼鸣更加衬托出古道的幽静与神秘,马儿的喷鼻、笃笃的碎步,特别是那不时响起的马铃声,着实令人怀想不已。爬上山头,古道拐一个弯,继续远去。遗憾的是,那柯里古道所剩约十公里,昔日蜿蜒崎岖,四通八达的悠远古道,只能借助想象在心中凸现、复原了。
茶马古道的主人自然是马帮,他们日夜出没其间,不停地行走,一代又一代,连结起一条不同民族长期交往、中外文明相互交融的纽带。茶马古道以及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无数马帮,共同打造了一个声名远播的民族品牌——普洱茶。如今,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小路、驿站、古镇、茶庄、古桥、石碑等,在历史与时代的淘洗中,或衰落失色,或销声匿迹。可是,我们却能在每一壶飘着馨香的普洱茶汤中,在厚重的茶叶编年史及茶文化交流史中,找到它们依稀闪烁的影子。美国医学专家约瑟夫教授在对茶叶作过多方试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