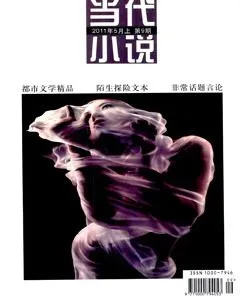谢幕
2011-12-29张国平
当代小说 2011年5期
那天夜里王三炮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草班子里的戏生,不知给谁家办丧事,搭了台子唱戏,也记不清唱的哪出戏,只记得唱词很悲切。王三炮正投入地唱,后台突然钻出一个人,对台下喊,都回吧,都回吧,散场了。
正唱得好好的,怎么说散场就散场呢,王三炮心有不甘,对那人发脾气。这么一急王三炮便醒了,望着黑咕隆咚的房顶寻思了半天,不知那梦是好是歹,寓意着什么。
不知是否跟那场梦有无关系,2000年对王三炮来说是最晦气的一年。王三炮的脚步刚刚跨进世纪之初,倒霉事便接踵而至。
马上要春节了,王三炮准备置办年货,去了百里之外的小城,带着老婆葛芝兰。王三炮是老井村数得上的有钱人,年货的事当然马虎不得,东西好赖不说,起码得有个风光的来路。其实老井村离县城只一步之遥,县城的北环离王三炮的家也不过五十米,开上王三炮刚买来的轿车,到县城最热闹的集市撑死不过十分钟。可是,王三炮置办年货却要到小城。小城是区府,城市大,东西全,样式新,最关键的是名声好,一样的东西说起来也高一个档次,就像一件花衬衣,穿在不同的女人身上,感觉是绝对不一样的。
当然,去了小城是要住一宿的,小城那么大,不好好逛一逛怎么成,所以,当天去当天回是件很没面子的事。王三炮的连襟生病住院了,儿子和儿媳恰巧不在家,看家的事便落在老爹王木头身上。
王木头七十多岁,没啥文化,粗人一个,电视里蹦蹦跳跳的节目没啥看,王木头吃了饭便早早地睡觉了,睡在王三炮宽大的席梦思上。王三炮走的时候吩咐了,让他住偏房的西屋里。儿子有钱了在老子面前说话气也粗,对他的话王木头几乎是言听计从的,但是这次却违反了。儿子的房间里有空调,外面寒风刺骨,屋里却温暖如春。偏房的西屋冷,冷得如冰窟窿,这把岁数了这么打发我,当我不是你爹?当我是条狗?
反正家里没人,才不受那份罪呢,于是王木头睡在了儿子宽大的床上。软软的床垫,暖暖的被褥,王木头很快便进入了梦乡。梦里遇上去世两年的老伴,老两口多日不见,见了面难分难舍,情意绵绵,好好地亲密了一把。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王木头突然听到大铁门被砸得啪啪响,一激灵翻身下床,惊出一身冷汗。坏事!儿子突然回来了?自己脏兮兮的身子睡在儿子床上,被他发现了还不是一顿没头没脸的数落?王木头连忙穿衣服,睡眼蒙眬地朝外走。
不对。外面黑咕隆咚,冷得刺骨,王木头闷着头朝外走,突然觉得不对了。儿子是有钥匙的,怎么会没命地砸门子。是自己心虚,怕是做梦吧?王木头侧耳细听,铁街门的确啪啪作响,还伴随着女人尖细的喊声:三炮,开门,开门!
谁呀?三更半夜的。王木头隔着门缝对外问。
在,他在。不是一个女人,几个女人的声音在嘁喳,然后一个女人尖叫着喊,三炮,给钱,我们马上回家过年,给钱!
谁差你钱?三炮差你钱?王木头问。
别装蒜了,我们知道这是你家,开门,给钱!女人在外面七嘴八舌。
差钱找三炮要去,我是他爹。王木头说。
你是他爹?我还是他娘呢。外面嘻嘻哈哈一阵笑声,说,我们是两口子了?开门吧,咱们热乎热乎。
谁家的不要脸的?谁家的卖×娘们,滚!王木头吼。
三炮才不要脸,搞了我们一年一分钱也不给,他才不要脸。
是呀,我们卖×,可卖×也得卖几个钱不?三炮把我们都搞了,过年了躲起来,休想!就算他藏进他娘×眼儿里也得给钱。
王木头明白了,是一帮小姐。三炮在外面的事,王木头是知道一些的,村里人都在议论,说三炮在枣乡度假村怎么搞怎么搞,这事王木头也曾跟他说过,说你也是当老公公的人了,咋就那么不注意影响呢?可是,王三炮只嘿嘿一笑,置若罔闻。
滚!都给我滚!
夜半三更,小姐们的喊声邻居一定听得一清二楚,丢人啊,王木头急得脖子上的青筋蹦起老高,对外面吼。
哟哟哟,好大脾气呢,别急别急,气大伤肝,替三炮给钱吧,给了钱我们马上滚。外面嘻嘻地笑着,拿捏着腔调说。
没钱,快滚!王木头说。
没钱?我们让他白搞?到底给不给?不给我们可喊了。便有小姐扯直了嗓门喊,三炮不要脸,搞了小姐不给钱!
我日你奶奶!王木头摸起一块砖头,哗啦一声开了门。
呼啦一下,七八个小姐跑开了。到底是上了岁数的人,又黑咕隆咚,一脚深一脚浅,王木头追了几步便气喘吁吁。
见拉开一段距离了,小姐们又站在远处喊,三炮不要脸,搞了小姐不给钱!
这还了得?你让俺这张老脸朝哪搁,王木头像头发疯的老牛,举着砖头朝远处追,直追得小姐们无影无踪了。
丢人啊。王木头气呼呼地锁了门,觉也不睡了,吧嗒吧嗒地抽闷烟。
可是一根烟没抽完,外面又传来砸门声和小姐们的喊声,三炮不要脸,搞了小姐不给钱。
王木头开门,拎着砖追,小姐们跑。王木头回屋,小姐们又来。那一夜反反复复多次,王木头折腾得老骨头快散架了。
全村人都知道了,害怕啥丢人不丢人的,等王三炮回来,王木头当着儿媳葛芝兰的面,对王三炮一顿破口大骂。
这是王三炮发财以后王木头对他第一次发这么大脾气,若是往常,王三炮不翻脸才怪。可是这一次王三炮却低头不语。
快过年了,你看看你整的啥事。王木头以老子的口气说,把钱给那帮不要脸的,破财免灾。
王三炮倒很乖,开车去了枣乡度假村,一人两千元,分发给小姐们。王三炮也冤,吃吃喝喝买金买银没少破费,现在居然还要钱。
其他小姐都很顺利,乖乖地接了钱,回家过年了,只有一个叫小鸽的小姐不肯接。小鸽说,我没给你要钱,那天夜里我没去。你也别想拿钱打发我。
小鸽乖,这个我信。王三炮嘻嘻地赔着笑脸说,不过快过年了,有她们的也得有你的,拿上回家吧。
咱可说清楚了,这钱是让我回家过年的,跟你的承诺无关。小鸽说,说清楚了我再拿钱,一码事不顶一码事。
承诺?我承诺啥了?王三炮问。
小鸽说,你说过,而且不止一次说过,跟我结婚的。
啥?我啥时给你说过结婚的?王三炮问。
小鸽说,你忘了?你在我身上的时候都这么说的。
屁话。那时候说话也算数?王三炮说。
说话不算数算放屁?小鸽说,放屁也不行,放屁也得算数。
你要不要?不要拉倒,一分钱也不给了。王三炮耍起了横,将钱甩在小鸽脸上。
对散落在地上的钱,小鸽眼皮也没抬一下,说,不行,这点钱别想打发我。
没想到平时对他百依百顺的小鸽居然这么硬,王三炮软了,问,你究竟想怎么样?
小鸽说,跟我结婚,你说话得算数。
我的姑奶奶,算我放屁行不行?王三炮说。
不行,你每次在我身上都这么说。你还说跟那个老婆娘散伙,跟我结婚。小鸽说,王三炮你不是不知道,我的第一次是给你的,而且我只跟你一个人好,我只当领班,没跟其他男人乱搞过。不信你去问问,看我是不是这样。
这点王三炮是知道的。小鸽原本不是小姐,原来是个打工妹,在一家超市上班,后来被王三炮搞了,也说了跟她结婚之类的话。因为跟王三炮搞,小鸽被超市开除了,王三炮没办法只得在枣乡度假村租了间房子,长期跟她好。严格地说应该算情人关系吧。可是王三炮怎么能保证,小鸽就没跟其他人好过,一件衣裳扔在污水里就能保证不染污点?
不过现在的王三炮没工夫跟她纠缠这个了,王三炮只想打发她回家,自己也好安安生生地过个年,闹得风风雨雨,在儿子儿媳面前,这个爹的老脸朝哪放。
好小鸽,我知道你最心疼我,这个婚呢暂时还离不了,咱还得从长计议。王三炮苦着脸问,按最坏结果算,假如我离不成婚,你想我拿多少了结?
你得兑现你的话,不兑现不行。小鸽说,我不要你一分钱,等的就是那一天。
我的姑奶奶,我是说假如,假如呢?王三炮问。
小鸽伸出一把手。
五万啊?王三炮的头嗡的一下。
小鸽不紧不慢地说,五十万。
啊?你他妈的想杀人啊?五十万还不如杀了我。王三炮嗓门都直了。
小鸽说,其实我并不在乎你的五十万,还是想你兑现你的诺言。要么你跟我结婚,要么给我五十万,要么你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
要过年了我的姑奶奶,别说这么晦气的话好不好?
你说怎么办吧。小鸽问。
王三炮将地上散落的钱捡起来,又连忙摸口袋,又摸出一沓钱,加在一起说,这五千元你拿着,先回家过年,等回来了咱再商量。
小鸽说,不行,你得写个欠条,不写下你的承诺,等我回来你再说你放屁怎么办。
王三炮好哄歹哄小鸽不松口,只好写下了欠条:欠小鸽五十万,以后慢慢还。
事态严重。王三炮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思索,今后怎么办?连杀了小鸽的念头都有了。王三炮想,等机会得将自己的欠条想办法撕了,那东西握在小鸽手里早晚是个祸害。
这年的春节,王三炮过得索然无味,被小姐们堵着门子要钱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了,全家人都没好脸色,刚过门的儿媳妇见了他更躲得远远的,王三炮自己也不想在家待,钻进满子的小商店耍钱。
满子的小商店一共三间,一间摆放着各类商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烟呀酒呀的不用出门买了;一间开着小吃部,平时供应外村打工者饭菜,几道小菜炒得味道鲜美,男人们干完活了可以在这里解解馋。老井村人几乎家家都参与了捣腾吊车,邻村的亲戚朋友也参与之中,有的入股,有的帮忙,所以村里很多外来人口。买来一辆破旧的废车,几经捣腾,修修补补打扮得新娘一般,再卖出去价格翻上几倍,等于白捡的钱,谁不眼红。满子最里面的一间设了赌场,乌烟瘴气的屋里常聚着男人耍钱。
王三炮的手气不顺,大年到小年短短十五天,输了近二十万。
王三炮便在心里骂娘,骂那帮小姐,骂小鸽,都说女人是祸水,这话不假。
钱是龟孙,输了再拼。王三炮这样安慰着自己,这个晦气的春节也就过去了。过了小年又该捣腾吊车了,节前刚买了辆旧吊车,整修得差不多了,喷上新漆,差不多就能卖了。王三炮粗略算了一下,按当下的价格,一共能赚三十万,这样春节输的钱就弥补了。不过他始终在思考小鸽的话,那五十万怎么办?五十万王三炮是拿得出来的,可那都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白白给了她不成?
刚刚联络好买主,突然一股风传来,说上边要来查了,抓紧躲一躲吧。
一辆破旧的吊车,修修补补,喷上名牌厂家的牌子当新的卖,毕竟是件违法的事。尽管上边的环节都拿钱疏通好了,但上级上面还有上级,上面精神来了,还是要做做样子的。有不长眼被查住了,还真得公事公办,没收吊车不说,还要罚款,甚至拘留。这些年媒体厉害,不把事做得跟真的一样不行。
于是王三炮连夜将吊车开到了外村亲戚家,结果买主也躲掉了,耽误了时机。
捣腾吊车违法,买吊车的也违法,这事谁都不敢朝枪口上撞。
买吊车的人走了,小鸽倒来了。小鸽径直走进了王三炮的家,掏出王三炮写的欠条,死皮赖脸不走了。王三炮的家一下成了马蜂窝。
葛芝兰哭成了泪人,儿媳赌气回了娘家,儿子小川怒火三丈,啪啪给了小鸽几耳光。王三炮趁机撕了欠条,一把揪住小鸽的衣领,老鹰抓小鸡地将她提起老高,吼,滚!
小鸽不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还是那句话,要么结婚,要么给我五十万,要么你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小鸽说,反正我跟你好几年了,不能轻易了结了。
王三炮家的吵闹引来了围观者,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老井村的男人这些年不守规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玩小姐,耍钱赌博的人多了去了。在老井村女人的潜意识里,男人有钱了添的这些毛病已不算啥,只要顾面子,女人是能接受的。像老井村第一富户王五群,小老婆都有孩子了,人家在县城给她买了房子,从不带回老家,家里的老婆,外面的小老婆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家里的老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没那回事。可是谁也没有王三炮这事办得窝囊,你王三炮搞小姐给钱不就完事了?干嘛让人家找上门呢。
男人们是知道原因的。平时王三炮总是讽刺其他人,说你们那算啥能耐,搞小姐还要花钱,看看咱,搞了也是白搞,你情我愿,舒坦。所以男人们围上来,多半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虱子已爬上了秃子的头,王三炮顾不得那些了,脸色黑紫地对小鸽大打出手。王三炮没想到,柔柔弱弱的小鸽骨子眼里居然非常硬,遍体鳞伤居然没喊一声,只一个姿态,打死我可以,不答应条件不行。
到最后小鸽想走也走不成了,小鸽被打得动弹不得。
擦黑的时候小鸽是被王三炮拖到机井房里的。小鸽被拖着,嘴里仍不停地喊,王三炮不要脸,我跟他好了好几年,答应跟我结婚,说话不算数,说话等于放屁。
那间机井房离村二百米,早就废弃了,四处透风,小鸽动弹不得,不冻死才怪。到底是女人心肠软,不知是谁家女人不忍心,送去了一件破棉被。
破财免灾,你王三炮平时风光了,这时候也该出点血了。男人们议论着这事,纷纷散了。
女人们不肯走,劝葛芝兰,事已经出来了,再哭能有啥用,让王三炮把她送到医院吧,打成那样出了事都不好说。完了给点钱算了吧。
可是葛芝兰哭得昏了头,哪还知道怎么办,一群女人见葛芝兰不吐口,知道劝也没啥用,不再说了。
还真如女人说的,小鸽真的出事了,夜里死了。
家里闹得乱哄哄,那天王三炮没脸在村里待,独自开车去城里喝酒了,喝得一摊烂泥,睡在宾馆里。
直到第二天中午王三炮的酒劲还没退,房门被服务员打开,进来几个警察,王三炮被带走了。那个时候王三炮还不知道事情真相,等到警察讯问一点点深入,王三炮才知道小鸽死了,被人掐了脖子杀死的。
尽管最后证明不是王三炮干的,但他在老井村再也抬不起头来,平日里威风一扫而光,走路耷拉着头,蔫得一点脾气也没了。
小鸽是傻岭子杀的。傻岭子想小鸽的好事,夜里摸进去,不想一个做小姐的竟然不干,跟傻岭子厮打,傻岭子见好事做不成,恼羞成怒掐死了小鸽。
从拘留所出来,王三炮几乎夜夜噩梦,梦见小鸽对他提条件。仔细回想起来,王三炮内心是有愧的,这么俏丽的一个人,因为自己死了。王三炮便想起小鸽的种种好,想起跟自己缠绵时的情景,柔声细语的,情意绵绵的,现在居然死了。
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还不如给了她五十万,仔细算下来小鸽跟自己已经六年了,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该嫁人了。兴许拿了五十万嫁个不错的男人,小鸽会过得不错。所以王三炮常常夜里惊醒,醒后一身冷汗。
日子还得过,王三炮又将力气用到吊车上,想用拼命干活消减自己内心的愧疚。
可是不久王三炮又被一个消息惊得魂不附体。上海人阿来打来电话,说吊车砸死人了,是王三炮刚刚卖出不久的吊车,那边起诉生产厂家,结果查出吊车是冒牌货。阿来说,我完了,万一顺藤摸瓜查出来,咱俩都得蹲大牢。
阿来说,我得跑了,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躲上一年半载。可是我手头钱紧啊。
阿来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是该破财免灾了,王三炮再不敢怠慢,给阿来卡上打去了十万块。
这可不是小事,王三炮吩咐阿来躲得严实一点,千万别露面啊。
王三炮销往外地的吊车都是通过上海人阿来销售出去的,王三炮跟阿来合伙了十来年,双方已形成了默契,阿来对吊车的来源一向守口如瓶,万一阿来供出来,那不只是一辆吊车的问题,一查就是一串儿,家产没收不说,够蹲几年大牢的。
阿来很长时间再没联系,王三炮悬着的心渐渐平静了。阿来的为人王三炮是了解的,不来电话,肯定是没啥问题。躲了这一段,等风平浪静了阿来还会来找他,还会替他销售吊车,两个人是一个线上的蚂蚱,好处分享,利益双赢。
枝头泛出了新绿,春天也就到了,这段时间被一串儿倒霉事弄得焦头烂额,王三炮在这个春天里终于缓了一口气,是该好好捣腾吊车的时候了。
王三炮买了三辆旧吊车,停放在胡同口外的谷场上。三辆旧吊车三十万出头,过两个月捣腾新了,价格少说也值六七十万,如果恰巧碰上雏手,卖八九十万也不好说。听说上边风声越来越紧,得抓紧时间,万一吊车捣腾不成了,赚了钱再干其他的也好办。
王三炮准备大干一场,王三炮想让全村人好好看看,我王三炮不只是会丢人现眼,还很能赚钱。王三炮的心一回到吊车上,底气马上足了。
吊车是王三炮的灵魂,心思全扑在吊车上,王三炮把前面的事一点点忘却了,包括死去的小鸽。
捣腾吊车不但是个技术活,还特费力气,一会儿爬上面,一会儿钻车底,一天下来累得散架似的。
那天夜里王三炮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震耳的爆炸声惊醒,隔着窗户朝外看,漆黑的夜里红光刺眼。
大喊不好,王三炮胡乱地扯了一把衣裳,疯跑出门。谷场上三辆旧吊车已淹没在大火之中,轮胎因大火而膨胀,发出震耳的爆炸声。
三十万啊!王三炮蹲在地上抱头大哭。
三十万就这样成了一堆废铁。车上明显是被浇了汽油的,不然大火不会那么旺。谁干的?难道是小鸽冥冥之中的鬼魂?
对小鸽的内疚刚刚被排挤出去,因了一场大火又钻进王三炮的心里,像虫子在上面一口一口地咬,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一连串儿的打击让王三炮大伤元气,刚刚挺直的头又蔫成了老菜瓜。
咋就这么倒霉呢?王三炮那天去找半仙。半仙是这带有名的算命先生,据说可替人逢凶化吉,避灾为安的。王三炮路顺时哪信这一套,现在不得不耷拉着头走进了半仙家。
半仙焚烧了一堆黄表纸,又闭着眼睛掐算了半天说,你家祖坟不行,风水不好。问题就出在你家祖坟上。
迁祖坟?老辈人也不同意啊。王三炮说。
另有破解之法。半仙缓缓地说。
你说,你说。王三炮急切地问。
破解之法全仗自己之心。半仙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了捏说,俗话说得好,心诚则灵。
王三炮马上明白了,又掏出一沓钱,呈上了说,先生明示。
半仙说,大凡风水宝地,需前有水,后有山,山生骨,水生灵,阴柔相济,家族兴旺。你家前面不是有条河嘛,远是远了点,但也无妨。关键是后面没有山,无山则不稳,凡事怎可安生。
这可怎么办,我怎么能让祖坟后面有座山,即便愚公再世也难办啊。王三炮愁眉紧锁了。
我们虽不可移山,但可移石,山是石之子,石是山之父,所谓石生山,山聚石也。所以石即是山。半仙说。
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在祖坟后面放块大石?
就是这个意思。半仙说。
这也难办,我家祖坟后面是王栓家的地,放块大石头既占地又碍事,他不会同意的。
凡事有明必有暗,所以山也有明暗之分。半仙说,你可以造一座暗山。
何为暗山?王三炮问。
入地为暗,你可以将大石放入地下。半仙这么一说,王三炮全明白了。
这事好办,王三炮吊车出动,跑了一百多华里,从山上运来了一块巨石。王三炮将巨石运回村里时,全村人都疑惑了,就像他当年轰隆隆将吊车开回老井村那样稀罕。
王三炮当年当过兵,工程兵,提干没弄成,王三炮回到老井村心灰意冷,农活不干,吊儿郎当。那时葛芝兰还没过门,差点跟他吹了。
王三炮被王木头骂得不行,便出门到处跑,跑到油田去找战友。
后来王三炮便开来了一辆轰隆隆的大家伙,那时候人们还不知王三炮弄来这辆几乎散了架的破家伙有啥用,后来慢慢才知道,王三炮这敲敲那修修,修补修补,新漆朝上面一喷,焕然一新,仿佛来时还是个老太太,再出去却成了新媳妇。这一来一去,王三炮就已经赚了大钱了。
老井村再次疑惑地问巨石何用,王三炮不像当年那样口若悬河了,只嘿嘿一笑说,有用。
半仙已经交待了,事情只可暗做,既为暗山,事情也必须暗做,这叫和谐统一,步调一致,做得越保密越灵验。所以,巨石的用途王三炮是不能讲出口的。
巨石是后半夜被王三炮用吊车运到祖坟上的。埋掉巨石,造成暗山,需要挖一个巨型大坑,巨石可以隔着路吊放在祖坟后面,但大坑必须毁掉王栓家的一块地。小麦已长出老高了,毁掉了可惜,王栓发现了肯定不愿意,不过这没啥,多给点钱就成了。问题是如何埋掉那块巨石,半仙说过了,越人工越好,那样更原始,更原生态,更接近祖宗们的在天之灵。对这个问题王三炮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巨石旁边可以挖一个大坑,尽量离巨石近一些,最好将巨石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裸露在坑的上沿,然后用铁杠轻轻一撬,利用杠杆作用,巨石便能轻松落入坑中。
这个办法最原始,就按这个办法来。
铁锨、铁杠是事先准备好的,王三炮开始了这个秘密的行动。为了将巨石埋得更深,不至于以后影响王栓的农作,王三炮想尽量将坑挖得深一点,为此累得一身大汗。
老井村这带多半沙地,最适合种植枣树,所以也称枣乡。土质松软,也相对好挖一些,但毕竟坑太大,等大坑挖得差不多了,已经两个小时过去。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王三炮松了一口气,准备点根烟歇一歇。这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吊车声,震得地面微微颤动。旁边便是通往邻村的路,这个时候吊车轰隆隆地朝外开,一定又有消息传来了,上面一定又要进村检查。
每逢上面检查,王三炮经常这样打游击。担心身边的吊车,又担心家里停放的那辆吊车,王三炮想探出头看个究竟,便顺坑边提溜下来的钢丝绳朝上爬。
王三炮的手刚刚握住钢丝绳,突然一种令人心惊的声音在隐隐地响,仿佛一条巨蟒从地上爬过,嚓嚓嚓,嚓嚓嚓。那声音夹杂在震得地面微微发颤的吊车声之中,极其恐怖。一把细土散落在头顶,王三炮暗叫不好,抬头望去,发现头顶上一个巨大黑影铺天盖地落下来。
就这样,在这个世纪之初的那天凌晨,王三炮给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就像一出演得正好的大戏,突然因了什么缘故,提前谢幕了。
王三炮在巨石落在头顶的瞬间,蓦然想起了那夜的梦,那个面容模糊从后台钻出的人,朝台下挥手,都回吧,散场了,散场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