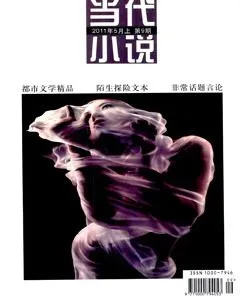伙伴之死
2011-12-29梁开文
当代小说 2011年5期
当时我正在宿舍里看一部喜剧片,电话里听到斌说的消息,我竟然勃然大怒,虽然斌是我弟,我还是忍不住骂道:
“操,别拿死开玩笑。”
“哥,我没开玩笑,路路真死了。”然后是哽咽,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一
斌和路路同岁,比我小两岁,我们同村并且是邻居,位于村子东头。我们村在梁山县的东北方向,虽然大家以水泊梁山为豪,我敢说村里大部分人都没读过《水浒传》,虽没看过这部名著,可是村里人身上却有莫名的江湖气。不知是因为水浒遗风还是每个男人都要经历打架流血的年龄,我们村东头和西头的少年可谓势不两立,经常发生武斗。那时候斌和路路是我们的主将,胜多败少。小学的时候,要去离家一公里远的学校上学,由于怕西头的埋伏,我们无论上学还是放学都在一块儿,回家之后不写作业而是马上到场院里集合,锻炼新的打架招数,那时貌似打架斗殴才是最重要的事。
梁山县的周边开设了许多武术学校,斌和路路就被家里送到了武校进行学习。当时我和我们东头的伙伴还经常去镇上武校看他们,武校封闭式管理,但是我们可以隔着门栅栏寻找斌和路路的影子。每当看到他们,我们都大声叫喊,他俩听到声音就趁休息时间跑到门口。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是那种只有在武校才会穿的衣服,色彩斑斓,与我们死板的校服截然不同。当时武校的墙上刷着硕大的红字:强身健体,保家卫国。
因为村东头的打架主力转校,我们的气势和实力明显不行。记得有一次,我们被西头的一伙围攻,一个子很高的家伙一直挑衅我。说来惭愧,我自幼体弱,打架从来没有赢过。但是那天我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原因我忘了,可能是考试又没及格,或者被其他人嘲笑上厕所没有带纸,总之是有满肚子的火气。面对高我一头那哥们的挑衅,我发疯似的脱下拖鞋,拿在手上朝着那张挑衅的脸就是一耳光,当时气氛尴尬,那家伙没想到我敢打他竟然愣住了,打完之后我立马感到后怕,穿上拖鞋对我们村东头的伙伴喊:快跑。
等到我们跑远之后回头看,那家伙才回过神了,搬起一块大石头就朝我们追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穿拖鞋能跑这么快,一溜烟跑回家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时候虽然村子两头的少年势不两立,但是大人们还是相敬如宾。所以当时我们打架都在村外,在村里虽然大家都不说话,但也不至于动手,而且打架之后双方回家也不告诉爸妈。但是那天那家伙真急了,搬着石头到了我家。我爸妈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让人喊来了他爸妈,两方协调之下才将问题解决,当然我家负责了医药费。
事情解决之后,虽然我被爸妈一顿教训,但是得到了我们东头伙伴们的推崇,甚至后来也传到了身在武校的斌和路路耳中。斌说:“哥,打完就跑聪明啊。”路路说:“你那天要是不跑就是纯爷们。”所以我和斌是亲兄弟是有原因的,而路路的性格从小就那么执拗。
宝军的爸爸是村里最有名的理发师,夏天炎热,东头的小男孩经常一块儿理成光头跳进池塘游泳。邻居大婶看见我们几个男孩就发愁,她边看我们边叹气:这七八个小男孩长大之后娶媳妇得花多少钱啊?仿佛我们几个娶媳妇都得靠这位大婶出钱似的。我们不管那么多,扑腾起来的水花充满了快乐。路路晚长,那时个子最小,我们老在河里欺负他,并说:找你姐姐来帮忙啊。
村后面有一片梨园,每到收获季节我们总会去打打牙祭。当然是有人望风,有人潜入。记得有一次,我、斌、路路还有宝军和志超一块儿偷梨,结果竟然失手被抓住了。梨园主人是个外来户,但是毕竟我们做的事不光彩,也怕被送到家里挨揍,便老老实实地接受教训,一顿“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能偷鸡摸狗不然长大了发展到抢银行就会抓进监狱枪毙”的教育和恐吓之后,梨园主人问我们:“你们几个都叫什么?”我们不愿把自己的真名说出来,从我开始,我说:“我叫小斌。”斌说:“我叫小文。”宝军说:“我叫志超。”志超说:“我叫宝军。”轮到路路了,他看到没有别的名字可用了,就一直没说话,因为急于脱身,我顺嘴对梨园主人说:“他叫兆成。”结果,我们不仅把自己的名字给透露了,还透露了路路他爸的名字。
兆成正是路路的父亲,一个在村里响当当的人物。直呼兆成其实不礼貌,因为论辈分我得叫他老爷爷,辈分和年龄相差太大,而且兆成不是那种把伦理看得很重的人,于是我就直呼其名了。路路他爸是我们村里当时惟一的高中生,可是最终没有考上大学。按照村中风俗娶了路路他妈,接连生了三个闺女。虽然路路的三个姐姐貌美如花、百里挑一,当时过家家,她们哪一个做我媳妇我都愿意。他爸却一直眉头紧锁,沉默不语。直到第四胎生了路路,他爸的嘴才好像泄了洪的大坝,见人就聊,有关天文地理、施肥种地、上学辍学无所不谈,而且一聊就是老半天。我作为路路的小伙伴,又是同样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所以每次放假都会被路路他爸拉住聊上半天。我们走到村头的杨树下,路路他爸搬块砖头往地下一扔,然后重重地把屁股撂在上面,而我就紧靠在那棵杨树旁边,用手抠着杨树皮,十分纠结地和二十年前村里的第一个高中生开始聊天,而且一聊就是不管风吹雨打直到天昏地暗,末了,路路他爸屁股周围一圈烟头,旁边的杨树被我剥掉了一层树皮。
他爸对我说:“得考大学啊。”我说:“嗯。”我说:“得让路路考大学啊。”他爸说:“那当然,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后来他爸发现路路在武校里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便在初中时候把他调进了我们镇一中,当然我弟也一块儿进了那所我已经毕业的学校。
二
我弟和路路在武校的时候就被同学称为“二梁”,意思是吃饭睡觉撒尿拉屎,总之是无论干什么都在一块儿,进了初中之后也是如此。初中生活开始住校,这方便了两人的为所欲为。这个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对两人的斑斑劣迹也是通过爸妈等人的转述。
大家都说大学生活是半个社会,可我们的初中风气就已经是一个黑社会了。我经历过三年的初中生活,其中的血雨腥风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宿舍很大,是那种瓦房的教室改造而成的,每一排瓦房有三个宿舍,我们宿舍就在最边上,我好像是三班,中间的是二班宿舍,另外一边是一班宿舍。一个班几十个男生挤在一个宿舍里,记得初一时,晚上熄灯后大家都没有马上睡觉的习惯,而是互相聊会儿天。
一天晚上,宿舍门突然被踹开,呼呼啦啦地进来十几个光着膀子的人,有的拿棍子,有的拿扫帚,有的拿砍刀。我们瞬间安静了,只听见他们在咆哮,意思大概为:你们宿舍吵来吵去还让不让人睡觉?再吵把你们宿舍给一锅端了。看到我们老实了,他们才趾高气扬地离开。临走时说了那么一句:昨晚一班围攻咱们宿舍,今晚咱们围攻三班宿舍,面子挣回来了。原来他们围攻我们是为了找面子,可是我们三班的面子去哪找呢?围攻四班宿舍?可是不在一排,理由不充分。回过头围攻二班宿舍?人家来十几个人就把我们所有男生给镇住了,哪还有什么胆反过来去人家宿舍。哎,当时我知道了,蛋何其多,三班是模范。打架不行,就忍气吞声地学习吧,我这么安慰自己。
斌和路路不同班,所以在班里就难免形单影只。可以这么说,他俩进入初中的时候肯定抱着好好学习的想法,可是那个学校环境真不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尤其俩人还接受过武校的磨练,脾气更加暴躁。路路进入学校后执拗的性格不改,经常为了一件事和同学争执到底,所以得罪了不少人。记得有一次,路路从家里拿了许多好吃的,回到学校就开始分给同学,但是惟独没有分给班里最强壮的一个,没有分给他是因为路路不喜欢他在女同学面前像个奴隶,在男同学面前又把男同学当成奴隶。强壮小伙没得到好处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在宿舍就把路路修理了一顿。路路找到了斌,斌属于那种性格硬中带软的,所以和本班同学交情不错。听到路路挨揍,斌立马找了十几个同学,趁着下课时间闯进路路班,把那个强壮小伙一顿猛揍,斌在旁边喊:差不多就行了。可是路路不依不饶,最后朝着他的脑袋踢了一脚,这一脚把脑袋踢成了脑震荡。
路路他爸赶到学校,赔礼道歉,花钱请客,终于把事情摆平。“你得好好学习,少打架。”路路他爸一贯的宠爱。“知道了。”路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终于路路成为班里的老大,后来又和斌合伙,慢慢地打出了名堂,在学校走到哪里身后都有一群人跟着。这种局面持续到初二。
但是人外有人,一次斌和路路过完礼拜天回学校,在路上被一伙人截住了。其实他们就是抢劫钱财的,这在我们那里也很正常,法律什么的对他们来说还不如下酒菜去得快。像我这样老实点的孩子,给点钱就算了。可是路路和斌却不想受到欺负,捂着兜里一星期的生活费不撒手。劫匪其实就是高年级的学生,一气之下开始动粗,斌看情况不妙大声喊:“路路,快跑。”这一喊就泄露了路路的身份,那些劫匪早就想灭灭路路的威风了,没想到这么巧给碰上了。这样路路更跑不出去了。斌和路路被一顿狂揍,斌被打断了胳膊,路路也是伤痕累累。
我爸把这件事告诉我时相当气愤,他说:“这兔崽子还给我说胳膊是翻墙头时摔断的,谁没翻过墙头啊,能摔成那样?”终于斌受到了惩罚,退学在家,开始了大多数农村青年习惯走的那条路,打工挣钱,有梦想却很难再实现。路路却还坚持上学,在继续上学这件事上他爸也同意。不过不同的是,路路想回学校报仇,路路他爸想让他考大学。
终于,在宝军的帮助下,路路收拾了那几个劫匪。宝军早就辍学,在县城闯荡,听说路路在学校里有摆不平的事情,便开面包车到了学校,车里的人不是学生年龄,下手极重。路路成功报仇,也惹下了大祸,被学校开除。虽然此事发已经许多年,但是现在镇一中还有路路的传说,“当年咱们村的路路那叫一个厉害,初一就当上老大,初二就联系上了县城里的流氓来学校打架,路路那时候头发很长,还有刺青。”现在村里的刚上初中的小孩这么给我描述。
被学校开除后,望子成龙的他爸托关系让路路转进了县城的中学,这一决定没什么错,却暗藏汹涌。
三
其实自从我上高中就很少见到路路了,因为高中一个月才放一天假。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路路转到县城学校后的一个春节,我们几个相约去梁山动物园玩,那次游玩大家心情愉快,还拍了许多照片。照片放到照相馆冲洗,冲洗的钱我垫上的,后来元宵节把照片拿回家,大家平均摊钱。其实每人也就五块钱,但是我使坏,给路路说,你照得最多,得给十块钱。路路说了句“真操蛋,就这几张照片还得十块钱,不过拍得挺好看。”就把钱给了我们。现在那些照片还放在我们各家的相册里,大家纯情如少年,笑容如阳光灿烂,身后是浑身肮脏的鸵鸟做背景却丝毫不影响我们合影的心情,可是路路却不在了,我怀念那个被我开涮过的伙伴。
路路终于没有满足他爸的大学梦,读完初中就退学了,路路不仅退学而且在梁山小城开始了混混生活。
考上大学之后,我逐渐和路路联系少了,有一次往4/925wEEL4AQbI2MwOKXtXFdAo7ygDGN4WEi/RMiaKQ=家里打电话,我妈告诉我家里正在分地。其实分地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娶走女儿或者老人去世的家庭把地退给村里,反之,娶来媳妇或者新添小孩的家庭就会得到村里的分地。那时候我就想到了路路家,路路家六口人,他的三个姐姐都准备结婚了,假如分地的话,他家就会由六口人的地变成三口人的地,对于以土地为生命的农民来说,这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谁都不想把手里的土地拱手让人,虽然在道理上没有任何纰漏。
最后所有的家庭都在村长的带领下重新规划了土地——除了路路一家。路路家现在三口人,却拥有六口人的地。
回到分地的那天。
由于拒绝交出土地,村长带领村委会和其他应该分到土地的村民气势汹汹地冲向路路家,此时路路家空无一人,大门紧闭。气急败坏的村长拿起铁锨砸向路路家的大门,看到村长已然如此,其他人也纷纷拿起自己手中的工具,不大的郑庄村回荡起“咣咣”的金属撞击的声音,据说持续了很久很久。可是到了傍晚,村里面突然来了好几辆面包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不以为然,以为走亲戚的摆谱为之呢,可是面包车径直开向了村长家的方向,刚到村长家门口,就从每个不大的面包车里面跳出来十几个年轻人,领头的恰好是路路,裸露上身,刺满纹身,手持砍刀,冲向村长家,庆幸的是,村长家那时候也正好大门紧闭,不然后果不可估量。
村长家没人,可村里面好多人都在,那几辆面包车在村里转了好几圈,伸出车窗外的砍刀在落日余晖下闪闪发亮,很漂亮,就像彩虹的一种颜色。
村长家后来换了门,路路家的地也没人敢动了。
大四下学期,路路突然到了济南,顺路找我玩,关于那天的回忆我现在还能记住几点:首先,路路不是一个人来的,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身边跟着另外两个人,一个平头,一个板寸;其次,我请他们三个在学校餐厅里吃的饭,几碟小菜,几句闲话;再次,吃完饭,那个小平头尿急,走到学校北门时就要在保安的传达室后面解决问题,被路路强行拖走,路路很是尴尬地对我一笑;最后,他们临走叫车时,我帮他们拿了一下那个塑料袋,有点重,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路路第二天离开了济南,临走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济南的妞儿不如梁山的辣。”
那年十月一日,我回家一趟,待了三天。在上午掰玉米下午摘棉花晚上倒头就睡的辛苦中庆祝了国庆节和中秋节。就在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路路开着一辆普桑停在了我家门口。路路一头长发,比我高了许多,虽然路路貌似凶神恶煞,但是我仍然觉得他是和我一块儿长大的那个小伙伴,受到父亲的宠爱,承载着父亲未完的期待,和他们在一块儿很踏实,很心安。我调侃他说:“你这车连个假车牌都不舍得挂,不怕交警查你啊?”
路路说:“没事,有一次我开车闯红灯,然后又故意退回来,问旁边交警主动认错怎么惩罚,梁山交警只敢打哈哈。”后来又和路路在很是凉爽的秋夜谈了好久,路路告诉我,那个和他一起到济南找我玩的小平头因为四处作案已被拘留。路路还告诉我,那个有点重的塑料袋里面装的是一把左轮手枪——200米之内的射程,如果瞄准心脏,就能致人死亡。
上次见到路路应该是去年春节宝军结婚时,宝军找到老婆之后就慢慢地疏离了那个圈子,挣钱盖房娶老婆,开始了正经日子。宝军结婚时,我给宝军当的婚礼司仪,而路路开着一辆雅阁给宝军当做迎亲车队,我问路路,这么快就换车了?路路说,那是别人还不上高利贷抵押的。我说,你得自己弄辆好车啊。他说,这没问题。
几天前的深夜,路路又去收高利贷,可是对方闻讯提前逃跑了。路路便和同伴驱车追赶,当时的夜晚肯定和以前的夜晚没有什么异样,只不过后来的悲剧让那晚增加了血腥气。飙车的激情可以让人忘记危险,凶神毫无预兆地到来。在一个路口,路路的车与一辆工程车相撞。
当晚凌晨一点,宝军和已经怀孕的老婆正酣睡,突然听到了敲门声。路路他爸急切地说:“快,路路出车祸了,你快带我去医院……”斌在清晨接到了宝军的电话,听到宝军说到路路死亡的消息时,斌也是和我一样的反应:“操,开什么玩笑。”甚至斌到医院门口时,还想着路路也许就是断条胳膊伤条腿,几个月之后照样活蹦乱跳。可是病房内白色床单盖在路路全身,旁边是已经声音嘶哑昏死好多次的路路父母。斌和宝军站到床边向曾经一块儿打架、一块儿拍照、一块儿偷梨的伙伴最后告别,死者满身血迹,生者满眼泪水。宝军说,路路出事时开得是辆好车,可已经完全被撞烂。
我无法修饰那种伙伴突然死亡的感觉,记得小时候我经常搂着路路的膀子走路,那种有所依靠的感觉让我轻松又踏实。可是现在,我回忆起这一幕,想重温那种感觉,我试图将全部的重力压在路路身上,可是路路开玩笑似的突然消失了,我晃了一下,抓空的感觉击败了失重的我。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