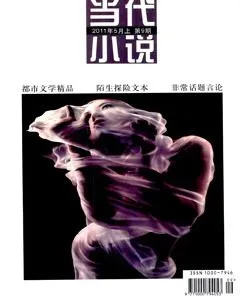单身汉杜伟亮(短篇小说)
2011-12-29林宕
当代小说 2011年5期
杜伟亮在廊檐下对着手机说,娟娟,你跳的“插秧舞”肯定不规范,却好看;我妈跳的话,肯定跳得规范,却不好看;我呢,假如我跳的话,肯定是既不规范又不好看。他尽量压低自己的嗓音,在说的过程中,他还不时地往四周看。他前面的石街上人来人往的,都是些陌生人,也没有谁留意他。有谁留意他呢?有谁知道他杜伟亮是个“袋里装满钱,心里盛满爱(这是娟娟给他的话)”的男人呢,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真有男女觊觎他这个在廊檐下打手机的男人,相互间陌里陌气的,怕也是白搭。他记得娟娟把这两句话送给他时,他惊得一跳,这不是当下每一个女人都想嫁的男人吗?我哪有这么好啊,我这么好的话,怎么会快四十岁了还在过光棍节?娟娟用指头点一下他的额头,正是因为你这么好,所以还在过光棍节,没有女的配得上你啊。
廊檐是一座古建筑的廊檐,共有六个角,他站在了其中的一个角下面。他身体左侧的一个檐角下,也待着一个中年人,走几步,就转身,又走几步,再转身,好像有谁规定他必须要待在檐角下。中年男人头发蓬乱、目光呆滞、神情沮丧。他不像是一个买卖遭受挫折的生意人,更像是一位“婚内失恋者”。“婚内失恋者”这个名称也是娟娟告诉他的,娟娟告诉他时虽然没有像另外那次一样让他惊得一跳,可也让他迷惑了好一阵。据娟娟讲,婚内失恋其实是伴随着婚姻制度的确立就已经存在着的,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它,不愿意面对它而已,婚内一方的失恋有来自于配偶的,又有来自于婚姻之外的异性的。那婚内失恋现象多不多?杜伟亮问娟娟。很多,很普遍,娟娟说,某种程度上,在我们周围,婚内失恋者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了癌症患者,而患上婚内失恋症的病人所承受的痛苦也是巨大的,要远远超过婚外失恋,如果婚内失恋是一只追赶着你的猛兽的话,你根本没法逃脱,因为婚内失恋者有婚姻这堵围墙把你围着,而婚外失恋者则没有这堵围着他的围墙。娟娟的话,让杜伟亮的心里无端地生发出了一种对婚姻的惧怕,以前这种惧怕也曾有过,在听了娟娟的话后,这惧怕感明显强烈了。娟娟又说,虽然婚内失恋现象一直存在着,可只有到了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人们才开始能够直面它了,而“婚内失恋者”这个称谓也就是最近被民间的社会学家冠名的。
杜伟亮头顶上的檐角是个倒挂的珐琅质的狮子头,这也体现了杜伟亮所在的王家角镇里许多老建筑的风格,龙、凤、麒麟、骏马、斗牛,等等,要么骑在屋脊上,要么挂在门楣上。好多动物的真身早已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却以这种方式留存了对它们的记忆,也在自己的身上保存了隐秘的兽性。杜伟亮继续对着手机说,我干脆不来看你们的演出了,人山人海的,我在“蓝屋”等你。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很嘈杂,可杜伟亮还是听清了娟娟的略带责备的话,你就想到在那里等我,你就想着那事。你不来看演出,我不去那里。
王家角镇东湖街街梢有一间杜伟亮祖上留下的老屋,本来一直空关着,一年前,杜伟亮把老屋重新装修了一下。装修好的那一天,杜伟亮领着娟娟去看了,两人走到小屋后面的那个小院子里,看到院里的一角正开着蓝盈盈的鸢尾花,鸢尾叶片则碧绿青翠。那些鸢尾花宛若蓝色的蝴蝶,就在一片碧绿青翠之上翩翩起舞。娟娟就说,就把小屋叫“蓝屋”吧。杜伟亮说,好的,就一直叫它“蓝屋”,即使这花谢了也叫。娟娟说,不会谢的,这花永远不会谢。杜伟亮看到那些蓝色的蝴蝶已经飞到了娟娟的眼睛里,变成了娟娟眸子上蓝色的火苗。
娟娟他们是在王家角镇的东广场那里演出,在石街上往东走七八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可杜伟亮还是没有迈下廊檐下的石阶,迈上石街。他想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就有些怕,虽然几天前娟娟把这场“王家角镇群众文化艺术节”的演出票子给他时,他表现出了要观看的浓厚兴致。
杜伟亮还是直接到了“蓝屋”。娟娟在演出结束后还是来了。杜伟亮没有去看演出,娟娟仍会来,这是在杜伟亮的意料之中的。娟娟甚至来不及卸掉脸上的妆,就跳“插秧舞”一样跳到了杜伟亮的身边,杜伟亮的激情也就立刻被娟娟袅娜的体态、粘人的热乎点燃了。
现在,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娟娟虽然长得很漂亮,左脚却是跛的。但是,跳舞和跛脚并不矛盾,特别像娟娟,当她刚跳罢了一曲优美的舞蹈重新开始走路时,人们发觉她原来左脚有些跛,就惊讶了,惊讶的同时,娟娟的舞蹈在他们的心目中立刻升华了。所以,娟娟的跛对于她的舞蹈反而是有好处的。娟娟跛得不是很严重,一般情况下,当她走路走到第三步时,人们才可以看出来她的跛。看出来后,她的舞步就踏在他们的心上了,她的美貌就像清水刚洗过一样更亮眼了。娟娟对杜伟亮说过,她没有得小儿麻痹症的福分,她的左脚是小时候被老家的驴车压坏的。娟娟的讲话有时会表现出难得的幽默。一位残疾女青年能表现出这种幽默,只能说明她既是豁达的,又是聪明的。
是的,娟娟是极其聪明的。当她第一次和杜伟亮有了那事后,她就说,你放心,我不要你承诺什么的。当时,面对着这位有过短暂婚史的女青年的话,杜伟亮哑然失笑,他也表现出了属于他的智慧,他说,我知道,你也不想承诺我什么。两人就相对而笑。彼此的笑都像水洗过一样显得明亮、透彻。为了强化这种明亮和透彻,杜伟亮甚至还试图去扮演一位好大伯的形象,他在一个周末的黄昏,带了好多卡通玩具去看望娟娟的儿子。离异后的娟娟是带着孩子从江北来到江南的王家角镇的。江是一条全国有名的大江,大江像是一条人为开掘的巨大沟壑,把江南、江北的人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不知从啥时开始的,江南人嘴里所唤叫出的一声“江北人”是包含着鄙视成分的。可娟娟这位“江北人”却让杜伟亮以及他身边的人第一次把鄙视的成分从“江北人”这三个字上剔除掉了。和跛脚一样,“江北人”身份竟反而衬托得娟娟更好看、更与众不同了。杜伟亮后来想,会有那么一种可能的,只要现在娟娟结婚,身边有个男人,当然不是杜伟亮这样一个地下的、不为人知晓的男人,那么在她周围人的眼里,她的跛脚、“江北人”身份、只身带来一个拖油瓶的身份可能会立刻还以本来面目,不再令人赏心悦目,甚至会不能卒读了。所以,这也是杜伟亮不愿与娟娟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的原因之一。
从江北来到江南后,娟娟通过她的一位在江南某县当局长的表亲,到杜伟亮任站长的王家角镇社会救济站当了一名合同工,负责被救助对象的造册、登记工作。
救济站门前的场角上有两棵树干很挺的楝树,在这一天,这两棵楝树成为了王家角镇龙星村唐宝妹老人的做小生意的特殊工具。唐宝妹把一根长长的铅丝绷紧在两棵楝树中间,然后把自家田里收割上来的几扎韭菜挂上铅丝。大部分的韭菜她则放在了树下的地上。由稻柴捆成的“韭菜扎”挂上铅丝时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农民们为了增加蔬菜的分量,往往在夜间把蔬菜浸在水里,再在第二天早上把吃饱了水的蔬菜担到城里或镇上去卖。
唐宝妹把“韭菜扎”挂上铅丝是为了招揽顾客,这铅丝上的韭菜就是她的店招牌。
你们不补足我家的救助金,我就把摊设这里,我就把市场管理费省下来。唐宝妹说。
唐宝妹的瘸腿孙子小五就坐在地上的韭菜堆边,神情淡淡地用一根枯枝在地上拨拉着。韭菜堆离救济站的门口也就三四米的距离,这像什么样?这让救济站里的员工感到难堪。大家都朝杜伟亮看,看他脸上的表情,可他脸上啥表情也没有。
副站长阿贵说,你孙子是两级伤残,不是一级伤残,只能补助这么多。再讲,几级伤残也不是我们定的,是区残联定的。阿贵的话已经给唐宝妹讲过多次了,可唐宝妹就是不听,就是讲救济站欠了她家救济费,就是要把救济站的大门口变成农贸市场,面对这个农贸市场,救济站站长杜伟亮脸上居然啥表情也没有。
唐宝妹没有朝楝树前方的西湖街叫卖,只是与她孙子一样坐在韭菜堆边。西湖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每隔一阵有人停下脚步,走到唐宝妹的身边,买上一扎韭菜,然后用有点古怪的眼神看一看王家角镇社会救济站的门牌,再重新走下石阶,走上西湖街。工作人员小荣再也忍不住了,再也不看杜伟亮的脸色了,他冲到了唐宝妹的身边,一手试图要把她从地上提拎起来,一手指着西湖街,说,他们以为我们救济站在贩卖韭菜了,你走,你赶快走。这时候,救济站里的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救济站的门牌已经成了唐宝妹真正的店招牌了,人们,会认为前来购买韭菜就是对社会救济事业的支持,人们这么一认为,唐宝妹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好。
站在门口里侧、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的杜伟亮想,这老太真是个聪明人啊,简直跟娟娟一样聪明。门外,唐宝妹在被小荣拉扯后,舞动起了自己的手臂,还叫嚷,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克扣我救济金,还想对我这个老太婆动粗?西湖街上行人开始围过来。
唐宝妹说,我要天天过来。
杜伟亮一步跨出了门槛,走过去喝下了小荣,然后对唐宝妹说,你卖吧你卖吧。唐宝妹立刻不吱声了,一歇后,看住杜伟亮说,我看你慈眉善目的,是个救济站站长的样子!可临到头了,却还是不愿补我,是个硬心肠的人。
其实,杜伟亮在唐宝妹第一次来救济站时,心里就涌出想满足唐宝妹的念头的,这个念头还挺强烈。他觉得不满足唐宝妹的要求,而宁愿不时地为分管副镇长去饭店料理餐后的帐单,这实在是有违天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要维护他救济站站长的尊严,像唐宝妹这样的人多了,他不能让人轻易突破他的权力范围,他要像守住自己的单身身份一样守住一名站长的堡垒、尊严。这就让杜伟亮内心充满矛盾了。他感到矛盾这把钝锯始终在锯他的肉。不过,锯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痛感就慢慢轻了。
娟娟已经一声不吭地站在杜伟亮的身边,别看单独跟杜伟亮在一起时娟娟叽叽喳喳地话很多,在单位上班时她却是不怎么说话的。平时,她就在救济站最北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静静地做着登记、造册工作。
杜伟亮对着救济站里的所有员工挥了挥手,回。救济站里的员工们就都回了。娟娟回了后又出来了,左右手各端着两杯茶,一杯给唐宝妹,一杯给她孙子。杜伟亮已经看出来了,娟娟其实跟他一样,心里也是想满足唐宝妹的要求的,也是想补上唐宝妹的救济金的。他与她是一样的人。可是,有些事只能是想,却落不到行动上。娟娟曾经讲过杜伟亮是位“袋里装满钱,心里盛满爱”的男人,其实讲到底,娟娟的这句话是对杜伟亮这位救济站站长的概括,原来说的是这个站长的职位,一位社会救济站站长确实应该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对于这个站长来说,袋里没有钱当然是不行的,心里没有爱则更不行。可是,他为什么常常感到自己不能随随便便地释放心里的爱呢?
下班后,刚走上西湖街,他就往娟娟手机上打。然后,两人就来到了王家角镇龙星村。唐宝妹的儿媳妇回安徽老家了,在一家民营企业里做挡车工的儿子还没有回家。杜伟亮把一沓钱放到唐宝妹家的方桌上时,十分担心唐宝妹会嫌少。可唐宝妹已经意识到了这钱是杜伟亮私人摸出的,她没有拒绝,当然更不会嫌少,她只是抓住杜伟亮的手,说,我明天不来救济站门口设摊了,你放心,不过我仍旧等着,等着你们把克扣我的救济金发下来。然后,她停顿了一下,眼光在杜伟亮和娟娟的身上来回转了一圈,又开口,你们很般配。或许这话是唐宝妹对杜伟亮、娟娟此行所表达出的一种特殊谢意,可杜伟亮还是让她的话吓了一跳。
回来的路上,杜伟亮说,我们今天去偷偷给钱,为啥不能名正言顺地给,非要偷偷地去给?
娟娟说,只能偷偷地,就像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多事情只能这样。
可16f35240d7037a2f755590c37ed8fffb是我们很般配。
很般配就一定有结果啊?
杜伟亮笑了。娟娟讲得对,很般配不一定有结果。不过,对于他杜伟亮来讲,没有结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结果的害怕。杜伟亮周围的好多朋友把婚姻比作了监狱,这些朋友中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众所周知,监狱是令人惧怕的一样东西。可是,杜伟亮老家有一位他小时候的伙伴由于偷盗进监狱了,三年后出狱,这位伙伴竟然变得白白胖胖的,简直像是从疗养院里出来的。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政府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使我们的监狱在人性化道路上迈进了大大的一步,另一方面也说明,监狱于人,还是因人而异的。没听说吗,国外有人由于衣食无着还自愿要求进监狱呢。那么,是不是可以做如此的比方呢,就是要求进监狱的人的那种衣食无着的状态,等同于单身男人惯常有的散漫、无序甚至万事的潦草和颓废,可一旦进了婚姻这座监狱,在失去自由的同时,单身男人身上所惯有的种种毛病也会消失了,婚姻这座监狱会立刻改造出一位焕然一新的男子。这位焕然一新的男子有时在杜伟亮脑幕上走动时,确实也曾让杜伟亮的精神为之一振。可是,在精神一振之余,他转眼一想,散漫、无序甚至万事的潦草和颓废又何尝不是一些男子所追求的东西呢?杜伟亮再一次陷于矛盾之中。看来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要让矛盾这把钝刀割自己。
他们回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白石路,白石路两边的农作物在微风的吹拂下像是漾动着的绿色波浪。黄昏的风里带着绿色植物的清新与远处农家屋顶上飘过来的正在烧煮着的晚餐的香味。一只黄鼠狼在他们前面几十米的远处快速窜过白石路。他们继续往白石路的尽头走去,杜伟亮的车停在那里。
杜伟亮说,我一开始就想把钱补给唐宝妹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你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蛔虫说不上,可我晓得你想得跟做得常常不一样。
那你晓得我现在在想啥?
那要看你想好后怎么做的,再推断,反方向推断。
哈哈。
哈哈哈哈。
这段对话让两人很开心,他们的笑声惊起了蛰伏在白石路南面农田里的一只小鸟,小鸟“唧”的一声腾空而起,消失在空中。
杜伟亮说,我在想,明天,我们到“百合楼”去喝咖啡。
娟娟像是没有听到杜伟亮的话,没有吱声。杜伟亮就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娟娟的脸色起了一些变化。
我不去,因为你常常想得跟做得是不一样的。娟娟说。
谁都知道,“百合楼”是青浦中心城区的一个空中平台,以前是城区南门的一个防汛瞭望台,现在被本城有名的“百合合百”婚介有限公司租用了,变成了一个空中的休闲场所。既然是婚介公司经营的休闲场所,可想而知,平时去那里的是些什么人。听说上“百合楼”还要凭票上,票子还挺贵。听说“百合合百”婚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锦平遇到认识的而又好多年没有谋面的中年男子,常常会问,你更新老婆了没有?李锦平的文化程度其实不高,可他这几年自从坐上了奔驰车后,就开始把一些书面化的语言运用到自己的口语里。李锦平和杜伟亮是认得的,有一次他竟然也这么问杜伟亮。杜伟亮说,我还单身呢,你没听说吗?结婚使人退步,离婚使人进步,为了进步,我干脆不结婚了。不过,一听杜伟亮还是单身,李锦平的眼睛还是亮了一下,连忙塞给杜伟亮几张上“百合楼”的票子,并说,要进步,先得退步。不过,今天的票是杜伟亮自己买的。
“百合楼”的下面是一大块没有浇上水泥的场地,种植着好多花,当然不会少了百合,可由于百合的花期短,所以,来“百合楼”的人往往在“百合楼”下还会看到三色堇、蔷薇、红豆、石斛兰等等。这“百合楼”下就是一个花圃了。楼上的人与其说是由旋转楼梯走上去的,还不如说是被地上的花托上去的。
今天傍晚,杜伟亮也是感到自己是被“百合楼”下的花托上去的,色彩和若有若无的香气像一双手,把他往楼上托,感受着这种托,他的身子有些酥软了。时值春末,白色的蔷薇花、淡红的石斛兰、深红的红豆等组成了一片缤纷的火焰,烘烤着上面的“百合楼”,看这态势,这花的火焰不把楼上的爱情烤熟是不罢休的。杜伟亮已经深深地感到,李锦平虽然只有中专毕业,可确实是一位高水平的商人,他把书面化的语言引用到自己的口语里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坐“奔驰”也是坐得其所,
他即将要把“奔驰”换成“保时捷”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
双脚踏上“百合楼”的楼面,杜伟亮才发觉楼面比他想象中大多了,足有四、五百平方米的样子。上次李锦平送给他票子后,他没有来,这次来了,才发觉“百合楼”丝毫没有空中楼阁的感觉,倒像是一幢大楼的一个楼层,不过这个楼层是圆的,沿着这个楼层的四壁,是一只只卡座。楼层的中央是一个像是供演出用的月牙型的舞台,舞台的北面有一个半圆形的长桌子,上面堆满了咖啡、水果茶、奶昔、鱼露等各种饮品。里面已经灯光通明,许多男女在饮品桌前穿梭,然后端着一只玻璃高脚杯走进卡座。杜伟亮问一位五短身材、脸上还长满粉刺的男子,怎么没有酒?
有酒的话要出事的,矮个男子说。
杜伟亮没有问出什么事,他已经从门边的司仪小姐手里拿了来宾编号,他属于“18”,他很高兴拿到了一个幸运的数字。矮个男子又说,待会儿要碰数字、滚珠结对、传花、抛绣球,还要看苏州歌舞团的演出。看来,矮个男子已经来过多次,对这里已经熟门熟路了。那么,在碰数字、滚珠结对等活动中,他就是数字“18”了,这个“18”会碰到哪个数字呢?他想着就走到了身体左边的一个卡座里。
对过,已经坐着一个女的了,正前倾着上身、低着头在打电话,光溜溜的长发遮住了她大半的脸,露出的小半张脸呈弧线型,白皙、光洁,有白瓷的质感。女子突然甩了甩头,露出了整张脸,并关了手机。弧线型变成了蛋圆型后,很怪的,女子脸上刚才呈现给杜伟亮的那种白皙、光洁的白瓷的质感突然没有了,原来她的脸色也有些黄、有些枯,明显需要爱情的雨露来滋润。女子扬起脸对杜伟亮微笑着。
杜伟亮也在脸上露出友善的笑。可他不想让自己化作雨露,来滋润女子的那张脸,如果这女子代表着另一个阿拉伯数字,他可不愿意让自己的“18”去跟那个数字“碰”。这时候,整个“百合楼”里猛地一暗,接着有镭射灯光晃了一下,镭射灯光只晃了一下,刚才大厅里冷灯光就变成了暖灯光,大厅也比刚才暗了好多。他发现穿着旗袍的服务小姐已经开始往卡座前的小桌上放饮料,也有男女自己走到大厅中央的长桌边,去拿各式饮料。
杜伟亮拨通了娟娟的手机,我坐在十三号卡座里,你怎么还没到?娟娟的票子是杜伟亮今天中午就送给她的,杜伟亮共买了两张票子,说,去凑凑热闹。娟娟说,去撞爱情?杜伟亮说,对,去撞撞看,说不定我撞上的是你。娟娟说,我们还不算撞上?杜伟亮说,我是指在那里,在“百合楼”里,那种爱情是要奔向婚姻的。
杜伟亮在打电话时,心里还在想,娟娟来了后会从司仪小姐手里领到什么数字?她来得晚,她的数字肯定很大,“碰数字”时,他会把他自己的“18”与娟娟的数字直接交给工作人员,然后让工作人员直接宣布这两个数字碰上了。好像也是刚才那个矮个子男子对杜伟亮说的,说卡座里一上来就相互有好感的人就是那样做的。两个数字碰上后,代表着这两个数字的一男一女就是今晚固定的“搭子”,在节目演出、游戏阶段,他们是一对组合,配合着与别的组合进行对抗或者联动。可娟娟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杜伟亮对着手机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娟娟说,家里有点事,再等一等。家里就她和她儿子,能有什么事?扫兴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在杜伟亮心里滋长了出来。
司仪小姐衣袂飘飘地走上了月牙型的舞台,朗声说:各位“百合楼”的尊贵的朋友,今晚皓月当空(其实没有),今晚花香弥漫(花香是在楼下),月洒爱,花传情,“百合楼”更是浓情一派(有些文理不通了)……
杜伟亮又给娟娟打电话,娟娟干脆说不来了。杜伟亮说,怎么回事?娟娟不说有点事了,说肚子疼。
这时候,司仪小姐宣布开场舞会开始。大厅里的灯光又暗了好多,楼顶上的镭射灯光又闪亮了几下,却不像先前一次那样晃眼了。杜伟亮的左手突然碰到了一样暖暖的柔柔的东西。原来是坐在他对过的那位女子起身了,拉住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左手,邀请他跳舞。
“你尊姓呀?”这女子的头发竟然长到了腰际。
“我是18号。”杜伟亮笑着说,想尽量表现得幽默些。
“我是23号,要不我们自由做对?”
杜伟亮已经搂住了长发女子的腰,她的腰比她的手更柔,更暖。闻香识女人,杜伟亮觉得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还是浓了一些。
现在,大厅里的光线更暗了,楼顶上的那盏镭射灯却在不间断地晃了,晃得很慢,光线也一点不刺眼了。他们跳得是慢三,可在转圈的时候,杜伟亮还是趔趄了一下,就在他重新摆正身子的同时,大厅里突然响起了尖叫声,然后整个大厅乱作一团。
当大厅的光亮重新变成雪白的冷光灯的光亮时,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有人跳楼了,从9号卡座的窗口往楼下跳的。
不供应酒,也出事了。杜伟亮想起了矮个男子的话。然后,尾随着别人,往楼梯口急走。一位中年女子在楼梯口脱跟了,可她很快闪到了一边,让杜伟亮他们顺利地往楼梯上走。
走下楼梯后,夜的岚气一下扑面而来,凉凉的。杜伟亮看到花圃里早已挤满了人,他感到自己的嘴巴干涩得要命,一颗心晃悠晃悠的,像是要晃出他的体内。周围虽然很幽暗,可他突然在花圃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先是站着,后来在人群的边缘走了起来,一颠一颠的。
是娟娟。他的心突然不再晃悠了。他想奔上去,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掏出手机往娟娟的手机上打,听到手机里传来他熟悉的彩铃声后,他看到不远处那个正在走动的女子也掏出了手机。
杜伟亮说,刚才在楼上怎么没有看到你?
娟娟说,什么?
你不是也到了“百合楼”的楼下?
什么“百合楼”的楼下?我还在家里。
杜伟亮正想再问什么,前面的那个女的突然不见了。
以前也有过的,以前娟娟也对他有过这种类似捉迷藏似的举动的。杜伟亮快步往前面的人群走去。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