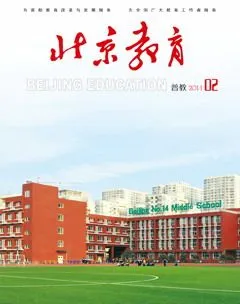在恍惚中清醒
2011-12-29梁晓
北京教育·普教版 2011年2期
德莱姆说:“多少时间是浪费的?没有。多少时间是确定的?零。如何破壳而出?脆弱。”
这是这一周以来唯一在脑子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因为真实,因为共鸣,所以深刻。
开学后工作总是很忙,辗转不同城市和区县,一个最深刻的感触是,一切在流动中。不同的文化带来不同的观念、生活、习惯。于是,某一方面避免了囿于固定的思维模式、教育模式、生活模式,不断有新的东西可以学习,在学习中与旧知碰撞而产生新的火花。这种碰撞有时带着一种新的生成而令人喜悦振奋,而有时又因矛盾、难下定论而带来些许怀疑,在不断的自我肯定和否定中徘徊,有时难免有些焦虑。
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既有具体操作层面,也有思维方法层面。指导有时确实需要细致,良好的行为和习惯的养成,会让他们终身受益。因此,在新的环境里又学到一些新的方法,不免特别高兴。但有时再从反面辩证地去想,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细致地去指导,那是我们成人经过细致思考后的一种严密的逻辑思路,如果对学生的每一个行为都这样以成人的经验去指导并要求,会不会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们思维的扩散性呢? 或者养成一些依赖性而缺少创意性了呢? 这样想的时候,心底又有个声音隐约浮上来: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也暴露了自己对于过于细致的规则的一种潜意识里隐约的反抗呢?
早上教研活动结束后,感受到对学生的一种全方位细致化指导的实效性和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性,很兴奋,觉得收获多多,朋友电话问候,还自我感觉良好地娓娓一番。到了下午,便又有了上述的一些认识。回到家,芸姐打来电话,便告知她想法。她先安慰地肯定我有这样的辩证的想法挺好,并告诉我要超越这些想法,做到无所不包。其实,让我心起波动的不是这些想法,而是在这一个阶段,我被这些都染过了,而自己却还没调出让自己感觉满意的色调。
时间在忙碌中流淌,新生一天天进步而带来的欣慰和成就感令人喜悦,而与之伴随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过于高强度忙碌而带来的自我空间的逼仄,我突然发现从开学到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去静心读点东西。唯一接触文字的时间是早上地铁上和晚上临睡前,而这两个时间段里,文字有时却也仿佛是在镜花水月中漂浮着,因为睡眼惺忪着,脑子便不甚清醒。这样的状态让我不甚喜欢,我问一个同事,你为什么看来会比较轻松?她回我:“因为回到家我就倒下了,最多看会儿电视。”而我,还是希望能再做些其他事。
除却学校里的那个阳光活跃的形象,剩下的时间便有些恍惚了。昨晚家里保险丝烧了,和先生折腾了一两个小时,告诉朋友时却变成了“瓦斯爆掉了”,让朋友虚惊一场,发消息来问:“你没事吧?”自己还纳闷:“这有什么事?”待得弄明白了原委,也挺不好意思。
今晚一个人在家。老父打来电话:“你在干什么呀?”回曰:“发呆。”话说出去,自己先一呆。好熟悉啊!很久以前,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时,也是这样回答,朋友觉得甚是好笑。同样的答案,今昔却是大相径庭,那时的发呆,脑子飘在云端,玫瑰色的绮梦……今天是真正的“呆”,呵呵……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其实和自己一直纠缠不清的不是他人他事,而只是——自己的情绪。情绪这家伙很怪,它有时爱憎分明,喜怒哀乐,非此即彼;有时却暧昧不明,立场极不坚定,让你摸不着头绪,只能一味被牵着鼻子走……很多人对它讳莫如深,有多少人能勇敢承认:“今天我抑郁了。”往往能坦然说出的多半是已经走出情绪低谷的。
脆弱,往往就来自对某种情绪和情感的无可奈何。恍惚中想起了王小妮的一句诗:“偏偏是/那种昂贵的情感/迎面拦截我。偏偏是那种不敢深看的光/一层层降临。”而其进一步的结果是,“我身上严密的缝线都断了。”再深究,那么“什么该和什么缝在一起呢”?
也许,人生真是细想不得的,要想生活得安详一点,就必须模糊、省略很多很多东西。当你因为读到梭罗的句子“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而泪流满面时,别忘了接下来立刻去读一读叶芝的这一句:“她劝我从容相爱,如叶生树梢。”“她劝我从容生活,如草生堤堰。”如此,恍惚的感觉也许就清醒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