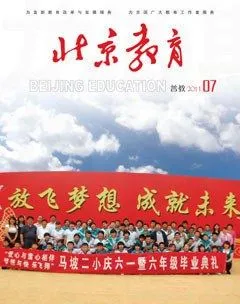安于此岸
2011-12-29周京昱
北京教育·普教版 2011年7期
活到快四十岁,琢磨出一个“真理”:自认为这个东西板上钉钉是你的,到时候准没戏;而很多事,在我看绝无可能,一觉醒来,竟成了。忝为人师,对本人来说,便属后者。从“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理念,到安于此岸、不改其乐的宁静,原先那个意气风发、充满幻想的我已被时间雕塑成今日的现实的我了。
一
刚工作,领学生们爬山。只一条山道,我走在中间,孩子们却遍布丛林各取其道。骂他们不听话,低头一看——只有我被路纠缠着,他们却在半山腰唤我“老师”。
有一段时间,学生们迷上了午饭后广播里的相声,我便因势利导,知识迁移——因为细究起来,相声中每一个“包袱”都是一个修辞格。孩子们却说:“我们没想过修辞格,我们只在乎笑。”我不禁哑然,因为我每听到一个精彩的段子,必分析这一处是比喻,那一处是夸张,这一处是反语,那一处是仿词……我的笑去了哪里?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很多地方比不得孩子,比如求知的欲望,比如视野的广度,比如感觉的清纯,比如面对这个世界所显示出的活力。
二
24岁那年我教高三。据学生后来说,第一次登上讲台时,家长们就企图将我“拿下”,原因是太年轻,没有“套路”,谁舍得用唯一的孩子给你“赌”?然而,当学生们为我笔下那个苍老、腼腆略显窝囊的老师流泪时,他们认识了文学的魅力,也开始钦佩我这位老师。
一位教数学同仁开玩笑说:“数学老师教一道题,学生能做出十道;语文老师教十篇文章,学生连一篇也写不出来,为何?学生上课开小差,你们语文学科总是最多……”这是个难于解释的复杂问题。我想,任何人都一样,当他意识到有些东西自己必须去感受,才可能有亲之近之的渴望。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缺失一种艺术的情怀、一种文化的乡愁以及一种创造的梦想,又如何重新点燃那一对对暗淡的眼眸呢?
素来佩服的是音体美老师,功夫好,若是没有示范的能力,怕是半个学期也混不下去。而语文老师,教不会学生写文章的,多半自己也不会写。认识且敢于承认这一点的,怕是少之又少。
听过一位白发先生的课,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倒叫我终身难忘了。他说:“最近读到一短文,说一中文系高材生反思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深感自己受了蒙蔽——那些条条框框的作文套路,岂不误尽苍生?’我快60岁了,很难说这辈子没“毁”过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当以生活为师。有些同学迫切希望作文能够永远‘一等’,坦率地说,我都写不出一篇人人眼中均够得上‘一等’的文章来,怎么能教你呢?”
潘光旦先生《大学一解》中云:“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意思是说,学校犹如一条河,师生就像一群鱼,大鱼在前面游,小鱼跟着,一起游的时间长了,很多东西自然而然便形成了。在本人有限的教学生涯中,无比珍爱这样一种“从游”的生活,无论是我出题,还是学生们出题,无论写诗、散文,还是写小说、剧本,恐惧作文的岁月我们一起走过。在那个季节里,我就像一个大孩子,与学生们依偎在写作课堂这个糖罐的周围,一口一口地舔舐那罐子里的蜜——那一刻,我们竟然相信,写作可以是一次游戏,可以是一出恋爱,亦可以是一场战争,比成功更重要的,是寻求一种更深层次的快乐、自由与安宁。
三
上个世纪末,我离开校园,以教学研究为业。教研工作的三门功课——听课评课、教研活动、命题及其分析——成了本人工作的主题。
陆机《文赋》中有一段很厚道的话:“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意思是说:批评家对一篇文章评论得头头是道,但真到自己拿起笔来才体会到创作的甘苦;这才明白,懂得如何把文章写好并不难,能写好一篇文章才是最难的。我想,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工作。如同批评家与作家一样,人的鉴赏能力总是大于他的创造能力。判断一节课上得好不好、如何好固然不简单,但真正难的是上好一节课、上好每节课。教研员不是万能的,与一线教师相比,我们也未必绝对的高明,故此,我对被我聆听过的所有老师报以感恩之心。
说来挺有意思,当初不愿到中学教书,怕高考;走上讲台又不愿教毕业班,烦高考——牵着全中国教师鼻子走的,莫过于高考!而眼下,本人干得最欢的也是琢磨高考。
当我站在南方一所县中学的门口,望着诸如“考得上大学穿皮鞋,考不上大学穿草鞋”、“请勿忘——你还是农村户口”等标语时,不禁哑然,且顿生惭愧之心。教育,当使人受益。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还很不发达的国家,教师能够与农民、工人、医生等职业平起平坐的理由,首先在于它能改变人的命运,使人得益于当下,贾宝玉、林黛玉毕竟当不了饭吃。这便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于是,我一面细细品味那部名为《春风化雨》的电影,羡慕那个被称为“我的船长”的基丁老师;一面心安理得地摆弄高考这个东西,作个对世道“有用”的人。
四
对于一个适龄人来说,“生儿育女”是个符号,有其象征意义,它与感恩、尽责、博爱直接相连。它能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变得眼泪汪汪,能使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变得脚踏实地,也能使一个人由崇尚轰轰烈烈、习惯于四海为家变得向往平静与安宁,学会朴素与安分,总之是使“岁月如流”这个宏观的概念变成一天天真实可感地“过日子”。走在街上,冷漠与迟钝了三十年的我,竟会觉得所有背着大书包、戴着厚眼镜、行色匆匆的孩子都是我的一部分。
台湾作家张晓风有一篇文章《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写自己作为一位母亲,站在阳台上目送孩子第一次独自上学时的情景,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想大声地告诉全城市,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们一个小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交错。
……
我不曾迁移户口,我们不要越区就读,我们让孩子读本区的国民小学而不是某些私立明星小学,我努力去信任自己国家的教育当局,而且,是以自己的儿女为赌注来信任的——但是,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
……
这篇小短文,我从学生时代一直读到而立之年。初读时,十六七岁的我坐在教室里,举目四望,试图从学校的一草一木中找到更多的信赖。再读时,二十四五岁的我坐在会场里,听教育专家讲师德,三个多小时的理论终是不敌张晓风的这几百个字。又读时,三十一二岁的我守在儿子的摇篮旁,从新生儿均匀的呼吸中感受着我与他、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种种关联……
作为一个有孩子的人,作为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我时常反躬自省的是:面对普天之下的那些母亲、父亲,我们又怎么敢怠慢!
林语堂有一段话:“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我知道自己正在懵懵懂懂中渐渐老去。我深知自己并非热血青年,相反,对很多轰轰烈烈的事常常抱有怀疑。我亦固执地认为,任何的时代都不缺乏少数的弄潮儿,而这个社会的中坚又常常是辛苦工作、耐得住寂寞的大多数。
一直拒绝承认,眼下从事的工作只是为了一个饭碗,实际上目前我还要以此为生。只想对自己说,惟愿不白吃这碗饭,并且尽可能吃得好一点儿。
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