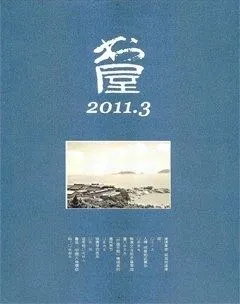尘外孤标
2011-12-29肖跃华
书屋 2011年3期
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戏曲评论家、文学批评家、书法家和诗人吴小如先生温文尔雅,不谙世故,尘外孤标,犹滚滚红尘中岿然挺立之鲁殿灵光。
2008年8月,先生“敬贻”余《莎斋笔记》,扉页挥毫数行:“仆平生读书治学并无谬巧,惟疾虚妄实事求是而已。业余爱好为聆歌与写字,亦重实学而轻浮夸。拙著虽皆零星小文,此意庶可体现。”寥寥数语,其治学为文宗旨一目了然。
先生晚年尝自责一直未能写出全须全尾五脏俱全的整本专题著述,数十年来只是打零星的游击战,写些饾饤小文。然其精通游击战法,每每出手弹无虚发,集小胜为大胜,战果辉煌。
负笈三校——名师亲炙
先生幼承庭训,家传有素,令尊玉如公乃二十世纪著名书法家、诗人,启功先生称之为“三百年来无此大作手”,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及津沽大学中文系。先生先后就读燕京、清华、北大三所顶级大学,其求学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今人难以复制。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当年学生界流传的这句顺口溜,其言外之意是如果物质条件许可,最好上燕京。这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可先生从天津工商学院商科二年级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后,觉得这里洋味太浓、官气太重,读了不到一学期坚决要求退学。教育长林嘉通先生再三挽留,然先生去意已定,真的回天津当教书匠去也。
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先生考入中文系三年级插班生。这时先生已结婚有了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光念书不行,还得搞点“副业”补贴家用。刚好沈从文先生从西南联大返京去看望林宰平先生,适先生在座。林宰老日:“这个年轻人是你的崇拜者,上课不听讲,专看你的小说散文。”另外介绍了先生的学业和家庭情况。那时北平已很紧张,夜晚城门紧闭,进出很不方便。沈先生十分同情:“你生活这么困难,在清华念书哪也不能去,找副业都没有机会,要是转到北大来,城里就有办法想了。”
“吃亏一年就吃亏一年”。先生听从劝告,凑完清华三年级又考入北大三年级插班生。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闻之叹息:“好不容易招了个好学生,可惜转学了。”沈先生十分信任地将《华北日报》文学副刊交给先生经营,先生认真负责,编发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将挂名“沈从文主编”的副刊搞得有声有色。十五岁的邵燕祥彼时进入先生视野并得到提携。先生与国民党的总编拍桌子:“这个副刊到底是你编还是我编?”坚决不肯撤换邵为红军张目的整版小说《沙果林记》,终于照发不误。
转益多师。先生负笈三所名校,先后受业于朱经畲、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废名、游国恩等著名学者,又深得林宰平、章士钊、陈寅恪、梁漱溟、魏建功、顾随等学术大师器重。大学毕业不久,即被当年入学考试阅卷老师、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举荐至中文系任教。院系调整后,先生留在北大,爱讲堂,爱学生,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直干到七旬退休没挪窝。
传道授业——沁入心脾
先生讲文学史,从《诗经》到梁启超皆持之有故;研究诗文,从先秦贯穿于明清近代皆言之成理,“是我们那一代治古典文学的顶尖学者”(邵燕祥语)。《周一良自传》亦有详细记载。
周先生任北大历史系主任,自称任内“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全力促成考古专业独立成系,二是与邓广铭先生合力挽留了吴小如先生。吴小如先生当时已定从北大中文系调往中华书局。我们觉得吴先生博闻强记,讲授中国文学史各段均胜任愉快,堪为青年教员的好老师……我们说服校系两级有关负责人而留住了吴先生。”周论亦证明当年林庚、吴组缃先生联名推荐先生由讲师直升教授为何用“知名海内外”等重语。季镇淮先生指导《近代诗选》编选注解,为何特嘱助手有困难找先生:“吴小如有办法,找他找他,他能解决。”
2007年早春,我慕名走进莎斋。
“贵姓”?
“免贵姓肖,小月肖”。
“你这个肖不读萧,读xiao,四声,首批简化字没有列入,后来约定俗成,萧乾老先生从来不认这个账。”先生见面礼虽未及“数典忘祖”,然而我却手足无措。往后,我又陆续听到先生关于义理、考据、辞章必须兼而有之的论述。“不通训诂章句之学,治辞章就成了空话;而欲明义理,不仅要从考据入手,而且靠辞章表达也很重要”,“不会写文言文和作古体诗,上课给学生讲古涛文是搔不到痒处的”,“如今认得几十个繁体字的人,就算知识分子了”,等等。方知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乃当代文学史领域通才。
先生文字声韵训诂知识精湛,被称为“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朴学守望者”(陈丹晨语)。治文学史“通古今之变”,擅长循“面”到“点”、“点”中有“线”,洞悉源流,论从己出,每一“块”内容都有发言权,由述而不作渐入以述代作佳境,最后水到渠成,形成一家之言。又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生动的吴小如”(彭庆生语)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
先生所著《读书丛札》浓缩了古代文学史精华,先后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人周祖谟、吴组缃、林庚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主张此书凡教中文的老师应该入手一册。《古典诗词丛札》、《古文精读举隅》、《古典小说漫稿》等影响至巨,深获语文教育界的赞誉。先生注释并统稿、定稿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选材精确,注释详尽,解说可信,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鲜见的精品力作,至今仍为美国一些大学古汉语必修教材。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之誉。
“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没有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先生在《古典诗文述略》付梓后,本应再写一篇《宋元明清诗歌述略》和一篇《词曲述略》才算有头有尾。但先生“一直未敢动笔,原因是研究不够”,有些问题拿不出较有把握的看法,“作为‘一家之言’,尚且未必站得住脚”,所以,为了避免误人子弟,先生“只有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留待将来再说”。这成了遗珠之憾。
戏曲评论——凿破鸿濛
余藏有先生论戏曲题跋签名本三册:“两本随笔集和老生流派综说,原收藏在《戏曲文录》中,后来分开重印。我的京剧观点十分保守,不足观也。”
先生“保守”之说,缘于新世纪初接到匿名信,“大肆诅咒我和朱家谮先生是顽固保守分子,京剧‘改革创新’的步伐之所以迈得不大、走得不远,就是我们几个顽固在拖后腿”。然而事实证明,那些甚嚣尘上的妄施斧斤负面影响至巨。
先生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弘扬我国传统戏曲艺术。近百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和《京剧老生流派综说》,是研究中国戏曲的经典著作,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文化著作奖”,被金克木先生称为“绝学”。启功先生称此书“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为,亦不能为”,“真千秋之作”,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同具“凿破鸿濛”之力,“如评诺贝尔奖于文学域中,非兹篇其谁属!”冯其庸先生首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论及开设戏曲评论讲座时反复叮嘱:“一定得请吴小如先生讲讲。”先生自称的这些“竹头木屑”,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颇有读者,有的外国朋友还越洋征求先生意见,将书中某些文章译成外文广为传播。
戏曲为先生主要业余爱好。先生自三四岁开始听唱片,五六岁便随家人外出看戏,十岁左右常常独自或偕弟弟同宾跑戏园子,十三四岁曾模仿小报文风老气横秋写剧评,十五六岁起陆续拜韩慎先、王庾生、安寿颐、王端璞、贯大元、刘曾复、阎景平等先生为师学戏,与奚啸伯、马连良、王金璐、裘盛戎、叶盛兰、童芷苓等著名演员友情甚笃。文革前,先生几乎每周必看京戏,一生看过一千五百多场,玩票学过四五十出戏,亦曾登台演出三场戏,戏码有《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捉放公堂》、《上天台》,先生扮杨波、扮陈宫、扮刘秀,观众席上有张伯驹、华粹深、周铨庵等先生及令尊玉如公。最后一场演出,欧阳中石先生慕名到后台造访,亲自为先生把场,先生与中石相识自此始。
文学批评——立论公允
先生二十三四岁时,立志对新旧文学作品从事介绍与批评。并约法两章:一是言必由衷,只说自己的话,不攀附或盲从任何人;二是力求立论公允,即使受业恩师也不一味揄扬赞美,好就说好,不足就径直指出。
如评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第一,他有极似苏东坡、徐志摩两人充沛的文章气势;第二,他有王安石、龚自珍和培根的老到洗练、挺拔波峭的文采。”至于缺点,“则嫌于西洋文献征引过于繁富,对不懂西文的人来说则近于卖弄,而看过原文的人又难免认为贻笑方家”。
如评老舍先生的《面子问题》:“不过作者在思想批判方面只是含而不露地略事点染,也可以说是‘怨诽而不乱’吧。可惜对人物的描绘太穷形尽相,表现在舞台上怕要使观众肉麻,不能算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罢了。”
如评巴金先生的《还魂草》:“也许这是作者写给少年读的一部作品,一百多页的文字终难免有铺陈敷演之嫌,因而叙述上使人感到有点拖泥带水。虽说用书信体作为小说结构在题材的姿态上比较新颖,但其牵强处仍能一望而知,使人感到些许生硬。”
后来书评环境不那么宽松了,可先生仍固执己见,胡义成先生的《明小品三百篇》出版后,先生发现仅就注释部分而言就有匕八十处硬伤,可一家报纸的图书推荐专栏还赞不绝口。先生四两拨千斤,“举其大端言之,作为当前古籍出版中一个遍体鳞伤的坏书典型”。《一本不值得推荐的书》刊发于《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赢得了读者界、书评界的广泛喝彩。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被金文明先生挑出一百三十余处文史差错。复旦大学资深教授章培恒撰文《恐非正解》,判定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双方唇枪舌剑,各有学者声援,闹得沸沸扬扬。先生如武林大侠亮剑文坛,《榷疑随笔三则》一个一个以正视听,文尾不忘提醒:“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故略陈鄙见如上。”先生短文刚一刊发,报纸、网站争相转载,“吴迷”们欢呼雀跃。
萧乾老误把“美国胜利唱片公司”写成“法国百代公司”,先生去信《北京晚报》,请代转萧老并希望顺手更正。萧老不想文过饰非,郑重其事回信想公开发表来信。先生亲登寓所劝萧老收回成命,结果还是刊出,萧老还在报端特表谢意。不打不相识。从此先生和萧乾老成了忘年之交。先生甫退休,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老就立即绍介先生为馆员,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先生颇似学术警察,眼见硬伤拔笔便战。有人将李白说成是唐朝的“第一古惑仔”,先生曰十分荒唐;周汝昌先生论文中有皇帝“登基”之说,先生认为名家所撰不宜随俗,应改“登基”为“登极”,特致电挚友建议改正;影视作品中念错字、用错典,先生亦发表文章予以指出。2010年中秋,我呈上王闿运、萧穆、吴保初、黎锦熙、罗家伦、萧一山、梁寒操、谢国桢等名家诗稿收藏随笔请先生斧正。先生一句“那我就不客气了”,便逐字逐句审读,挑出七处硬伤,提出三条建议,指出五点注意事项,那关心厚爱全体现在咬文嚼字上。
法书自乐——天真纯净
余藏有先生墨宝十数件,皓首时贤争相跋之。
周退密先生:“小如先生家学渊源,能文善诗,近年始得见其法书,冲灵和醇,神韵两绝,如不食人间烟火气。”
何满子先生:“右吴小如兄手写其自作诗,诗既清新隽逸,字复刚劲秀拔,洵称两美兼具……远非时下浪得浮名者所能比拟。”
“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先生自童稚之年,历八十春秋,潜心揣摩书道,取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来诸家碑帖之菁华一一临之,力求取法乎上。写字不逾矩、不妄作,点画分明,不弃横平竖直循规蹈矩,不以荒诞险怪哗众取宠。故其法书不俗气、不匠气,天真纯净,静如秋水,妍若春花,格调高雅。
“临帖作书,可代体操”。书法为先生乐趣和享受。先生每日临池不辍,却自始至终不参加书法展、不出版书法集(2009年初小孤桐轩主怂恿至再始假宋词而露庐山面目)。曾有企业家、收藏家、门人等再三动员,想包装炒作先生,先生笑而不纳。如效某大师写封信请国家领导人祝贺祝贺,打通电话请师友们吆喝吆喝,乃举手之劳、名利双收的事情,然先生不屑一顾。
先生逃名,其实是为了爱名。他逃的是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书坛里面。故先生法书养在深闺人未识,多在师友、学者、门人之间流传,先生也乐得与同道中人书来诗往、交流感情。
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宝驯的合葬之墓,其碑文由先生所书,此乃古槐书屋主人生前特别关照;启功《联语墨迹》先生欣然担任顾问,手书一序以助其成,因先生与元伯先生乃五十余年故交。茅盾纪念馆落成,先生撰书楹联“一代文章推子夜,毕生心血似春蚕”;张伯驹先生逝世,先生撰书挽联“丛菊遗馨,诗纪红毹真一梦;碧纱笼句,词传彩笔足千秋”;启功先生仙逝,先生撰书挽联“范世称三绝,垂辉映千春”,等等。这些都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联。
我藏有曹锟贿选通令遗稿,意欲先生题签,先生笑而不答。盖上有二老题字钤印,先生羞与哙伍也。先生臧否书坛人物,亦“尖酸刻薄”。论及香港某著名学者,曰“好热衷,好虚名”,只字不提其书法;论及京城某百岁“大师”,曰“此人品德很有问题”,只字不提其书法;北京大学某书法家呈上习作请先生赐教,先生曰“还得好好练”;国家部委某书法家呈上作品请先生点评,先生曰“得从头再来”;某上将辗转托人请先生为其诗集作序,先生仅书“古之大将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又见于今日矣”,只字不论其诗。盖上述所谓书家、诗家追名逐利,作品不入先生法眼耳。
先生惜名,其实是为了守住做人的底线。
某某某大校慕名托我求先生墨宝,并自定内容。先生不日来电,说改了两字,“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变成“千江水映千江月,万里云开万里天”。大校固执己见,先生斩钉截铁:“要写就按我改的写,否则就不写。”大校被逼让步。
笃于故旧——古貌古心
先生笃于故旧,情深意重,淳朴忠厚,古貌古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其他学术研究成果亦受到不公正指责。先生认为学术问题不应有“株连”现象,大胆站出来替恩师鸣不平。文化大革命中俞平老被隔离审查,先生亦打入“牛鬼蛇神”行列受到管制,然先生冒大不韪三进老君堂探望师母,告辞出门时遭小学生扔石块吐唾沫的“警告”而无所畏惧。当得知恩师可能“坐直升飞机”挨斗时,先生立即通风报信,一点也不考虑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王瑶先生“文革”中被“揪”出来“示众”中关园。王有糖尿病,小便极勤,被斗间歇想上厕所,遍尝闭门羹而忍无可忍,唯先生家中厕所随时容王缓解内急。王从一百平方米住宅赶到两间窄屋,唯先生挤出空间供王安放书柜。王曾两次萌发轻生念头,唯先生苦苦劝阻,相濡以沫,温暖着这颗伤痛的心。
周南先生主事新华社香港分社,曾劝记者写文章要讲求文采,提倡读点古典诗词,被人借题发挥,误为开口“训人”。先生深知其“根本没有官气和官架子”,撰文《外交官·诗人·鉴赏家——记老友周南》,发表于香港《文汇报》予以驰援,并赋五古一首以宽其心,其后半云:“古今同一辙,谤议何足伤!天地有正气,浩然盈四方。为君赋小诗,篇终接混茫。”
周一良先生因“梁效”问题陷于“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之际,先生赠《敬善寺石像铭》临本“雪中送炭”;谢蔚明先生辞世,先生撰《文字因缘四十年》深情怀念;王元化先生病中最后几日,先生专程自京赴沪到医院探望;何满子先生金婚纪念日,先生千里赋诗遥祝;经济学家厉以宁文革中受到迫害,先生赋诗予以安慰;门人谢冕甲子遭到诗坛“围剿”,先生赋诗予以宽怀;文革中老友邵燕祥先生所在单位“外调”情况,先生日邵某“过去就是最不像我熟悉的党员样子的一个党员”。戊子大雪前半月,先生嘱我提着还燕祥先生的《陈寅恪文集》、赠燕祥先生的《吴小如讲(孟子)》及人参点心等礼品一同前往探望。先生怕哪天一病不起无法自由外出探亲访友。先生戏言不料成为现实。
耄耋之年——撑门抵户
2008年冬至,我陪先生去清华园拜访何兆武先生。先生对何抱怨:“北京大学平时把我忘了,没有这么一号人,更谈不上什么福利。我老伴病了快三十年,蓝旗营的房子也买不起,根本没人管。但碰到有些事情就想起北大还有这么一号人,这些事只有我能做。”
周培源先生九十岁寿辰,北京大学想写个颂词,“忽然”想起先生和周先生相识,是最合适人选,特派校办主任登门求助。先生撰词:“道德文章,科学之光;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亲自书写在八尺宣纸上,又让人找来大化石篆刻北京大学图章钤印。事后校领导对先生说:“您知道吗,挂在那里一大片东西,就是我们北大的最气派、最显眼、最讨寿星喜欢。”
清华大学成立九十周年,北京大学想送副贺联。撰联条件之一是作者必须跟北大、清华有关系;之二是朱自清、季羡林先生都提到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对联里头得有;之三是北大、清华是兄弟院校,这层关系要写上。先生成为不二人选。“水木清晖,荷馨永播;九旬华诞,棣萼同欢。”先生撰完联后,又将内容掰开搂碎跟校办主任认真讲述了一遍,生怕校领导发言时露了马脚。
先生耄耋之年还撑门抵户、攻坚克难。
恩师严群(严复侄孙)先生文集久难付梓,出版社推说无人校样,先生自告奋勇,耗时三月将二百余万字的《严群文集》一一看过。师兄卞僧慧先生四十五万字的《陈寅恪年谱长编》无人审读,先生主动请缨,秉烛夜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门人之门人谷曙光先生四十五万字的《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乃其晋升副教授之敲门砖,先生连看带校还改,最后期限前三日交卷。2008年冬至2009年春这大半年时间,先生除学雷锋校对这三百万字外,还讲杜诗(《吴小如讲杜诗》出版中)、当“书奴”(应故旧门人强求挥毫),耗费心血,透支体力,先生病矣!
2009年7月,先生突患脑血栓,四肢摔得伤痕累累。余心不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将先生对何先生说的“牢骚怪话”录音整理后寄给北大校长,希望校方从保存国粹出发给资深老教授们一些特殊关心爱护,信件如泥牛入海。先生得知此事后,直言我太冒失。“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先生操守高山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