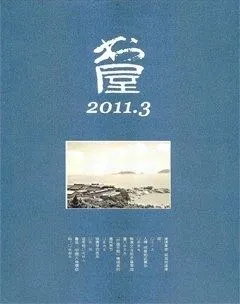鲁迅:中国人有信仰吗?
2011-12-29魏韶华
书屋 2011年3期
国民性批判是鲁迅终其一生坚守的工作重心、他力图以此动摇中国人普遍遵循的共同生存根基:“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叫,施行袭击,令其动摇。”而他对国民性许多精神侧面的批判都与他对国民信仰问题的关注相勾连,与西方的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一样,中国的鲁迅也敏锐地把握到中国国民精神信仰式微的走势。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人是一种信仰的动物,托克维尔断言:“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中国没有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本土宗教。杨庆塑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与西方、近东和印度的宗教不同。”中国宗教的特点是混合宗教,而不是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那样的独立宗教。自晚清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陈独秀、胡适等人均对宗教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之一。人的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上展开。所有的宗教都旨在将个人与社会的心灵提升到精神的境界。宗教的功能在于制衡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求,它对民众的精神提升力是省察一个民族国民性的重要方面。鲁迅在留日时期就对宗教信仰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中,包含有鲁迅对宗教文化的独特理解。关于宗教起源问题,鲁迅认为:“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陁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因陁罗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来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蘖。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在这里,鲁迅把宗教视为人类脱离有限相对的现世而向无限绝对的超世提升的一种努力,因而,他十分重视信仰对国民性格的化育功能。在《破恶声论》中,鲁迅明确指出:“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如果我们将宗教信仰视为“向上之民”的标志,那么,《文化偏至论》中“中国在昔本尚物质”的断语就隐含着鲁迅早期对中国国民缺乏真减信仰的痛惜与批判。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是“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毫无信仰的“浇季士夫”。作为启蒙思想者的鲁迅,一方面高扬科学旗帜,另一方面又反对“举世惟知识之崇”、“不思神閟变化”的倾向,他把借“科学”之名废除宗教者称为“伪士”。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信仰对象都被异化为实利主义者做戏的道具。这是鲁迅对中国信仰史所做的一个历时性扫描: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艺。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代)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现代评论》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
在这里,鲁迅的国民性考察已明显地深入到国民精神信仰层次。
克尔凯郭尔终其一生批判基督教教士和教会的市侩气和虚伪性,其核心思想正是在对所处时代信仰危机的批判中形成的。在他眼中,向工业化阔步迈进的十九世纪是一个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技术在改善着人们生活,也在逐渐物化着人们的心灵。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没有“上帝”的生存是向动物性生存的沉沦,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赋予人的生存以意义感,“信仰是最高级的”。“假如没有一种神圣的契约将人类聚合在一起,世世代代只是像森林中的树叶那样生长,像森林中的飞鸟那样自鸣得意”,那么,“生命该是多么空虚与无味啊!”克尔凯郭尔敏锐地觉察到:信仰已沦为有关信仰的言说,虽然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基督教气氛的浓郁、教会势力的强大,然而这些与真正的信仰相去甚远。
在东方,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普遍存在的信仰虚伪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国民精神信仰问题是鲁迅一生所关注的核心,他倾尽全力批判中国国民性中“无坚信”、“无特操”的人格缺失,这是他自觉不自觉地以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作为参照系而得出的结论。在鲁迅看来,中国人虽各有精神招牌而其实是什么都不信的: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
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与俄国想、说、做一致的“虚无党”——引者加)区别罢。
信仰难吗?克尔凯郭尔说:信仰实际上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信仰以弃绝为前提”。鲁迅发现中国人“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在“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中国人是彻底的实利主义者,“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的时候另外有老聃”。“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莫哈默德”。只要可以利用,“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所有的信仰对象均可变为世俗世界的工具,比如,历来尊孔者莫不“把孔夫子当做砖头用”。鲁迅对于佛教徒的认识也与此同,他“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竞等于零了”。鲁迅像西方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一样宣告长期影响中国人心灵生活的佛教和孔教“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当信仰仅仅变成一种言词和招牌,信仰已不存在,那么,它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鲁迅以此为基点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层拷问。在谈及广州人的迷信时鲁迅说:迷信本身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而中国人由于没有“坚信”,“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做戏”倾向:“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生活本身变得极“富于戏剧性”,许多事情只不过是“做做戏”而已。而这种“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因为“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而“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印度“甘地的把戏”若发生在中国“倘不挑选兴行场(日本语指戏场)就毫无成效了”。在这样的国度,许多事连“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而普遍的“不相信”又成为“‘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如此循环,使实利主义甚嚣尘上,彻底阻断了一个民族向上的精神提升。由此可见,在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由于无信仰导致的做戏、不认真,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项顽症。鲁迅认为,“玩玩笑笑”的态度,正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这把钥匙可以打开“特别的中国”的国民性的深层秘密之门。
在政治生活领域,“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对付的方法有‘蒙蔽”’。甚至连“归隐”一旦挂上招牌也脱不了“换饭”的嫌疑,因为“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正如路德所认为的:信仰一旦用漂亮的言词言说就已远离信仰本身。“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正是由于把从政视为“啖饭之道”,所以中华民国之后就有人“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而且“大都扮演得十分巧妙”。鲁迅感叹道:“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正是由于“无坚信”、“无特操”,“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说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
如果仔细考察鲁迅与许多文化人或文化团体的冲突,其原因也大多由于这些人或团体所体现出的“无坚信”、“无特操”上。在鲁迅看来,中国文人最善于用文字玩弄把戏。他说中国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有些人“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为的是捞些“冠冕堂皇的名目”而已。有些巧猾的“暴发户”甚至以“做作的颓唐”当做…爬上去’的手段”。到处充满了“文章之做戏”,到处是文字的“夸大、装腔、撒谎”。身处文界的鲁迅深切体会到:文人的“做戏”主要体现为多变善变,“革命到时,便是革命文豪”。鲁迅在分析“现代评论派”之变调时指出:“我真疑心他们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并结合佛教信仰的堕落进一步分析道:“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正因为“假知识阶级”毫无信仰,所以才能“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但在鲁迅看来“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在谈到期刊纷出的状况时,鲁迅发现“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与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拼命的挣扎和突变来”。
综观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均集中在对他们“无坚信”、“无特操”品性的批判上。在鲁迅笔下,他们成为国民生存状态的一种符号和象征。他明确批评创造派的某些革命文学家虽然玩着“艺术的武器”,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大相信”的。他们提倡革命文学,也是因为革命文学乃是“时行的文学”。他们的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而是源于一种“无坚信”、“无特操”的人格结构。这种“突变”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其间并“无线索可寻”,只是“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罢了。“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现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毫无正信的机会主义者总是“一面胡说八道,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准备着情势一变,就另换一副面孔;另拿一张旗子,从新来一回”。所以,文学界最大的堕落在于“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的一群‘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知识分子本是社会精神的承担者与传递者,在鲁迅的知识分子批判中隐含着一代先觉者更加深沉的愤懑和悲哀。
信仰意味着精神,信仰的缺失意味着精神的空无。缺乏精神性的“尚物质”倾向是中国国民性的深层底色,因为,信仰不仅关乎宗教,而“是一种根本的行为,我们人类总体的存在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信仰也是我们领悟总体实在的意义的关键”。当代著名神学家巴特更是明确指出:“信仰并非只和一种特殊的范围——宗教——有关,它和实际生活的全部都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早期的中国人“尚物质”观是他一生国民性思考的思想原点。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如果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秘密。如果没有秘密,世界就平淡无奇,人就有两个维度,否则,就没有能力使自己不断提高。”一个民族普遍的信仰缺失必将导致一个民族普遍的向世俗生活的跌落与沉沦。信仰是对纯物质之生活的不满,是一种力图超越“有限相对之现世”,向“无限绝对之至上”升腾的“形上之需求”,它所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向上”之心。,鲁迅虽未从纯学理的角度研究过宗教,但他作为一个独异的思想者从宗教信仰这一维度切人中国国民性思考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理应受到当今学术界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另外,鲁迅也从未明确表达过自己曾信仰过任何一种宗教,但多种宗教情愫的浸润,西方现代个体生存哲学家对宗教信仰“个体化”的思考都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心灵。表现在他生活中的韧性战斗精神、救世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都表现出真正的宗教徒式的崇信;他性格中的认真与诚实、坚定都显示出真正的宗教徒式的力量。在纷然多变的现代中国社会,他是最能够保持思想聚焦性的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内山完造甚至尊他为“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
真正的信仰不在言词之中,而在行动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称得上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信仰义士”,他像亚伯拉罕一样毫不动摇地持有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他像孤独的“过客”一样,拒绝廉价的慰安,弃绝巧滑的劝诫而奋然前行,任凭“夜色跟在他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