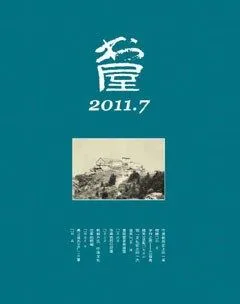一本
2011-12-29王翠
书屋 2011年7期
第一次出版《毛泽东选集》
——1944年
《毛泽东选集》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选集》出现过多种版本,我们现在所常用的《毛泽东选集》是1991年出版的四卷本。第一本《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则是在1944年。
1944年初,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辑《毛泽东选集》,胡锡奎进行指导,并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
《晋察冀日报》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同时报社又是党的出版社。报社领导机关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北的雷堡村。当时,邓拓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胡锡奎任晋察冀分局委员、分局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晋察冀日报》社的工作。
邓拓接到任务后,立即投入《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仅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编辑任务。其实,邓拓自1938年印制《论持久战》,就开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著作。1942年,他向《晋察冀日报》社资料室打招呼,凡是延安和各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及有关研究的文章和书报,都要送他一份。同年7月1日,他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他之所以能很快完成编辑工作,跟他多年努力收集和用功学习毛泽东著作分不开。1944年5月初,邓拓去党校学习,胡锡奎具体主持了后面的工作。其间,《毛泽东选集》的编选计划报告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及中央宣传教育部,并得到了王稼祥的批准。中央宣传教育部对拟收的著作还提过具体意见。
编辑工作完成后,书稿于5月定稿付印,7月出样书,到9月出齐五卷。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纸张十分缺乏、印刷设备陈旧,但印刷厂的同志把出版《毛泽东选集》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力求尽善尽美,保证出书质量。
这部《毛泽东选集》分为五卷,八百多页,约五十万字,共收入著作二十九篇。第一卷包括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著作五篇:《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宪政》、《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附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节选)》。第二卷是侧重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的十一篇:《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与中外记者团谈话》。第三卷是有关军事问题的三篇:《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附录《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四卷是关于经济思想的三篇:《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第五卷是侧重党的建设问题的七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出版了两种版本。一种是用凸版印刷的平装本,按卷分五册装订;另一种是布面烫金字的精装本,是五卷合订本。每卷封面用大号红色字体从右向左题名“毛泽东选集”,下署卷次。在扉页后,用整页的篇幅印制了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下印“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书名页上方署“毛泽东选集”,下方署“晋察冀日报社编”。背面版权上印有: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这里版权页上写的5月出版,实际上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后,6月份报上又发表了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临时补了进去。但版权页未及时做相应的改动,致使有时间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卷首《编者的话》由邓拓撰写,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这是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完全统一起来,使党成为完全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党的一个异常重大的关键”。
这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在根据地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精、平装各二千五百套在两个月时间内就售罄了。
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问世,如1945年苏中出版社版、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版、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增订版及续编本、1948年东北书店版等等。但无疑,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版《毛泽东选集》,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它系统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并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第一个历史决议
——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九十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共通过了两个历史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载入史册,为人们所熟知。而关于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第一个历史决议,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谈到第一个历史决议,就不得不提延安整风。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注意到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党内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党内的“三股歪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较为突出。同时,抗战以来加入党组织的大量新党员、新干部常常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成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滋长的温床,所以有必要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于是,从1942年到1945年4月,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在整风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和经验进行了讨论和总结。1944年3月初,周恩来到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4月和5月,毛泽东分别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中央党校作了《学习问题和时局问题》的报告(即《学习和时局》一文),对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
1944年5月1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着手《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召开前举行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七大的准备问题。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1945年4月20日闭幕,会期长达11个月,其间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在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的过程中,《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也在抓紧进行。
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1944年5月写成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1941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结论草案》)为基础的。《结论草案》是毛泽东于1941年“九月会议”后起草的。由于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在认识上尚未取得共识,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外地主持工作,未能参与历史问题的讨论,主客观条件均不成熟,此事即搁置起来。任弼时的“决议草案稿”与《结论草案》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1941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做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做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篇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1945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做了七次修改,并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也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而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1945年4月20日,举行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任弼时代表全会主席团讲话,指出《历史决议》主要是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这次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朱德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历史决议》又经集体反复讨论修改,直到1945年8月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于8月12日铅印成正式文件。
《历史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于十年内战时期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结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统一了全党思想,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3年王稼祥提出并阐发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是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考察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第一次提出并不是在七大上,而是在七大之前。
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在此之前,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理论界多半都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等提法,没人使用过“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如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2年7月1日,朱德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陈毅在同日发表的文章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创造,指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这篇文章写于延安整风深入发展的时候。1943年6月下旬,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的王稼祥应毛泽东要求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的文章。经过一周左右时间,他就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经送毛泽东阅批后,7月8日在《解放日报》头版位置上发表了。
王稼祥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达胜利前途的保证”。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中和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开始使用这一理论概念。同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一文中,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1943年8月,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同年12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七大之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