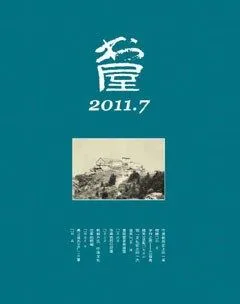代沟与对话
2011-12-29翟大炳
书屋 2011年7期
在我们生活中,“代沟”是真实的存在。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它是指年轻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隔阂形成的对立、冲突。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独辟蹊径地在《文化与承诺》(又译作《代沟》)中,从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出发,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代沟导源于文化传递的差异,她强调了文化进化中的间断性。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是数千年以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也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劳动主要靠人力进行,加之自然环境的险恶,使人们缺乏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人们从未奢望、也根本不可能设想自己的生活能和父辈、祖辈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眼里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前辈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从这里出发,米德阐释了前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微弱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无法改变的。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这样的文化中就构成了前喻文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这种文化的传递方式,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沟产生的可能。诚如房龙在《宽容》中所说:“在无知的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
我们再看并喻文化、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由于先前文化的中断使年轻一代丧失了现成的行为楷模。既然前辈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在并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世界中的成长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种由于老一代不再能够继续引导青年前行而产生的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若想使子女能够尽快适应迁居国的文化,最为基本的途径就是接受迁居国的教育。由于孩子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迁居国的语言,往往可以反过来向父母介绍当地文化,迫使父母去接受子女们所作的有关什么是标准行为的解释。但是,和年轻一代对新的行为方式的接受有一点不同,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须面临先前的行为方式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先前生活的否定,简言之,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这就使老一代不能不和年轻一代产生龃龉抵触。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转入了对后喻文化的剖析。
后喻文化是全书的华彩之章。它也是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米德的后喻文化理论完全奠基于二次大战以来迅猛的社会变迁之上。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确实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谓“信息时代”),那么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少数几个天才人物之一。二次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未来再也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而是今天的发展之果。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新生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林林总总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美国与美国人》就说:“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那么,对于如何解决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米德所给予的解答也更为深刻: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她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他们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米德却申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对话的双方其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他们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真是“石破天惊逗秋雨”啊!对老年人说,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的著名小说《父与子》,它所要表现的就是两代人的冲突的杰作,两代人的冲突就是以思想观点来分界的。小说的中心人物巴扎罗夫是“子辈”,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之对立的巴威尔则是“父辈”,即贵族自由主义的代表。通过他们之间的矛盾,作家肯定了巴扎罗夫作为“新人”的意义,尽管他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小说家与米德的看法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身为大学教授的我,对此也有切肤的体会。在当年的课堂上,你可以侃侃而谈地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当他们走向社会之后,经过历练和不断充电,他们反过来就可以指导你了。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老年人不能沉醉在如“老马识途,人老识理”、“生姜还是老的辣”、“明珠出老蚌”的虚幻的光影中,老年人一定要虚怀若谷地向青年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