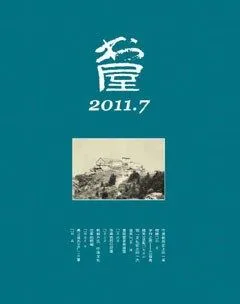“不弃旧诗爱新诗”
2011-12-29胡克庆
书屋 2011年7期
中国素有“诗国”之称,中华民族也是诗的民族。中国文学史是以孔子编纂的《诗经》发端的。近年来,有人认为中国的古代典籍都有诗的元素,并直接称老子的《道德经》为哲学诗。中国人还注重诗教,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故儿童蒙学大都以诗或诗的形式的文字为教材,如《千家诗》、《千字文》、《三字经》等,因此,国人对诗有特殊的敏感,粗通文字,便咏诗作词,以抒情怀。
但以上所说的诗,均指旧体诗即格律诗而言。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诗坛渐渐以白话诗即新诗为主流,成为“一代之文学”。旧体诗渐被冷落,甚至遭受遗弃。但尽管如此,旧体诗如同地火始终未熄灭。不说清末的同光体,还有郑孝胥、陈三立等以及南社的诗词作品。以“五四”运动的主将鲁迅来说,他虽写过不少白话诗,但人们知之不多,而他的旧体诗却广为流传,其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国人经典名句。而毛泽东的旧体诗词更是异军突起,独领风骚,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还有一个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当年白话诗的领军人物郭沫若,以及后来的老诗人臧克家等晚年都改写旧体诗,甚至连当代写政治抒情诗的贺敬之也以所谓“变通”的旧体诗为载体抒发对改革开放的感受。而当年以狂飚突进的姿态跃登诗坛的白话诗却日渐式微,深陷谷底,在各类媒体上很难见到它的倩影。在少儿诗教或朗诵评比会上,几乎都是传统的旧体诗词,偶而才有一两首应景的白话诗。当代诗坛出现这样的景象,难道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吗?
我这样说,并非提倡“告别‘五四’”。“五四”运动是以文字改良起始,从而演变为思想启蒙运动。胡适在他的留学札记中写的这句话足以说明他提倡白话文的初衷:“语言是看得见的东西,一滴墨水像露水滴在思想之上,它使无数人展开思想的翅膀。”正因为这样,“五四”运动不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仅从文化角度而言,散文方面是极为成功,并得到广泛传播。但在白话诗方面却不尽人意,值得进一步探索。
胡适在谈及白话诗时曾这样说:“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他还写过一篇论诗的诗《梅勒庄——白话诗》:“文学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溺’,今天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闹闹。”这也许就是他的诗的观念。但是这首诗作为他的创作实践,与其称其为诗,不如称之为散文更恰当。散文可以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诗是有其特定的规律的。中国古体诗是历代诗人根据中国的语音特点演变而来,是历史沉淀的审美感觉,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对此当时著名白话诗人俞平伯也有疑虑,认为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工具”,对于新诗“大约表示同感的人少,怀疑的人多”(《社会上对新诗的各种心理观》)。闻一多是最早提出新格律诗的设想,他写于1925年的《死水》较早两年写的另一篇《红烛》更具诗的规范,《红烛》诗的前面还题写了李商隐的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说明他由此而引发的感慨。另一个被称之为现代派的诗人戴望舒也从传统旧体诗中寻求新诗的营养,被广为传颂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寞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这不就是南唐中主李王景 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白话版吗?戴望舒还有一首不太为人所知、但却最具传统诗词色彩的《烦忧》(为了便于理解,特作规范排列):
烦忧
戴望舒
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有人问我烦忧的缘故
有人问我烦忧的缘故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
这首诗是旧体诗中特有的表现形式——回文诗。“回文诗,回复读之,皆歌而成文“(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这首诗不仅在表现手法上,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如旧体诗那么凝炼、空灵,具有浓厚的诗的韵味。
除了从传统的旧体诗中追求诗的完美外,还有人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像刘大白的《卖布谣》:“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弟弟裤破,没布补裤……”有的白话诗人甚至借鉴外来的诗的形式,如冯至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冰心的“泰戈尔短句”,这些都说明白话诗有待进一步改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老诗人的更迭,对传统的旧体诗与民歌渐渐疏远,追求白话诗的完善也渐渐淡忘了。在此期间,虽然也出现过富有诗情、诗意、诗境的白话诗,但也很难像旧体诗那样被人们广泛接受和流传。
诗与散文不同,有其一定的规律与规范。在我看来,诗必须具备三元素:形式美、音韵美、思想美。而胡适只强调文字的意义,即思想美并以此作为诗的唯一元素。这是不够的。我们不妨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芬的一首诗为例:
孙用翻译的白话诗:瞿秋白翻译的旧体诗
自由,爱情, 生命诚可贵,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爱情价更高。
为了爱情, 若为自由故,
我可以牺牲生命; 两者皆可抛!
为了自由,
我又将爱情牺牲!
同一内容的诗,孙用的白话诗现得松散、平淡、无力;而瞿译的“变通”旧体诗就显得凝炼、紧凑、有力。瞿的译诗当年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不胫而走。除此以外,还有人从事旧诗的翻译,但人们从中感受的只不过是讲解作用,引用、朗读的仍是原诗原句。如《诗经》首篇“关睢”三章的第一章:
原诗译诗(陈子展译)
关关雎鸠,关关唱和的雎鸠,
在河之洲,正在大河的沙洲,
窈窕淑女,幽闲深居的好闺女,
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
原诗与译诗不妨各读一遍,你顿然会感到,原本一杯浓郁的佳酿变成了寡味淡水。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形式上,音韵上,正是因此而传递了思想内涵。这都说明诗需要形式美、音韵美、思想美,只有“三全其美”的诗,人们才会接受并推崇。
有人总以为旧体诗由于语音的障碍令人难以接受,殊不知历代旧体诗中也有为数可观的诗明白如话。如李白的《静夜思》、《赠汪伦》等,甚至乐府中的《木兰词》等,读起来并不费解,有的是一读即懂,边读边记,终生难忘。其实,当年白话诗人的诗中也有类似“变通”的旧体诗,如鲁迅的一首《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胡适也写过一些“变通”的“五言”、“七言”,甚至在传统旧体诗中少见的“六言”:“偶有几根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自称过河卒子就是由此而来,这说明他们也并非绝然不讲究形式,只是语言更接近口语而已。因此,我以为只有“三全其美”的诗,不止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还能取得“三易”即“易懂、易记、易传”的效果。
只是这一切都要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白话诗不仅要从传统旧体诗中吸取营养,还要从民歌中获得生机,就像有人说的:文学“寻根”是眺望未来。毛泽东在给陈毅一封信中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有志之人当继承古典诗词、民歌甚至白话诗的传统,坚守历史沉淀的审美感觉,创造出有民族特色的新格律诗,包括“变通”的古体诗在内。当然在多元化的社会,也允许那些有诗情、诗意、诗境乃至以散文构建的诗。新格律诗需要形式美、音韵美、思想美,并以此达到“易懂、易记、易传”。法国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纪德说过一句话:“艺术诞生于制约,毁于自由。”值得我们深思。
“不弃旧诗爱新诗”,这就是我期待中的诗坛。但是,旧诗要与日俱进,加强口语入诗,思想更新,如当年黄遵宪、梁启超所提倡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新诗则要继承传统,努力构建结合体,坚守历史沉淀的审美观,形成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诗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