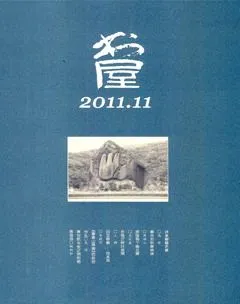书屋絮语
2011-12-29
书屋 2011年11期
在诗意匮乏的当下,发表几篇诗评如何?策划本期《书屋》时,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也这么做了,而且放在了第一个栏目中。这并非不识愁滋味的矫情,而是感到梦想和诗意,当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纳兰性德有诗云:“好梦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诗人的不甘,揭示了人性深处不灭的渴望。
我在《书屋》供职多年,读过无数的妙文佳作。击节赞叹之余,也抱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态度推介给大家。本期“学界新论”栏目,发表了有关梁启超、翁文灏、韩素音、何兆武的四个人物小传,皆滋味醇厚,值得一读。作者周树山、危兆盖、王鹤、肖跃华分别是资深的作家、编辑、记者和军人。
周树山先生的文字老辣而俏皮,正适合描摩“流质易变”的梁启超跌宕起伏的人生。正是,非老辣不足以洞见幽微,非俏皮不足以渲染奇情。在周先生看来,梁启超以簪笔风议之资,而担揽辔澄清之责,有如以孔、孟的禀赋去干苏秦、张仪式的事业,其结果必然是一败涂地,本人也归于心灰意冷。危兆盖先生长期在《光明日报》做编辑,文字严谨而沉郁,无论是表彰地质学家翁文灏的爱国之心,还是总结其科学精神,都言之有据且富含深意。成都才女王鹤的文字则以灵动透逸见长。她把韩素音这位种族、文化上的双重“混血儿”的爱情故事、著述生涯等娓娓道来,让人不胜感慨唏嘘。肖跃华先生为军中才子,尤喜欢和老辈文化人如何满子、吴小如、赵宝煦、何兆武等交往。他写乡贤何兆武,展拓开张之势中蕴含揉磨入细之妙,所引何兆武先生评吴晗、殷海光等人的话语令人大开眼界。
《书屋》的作者,汇聚了知识界的各路精英,虽面孔有新旧,交情有深浅,但大家都是热爱读书的人,而且许多确为文章高手。如本期《书屋》中,余凤高、鲍牧松等先生的文章就做得非常好。
每期《书屋》杂志发出去后,总会收到不少的回应文章,这说明读者读得很细致,很认真,无形中也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本期杂志“编读往来”发表了两篇文章,就“究竟谁是《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的创始者”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我以为发表这些回应文章是很重要的。对于一本杂志来说,有不同的声音是一件好事。至于是非曲直,读者自会在比较中作出评判。
无论哪个编辑,因经历、学养的不同,都会有自己的偏好。但就职业精神而言,有时要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的偏好,这样才能让杂志枝叶丰茂,而免于偏枯。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说,自己四十岁之前,“每见得人家不是”,四十岁以后,“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这不是教人和光同尘,而是说人到中年,傲气已随青春放到青山的那一边。因为饱历世变,阅人多矣,才知晓虚怀容受的好处。
(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