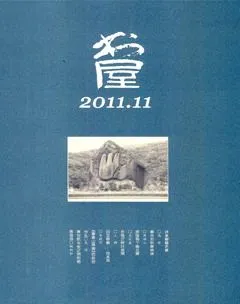寂寥天地间
2011-12-29罗维
书屋 2011年11期
陈渠珍号称民国湘西王,谤誉集于一身,既有人说他是剥削压迫湘西百姓的军阀土匪,也有人认为他是始终为湘西前途操劳的地方长官。在民国湘西这个当时社会矛盾极其复杂,民风骠悍、民气雄强的偏僻地区,无论是达官士绅,还是草根民众;无论是南来北往的乱世军队,还是占山为王的凶匪恶盗;无论是外来却成为主流的汉人,还是本地的却被边缘化的原住民——苗人,对于陈渠珍这个名字无不怀着敬重乃至敬畏之心。
他曾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也做过两袖清风的草民;一生运筹帷幄,戎马生涯,掌握生杀予夺的军权,却也能挥毫泼墨,写出流传千古的美文;他有着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事功之心,却能谨记修身养心的老庄之道;他能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却又狷介刚直绝不谄媚权贵;征战杀伐一生,还曾有和高原藏女的一段动人的塞外奇情。总之金戈铁马和杏花春雨集于一身,倒也符合人们对于绿林豪侠的浪漫想象。
今天的人们有时候并不在意历史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而更乐意以猎奇的目的和简单的思维来看待和打扮历史。比如陈渠珍,出于某种历史的成见,一直被想象成民国湘西的土匪王。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地方博物馆和文史作品将之以大土匪对待;又出于对奇情异恋的浪漫想象,人们总是在陈渠珍的西藏之恋上大做文章。可是一旦真正了解了民国湘西的历史以及陈渠珍复杂曲折的经历后,你便会为陈渠珍被如此草率而肤浅的定义感到无奈和悲凉。好在近年以来,随着凤凰旅游越来越热,随着湘西地域文化的研究深入,沈从文的湘西作品中那个有着游侠者风度的“陈统领”越来越被学者和读者所关注。人们开始希望了解真正的陈渠珍,了解陈渠珍后面那段动荡的民国湘西史。
非常及时地,陈渠珍的后人,他的外孙女田俐、田冰编著的《侠骨儒心:湘西人杰陈渠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田俐我见过一面,乍看之下温婉明秀,交谈一久却可以感觉到她的坚韧和力度,也许正是这种坚韧,使她抱着坚定的想法要让外公的才华、功绩为世人所知,达到为外公“正名”的目的。这几乎已经自觉地成为了她柔弱肩上的使命。有这样的外孙女,想来九泉之下的陈渠珍应该感到欣慰而开怀了。
这本书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陈渠珍西藏历险的自传体小说《艽野尘梦》的白话译文。有人认为《艽野尘梦》完全可与沈从文之成名作《边城》媲美,因他们恰恰同是凤凰人。我以为这不算过誉之词。说起沈从文和陈渠珍的缘分,是沈迷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在他的《从文自传》中有很多地方提到过这位统领官,且评价很高。因为沈从文早期生活有过六年半流浪式的军旅生活,当过竿军里的小兵,后来曾做过巡防军统领官陈渠珍的文字机要秘书,并在1923年离开部队时,得到了陈渠珍的资助。因此他得以比别人更了解这位湘西王,并且更客观真实地评价他。在《学历史的地方》中沈从文说:“这统领官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诩的军人,由于他那份稀奇精力,竿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在《保靖》中也提到到过,“一切都得那个精力弥满的统领官以身作则,擘画一切,调度一切,使个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平时律己之严,驭下之宽,以及处世接物,带兵从政,就大有游侠者风度。”以上说到的统领官就是湘西王陈渠珍。这些评价是带着钦佩和赞美的口气的。这两人同为凤凰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分别以政治和文学的方式共同做过一个重塑“湘西精神”之梦。
但凡看过《艽野尘梦》的人,没有不被陈渠珍在西藏历险猎奇的故事所折服的,更没有不被他与爱姬西原之间相濡以沫的爱情感动乃至落泪的。可以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中国文言文叙事作品之一。如今译成白话文自然更为通俗易懂,尤其是译者是作者的后人,字里行间寄托着对先人的深厚情意,即使中间有不甚客观的地方,也蕴藏着译者的一片苦心。下部为《寥天晓梦》,写的是陈渠珍西藏封将之梦破碎,黯然回到湘西后,另起炉灶,崛起于湘西群豪之间的故事,可划为纪实性文学一类。由于作者是陈渠珍的后人,在叙述中自然会提供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生活细节,这也是这本书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夜阑人静之时,一气翻完全书,眼乏而人不倦,因为心思全被陈渠珍的故事所占据,蓦地,脑海里跳出几个字来——“寂、寥、天、地、间”。陈渠珍熟读经史,尤好老庄,他在湘西主政时,各地住所全部取名为“寥天一庐”。也许只有庄子的逍遥之境才能容纳这位高傲狷介、身负绝世才华而又不得见用,只能在湘西偏远一隅苦心经营的湘西军人政治家。在动荡纷乱的人间世,有梦想有坚持有操守的他注定只能是寂寥的,孤独的。
1882年陈渠珍出生于凤凰一个士绅家庭,父亲曾参加过湘军。他原名陈开琼,是父亲按氏族排行为他取的名。后来自己改名为陈渠珍,字玉鍪。这名字寄寓了陈渠珍对自己处境的不平和期望。“渠珍”就是丢在了水沟里的珍宝,不被世人见用的意思。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就会发光的,虽然生于乱世,日后的陈渠珍却也成为了威名赫赫的人物,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那一笔。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如他的名字的吊诡之处,在湘西层峦叠嶂的束缚之中,他纵然胸存天下却无平定天下的气魄和实力,终其一生,他的命运始终在湘西起伏浮沉,这又是他人生的悲剧。
“玉鍪”之意更为深远。鍪是古代武将的头盔。玉鍪出自《淮南子·汜水》:“古者有鍪而锩领,以王天下者矣。”可见他胸怀之远大。有一次他身边的人向他赞许蒋委员长如何不可一世的权威时,他从鼻子里面哼了一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自身才华无法施展于世的无奈。关于他宁愿受到冷遇也坚决不向蒋介石摇尾乞怜的狷介,在老一辈凤凰人那里也一直是被津津乐道的。他的偶像都是些什么人呢?是曾国藩、王守仁这样的大儒、大军事家。
民国十年的时候,面对南来北往的军阀以及被不断骚扰而痛苦不堪的湘西民众,他喊出了“湘西是湘西人的湘西“的口号,从而让湘西人前所未有地同心协力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他在主政湘西期间大力发展湘西地方的教育和经济,在湘西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国湖南政局风云变幻,主持湘政的督军、主席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斟换。陈渠珍为了不让湘西老百姓受战乱之苦,不让湘西军队成为军阀们争权夺利的筹码,苦苦死守一隅,像母鸡护住小鸡一样守着这块地盘,稍事安定便搞自治、兴教育,实现自己的礼运大同之梦。吊诡的是,为了这一个民生之梦,他又做了不少损害民生的事情,譬如种鸦片,制吗啡,收取苛捐杂税。没有经济来源,他便养不起筸军。
陈渠珍崛起的原因之根本是他的军事才华,其中包括他的剿匪才能。他剿匪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正是引起后人诟病,称其为匪王的缘由。在他看来,土匪也都是湘西人,是被穷困所逼,杀了他们,家里的孤儿寡母也就失去了依靠,故除了十恶不赦、民愤极大的个别小股土匪,他是能收编就收编,不赞成一律剿杀。而招安的土匪武装也成为他军队壮大的重要兵源,且他在土匪出身的这些湘西军人们心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他们只听从这位老师长的号令,这也是人们称他为湘西王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陈渠珍并非招安了便了事,他为了让土匪能改过自新,转而成为真正的军人,摸索出了一条值得后人为政治军时借鉴的路。
他非常重视军人的思想道德问题,认为“祸乱无止,原于良心梏亡”,因此军人要讲良心,而这个“良心”虽为天所赋、人所固有,但究其本原、加以阐发则可以作为军人身心修养的准则。因此陈渠珍虽被称为“湘西土皇帝”,和那些只顾自身利益穷兵黩武的军阀有很大区别。他说:“有良心的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因为军人存心是处处求人民的利益,不顾自己牺牲的。土匪存心是处处求自己利益,不顾别人痛苦的”。即以有无良心作为是否是“匪”的标准,这就给了那些想改过自新的土匪以正名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土匪成为一个有良心的军人时,他也就首先成为了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也就获得了在社会立身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活着”与“存在”之间的巨大区别——这大概是陈渠珍苦心孤诣地写《军人良心论》的真正目的所在。
湘西军人在长此以往的思想教育中渐渐形成了极强的荣誉感。读者都熟悉沈从文的成名作《边城》,在这部以民国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中,翠翠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却不愿与恋人私奔,而宁愿为荣誉和尊严自杀,导致翠翠母亲生下翠翠后也追随他做了一对亡命鸳鸯。这种梁祝似的悲剧并非仅仅是传奇。它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湘西地方军人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尊严感。而这种湘西军人精神的培育也和陈渠珍的军事思想教育有很大关系。
陈渠珍对于湘西地方风气,对于湘西人的精神面貌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正是他治下的筸军——后来的陆军一二八师走出大山,勇靖国难,在抗日救亡的前线,穿着黑衣、包着头巾,拿着土枪土炮和日军作战,打出了有名的嘉善战役,显示了湘西人的不屈和顽强,他们中间有很多就是被收编的土匪。
陈渠珍老于世故,可是从他的一生经历看起来,他也有真性情,有大智慧,他的同仁好友曹典球说:“君智深勇沉,而性情恳挚,卓然有古人之风。”与他同时代的湘人、曾担任驻俄国使馆参赞的陈继训称他是“儒而侠者”,亦并非过誉之词。正如书名一样,陈渠珍是个侠骨儒心的清末民初的士人兼军人。
《侠骨儒心》一书为我们展示了陈渠珍在民国湘西主政期间保境息民、力行自治、发展教育和经济的求索之路,但我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他在军阀混战中保护湘西不受战乱之苦的殚精竭虑,以及在种种政治势力之中捉襟见肘的应付。感受到他内心的苍凉和无奈,悲愤和无助。
陈渠珍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军阀的民国地方官。他以军人的身份梦想在湘西一隅实现乌托邦式的大同梦想,其思想的局限性也颇为明显。例如他和贺龙之间有过交往,贺龙还曾是他的部下。对于贺龙的队伍,他和他的部下能放就放,睁只眼睛闭只眼睛,所谓“剿共不剿贺”,这让贺龙队伍的有生力量能够得到一定的保存。并且据可靠的史实,他有过曾经接济贺龙军队的事迹。可是相比之下,贺龙眼光更为远大,但陈渠珍却只想在乱世中做一方诸侯。这种思想使他与革命道路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