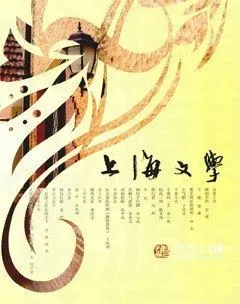恋阙与胡笳
2011-12-29张承志
上海文学 2011年4期
A
一位熟识的日本评论家谈及我的《敬重与惜别》,说了一句出人意外的话。他说:“如果日语中还有‘恋阙’一词的话,张承志对毛泽东的感情就是它。”
我先是吃了一惊。
这“恋阙”一语既用日语讲出,我的思路便被斜拉歪拽,朝着“阙失、残缺”等处寻觅。词义未明,而一股类似憾意的感触,就已经袭来。仿佛自己的潜意识里藏着什么。藏着什么呢?
查了之后才知道,这完全是一个中文借词。从出典到读音,都来自中国古代、尤其唐诗。
——当过考古队员的我,早知道古建筑中的阙,还知道午门其实就是汉代门阙的演变。恋阙,即留恋宫阙,比喻心不忘君,典出杜甫等人。如:“恋阙丹心破,恋阙更忆家。”朝天阙,想皇上,在野的士大夫远向宫阙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遥拜。爱得恋得心破碎、白了头——令人遗憾,只是古典的败笔而已。
我还不清楚这一词汇借入日语后的具体用法,它与“四十七士”似有一线相通。无疑它与天皇制也会搭上关系。突然想起,不少电影都有志士死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镜头——那就是恋阙!
恋阙,虽然出典高贵,不过只是奴才的表达而已。
B
我苦笑,真是说不清了。
显然,同文同种的阅读,仍隔着巨大的障碍。他们居然没有发现——那一股发了霉的忠君情,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复杂感受,并无一丝类似。
韩愈、杜甫等人用这个词,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忠诚。而我却终此一生,也不会向什么朝廷示忠。对毛主席我藏着一份自己的感情,那感情与对革命的观点、以及胸中因革命失败而涌起的遗恨——渗透纠缠。但它从未愚忠,更从不作态,它意味着我更尖锐地直视着他的错误。唯因革命的又一次无功而终,而深深地痛惜与遗憾。
——若说有什么让我依恋,倒是有一对名字的旧事,多少年来一直难忘。
C
那时,我刚刚经历了“荣获”1978年即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眼前洞开着黄金屋颜如玉的青云梦——正是那节骨眼儿的时刻。
君不见,除我之外又有几人——不是从那时起便一步一步异化,四眼如钩瞄准官位金钱,而且装腔艺术、作态诗歌!
而我在那个节骨眼儿上,曾不假思索,只仗着——那时全仗olCABqIAKwQMO5bCOGOmbQ==蒙古草原的养育而择题命笔,所以现在我也用蒙语比喻——仗着“小马的气性”(uro-in iang),拒绝过一次思想的妥协。
唉,jang-tai的天性!可能就从那一天,我开始了不妥协、也必须吞咽下“不妥协”种下的硬皮果子的人生?
故事很简单:
在我的第一篇草原知识青年笔记《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莫名中彩、使得我突然变成了作家以后,我马上兴致勃勃,开始了第二篇。如后来的黑骏马一样,那是一篇题目先行的作品:我不管写好写坏、情节逻辑框架是啥,先咬牙决定,题目一定叫做《刻在心上的名字》。
我要杜撰一个故事。要借助编造的“小说”,塞人我珍视的名字。这个名字乃是蒙语,叫“阿尔丁夫”(Ardin-ha)、意为“人民之子”。但它必须与另一个名字接续,完成一个思想的传承。那个旧名字叫“红卫兵”。在一个蒙古叙事中,哪怕它难译胡语,终于被我把双语言两思想,硬是搅到了一处、画圆了圆圈!
稿子写成、或者说概念之圈被我描出来以后,我以当红获奖作家身份,把它投寄给一份大刊。
大刊编辑不满我这过时的念头,又怜惜我这文学新秀,于是破例费心,亲操牛刀,指示迷津,为我写了近乎一页的大纲。无疑,若我孺子可教,则瓦可充玉,只等我按照一页梗概,“创造”出一篇新的佳作,顺风便可以接着刮。
——大刊虽大,但不足惧。那时的我,浑身羊膻浓烈,豪气傻气贯通,刚从蒙古归来,又正学习哈语。满腹胡笳的浪子回乡,胸中激荡的意气,岂能任人摆弄!
大刊不悦,稿被退下。
他们不知道,“新秀”就是这样炼成的。我自我打分:那是我作家生涯中,第一次宝贵的不妥协。
D
关于大刊到此为止。若不是为了思想的叙述,我毫无兴趣对别人说哪怕一句讽刺话。
我要说的是——在1979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正在痛感、我渴望倾诉的,是革命者与人民的关系、是革命史的前一环与后一步的接续、是我们红卫兵一代正在反省或摸索的一个结论:唯有在人民的大海里我们才能获得重生,唯有人民的利益才是我们忠诚的对象。——这句话像娃娃说的大实话,但多次证明它也相当费解。
稿子辗转良久。
但是即便我不是千里驹、顶多是一匹jang-tai uro(有脾气的小马),我的出世,却处在一个有许多伯乐寻寻觅觅、打着灯笼寻找的时代。
好运气追着我。辗转良久之后,我遇上了当时《青海湖》的主编老赵(已逝的赵希向先生)。显然,他对一个青年作家居然为这么呆傻的一点想法而发愁,大大不以为然。
唯因伯乐来,uro作好马。我的粗糙习作《刻在心上的名字》——关于一个非要找一个和红卫兵意思一样的蒙古名字的知识青年、在草原上走到了迷误与伤害的尽头,终于懂得了“阿尔丁夫/人民之子”含义的思想,被发表了出来。
我自知它并无艺术可言。以往结集时,我总把它和另几个篇什一起划出删掉。除了一次例外,从未把它编入书中。
而这期间,三十年已弹指而逝。
最近的某一天,鬼使神差一般,我把它重读了一遍。
重读之后我不免沉入遐思。当年自己的删除,可能不必要,也可能有好处。那三十年前的往事,恍如隔梦。一阵阵心中涌起的,是对老赵的怀念。
《青海湖》还在,老赵却隐去了。在西宁甚至编辑部,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踪迹。他的淡出离去,一如当年的出现——给我留下了一丝神秘。
在1979年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对当红获奖作家的话语限制,没准有点可供咀嚼的滋味。但于我而言,我命中前定的、对自己坚信的真理的坚持、与对话语限制的突围,从那时就早早开始了。
那一年我三十一岁。每当摊开稿纸,便向草原寻觅。蒙古草原几乎是我唯有的文化资源,也是我自信的依据。
随着古代的终结,恋阙已是一个死语。在我心里它并不存在。一个时代过去以后,我心中唯有一对名字深藏。哪怕心如生锈,但那刻在心上的名字,才刚刚打磨,正呈现它的光亮。
E
别忘了:两个名字,没写出一点艺术。
我还没有原谅那篇生硬喊叫般的小说。它享受了社会的援助,但没有达到艺术。
此刻我想稍稍补救一回。
虽然此刻我拥有的,都五音逆反声若胡笳——与恋阙者分庭抗礼的艺术,会相当异类。
并非是恋阙,且正好相反。包括对那位伟人;堵噎我们胸中的——是注视着革命退潮的痛苦。是对缺残历史的无奈。
对缺残的爱惜,有难言的美感。它藏在人的情感奥深。它是泥巴里、下贱中的一个个外族异类,是一些纯朴姣好的女性,是一些缄默无望的农夫。它也是耗尽了我半生年华的——西吉海原的穷山恶水,伊犁喀什的绚丽风土。它们一件件一处处都并非寄身高阙,而是尽数都在底层!……
每逢此时,胸中便有胡笳奏起——
我猛然想起一首蒙古的短歌。
也许我该说,是我的满腔心事,曲扭周折,换成了一节胡音的哀调。
海忒~阿勒斯~达~~
霍莱~德勒斯~~
谁在我心底埋下了如此一节?它响着,如提醒我——那旧有的惯用武器。我觉得它有一种混血的韵感;虽早已彻底地蒙古化,但又可能起源于坝上汉地。一丝远溯晋北、也没准是东北的味道,说不清地早就消逝了——但唯有它收藏着什么,那是拂之不去的思绪,一种叫做缺憾的东西。
那一瞬只是掠过耳际,便被我死死记住。它从被我听见的那一刻起,就与我纠缠不已,在夜阑之际——逼我为它填词。
居然有这样的旋律!它勾引已经埋葬的旧事,挖掘不合时宜的心思。它如在催促,无论能否,强人所难,要求填入合适的词,回应它渺渺的招魂。
——以下三段,便是我以蒙语写的歌词的、不求其工的随手汉译。
乌洛
变了颜色
没人能认出来
北方
沙窝子上
德勒斯草枯黄
老人
远望着我
不靠近到这儿来
这三段,分别使用了蒙文“白头”的u、h、n头韵。
为了不在推敲中耽误,更考虑到自己毕竟是用汉语写作,这儿只列出了汉语。其实它的每一句,都是用蒙语吟味过,大体觉得通顺之后,才搜寻对应的中文词再把它们填进去的。
至于歌的题名,我本意想写的,是“小马的名字”。但那样不合蒙古民歌的格律。我遵守文化规则以马为主格,题目也自然成了《有名的小马》(Alder-tai uro)。
连文体也是莫名的前定。
只有使用亲爱的蒙语,我才能尽情倾吐——既区别于古代中国文人的恋阙、又把埋藏心中的缺憾、同时还把对历史的感觉,多少表达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