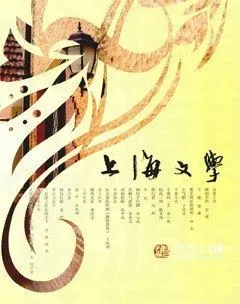文化制约着写作
2011-12-29吴义勤程永新王尧何言宏
上海文学 2011年4期
主持人:何言宏
对话者: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程永新 作家、《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王尧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前几期有幸邀请到了王尧、张清华、张学昕、黄发有和邵燕君等朋友,分别就新世纪文学与中国社会、新世纪文学中的精神问题和新世纪文学的“当代史叙述”等做了讨论。这样的讨论,实际上就是“纸面上的学术会议”,大家各抒己见,互有激发,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本期我们想讨论的是,对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来说,它所处身的文化语境具体如何?这样的语境与我们的文学之间具体又有怎样的关系?其对新世纪文学有着哪些方面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于我们的文学来说,我们是否可以想像或建构一种更加有利于我们文学实践和文学发展的文化语境?
新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
何言宏:新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对于文学的影响与制约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几个月前毕飞宇兄向我提起的,他的一些想法对我很有启发,但他年底因为太忙,参加不了这次对话了,非常遗憾。吴义勤兄的著作《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思》关注的也正好是这个问题,只是他所关注的是整个的新时期文学,具有“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指向,而我们这里所集中讨论的,却只是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及与其相应的文化处境问的关系。说到新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我以为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主流文化与消费文化,对于我们的文学来说,它们都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在此之外,我以为在21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的文化格局中,知识分子文化却处于相对衰弱的地位,难成气候。以主流文化、大众消费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三分天下的方式来把握我们的文化现实,似乎从1990年代以来就已经成了我们的基本思路,21世纪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否仍然有效?吴义勤:关于文化语境与文学的关系,我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思》中有一些简单的涉猎。言宏兄从主流文化、大众消费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三者的关系角度来讨论新世纪的文学,我觉得比我当时对新时期文学的讨论更有意义。因为新时期文学从“文革”时期过来,政治化的文化根深蒂固并非一夜就可消除。因而,“新时期”之“新”其实是很相对的,形态和本质是“旧”的,但我们的愿望和理念可能是“新”的。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状况,涉及到理论和实践层面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新时期之初,其实政治文化、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至少在表现形式上都是高度“合谋”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分野其实是逐步实现的。就拿意识形态话语与纯文学话语的冲突来说,如果没有先锋小说的那种极端化的“形式主义革命”,其实是难以做到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评价先锋小说有时颇为为难的地方。有人可能会说先锋小说以“纯文学”作标榜,但其实在纯文学领域的成就反而有限,倒是其理念和思想的革命更有价值。但随着新时期的展开。各种文化的“合谋”开始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与本质开始显现,这为不同类型文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与根据。尤其是新世纪以后,言宏所说的主流文化、大众消费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三者的发育已经渐趋成熟,彼此的本质和内涵已经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以此来考察其对新世纪文学的影响,我以为是非常有效的。
程永新:言宏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现实“三分天下”的表述很有意思,从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确实有点像“乱世”,文化语境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是显而易见的。进入新世纪,文学发展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具有普遍性,单说制约的话,你说哪朝哪代没有文化的这种制约呢?中国有制约,国外就没有制约?东方有制约,西方就没有?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知识分子人世与出世的矛盾始终贯穿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史。只不过中国社会这几十年的急剧震荡和飞速变化,动摇了我们的习惯思维定势,使我们一下觉得有些无所适从而已。其实今天大陆文化界所经历的困境,正是台湾、香港几十年前所经历过的,也是西方社会一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在我看来,乱世造英雄,急剧震荡的社会也许恰好刺激作家们的灵感,不然,你就无法解释新世纪十年,文学总体处于低迷状态,但我们还是收获了《人面桃花》、《额尔古纳河右岸》、《秦腔》、《春香》、《第四十三页》、《黑白城市的电影》这些文学精品,没有生活的巨变,就不可能产生余华的《兄弟》和莫言的《檀香刑》这样引起争议的作品,不可能产生《月色撩人》、《睡觉》和《陪夜的女人》这些表现边缘人物的另类小说。
王尧:对当下文化形态的三分法,是这几年知识界对当代中国文化状况的基本判断。我的建议,还是用“精英文化”代替“知识分子文化”这一概念。因为,即便是“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在广泛意义上也是“知识分子文化”,讲“精英文化”,就把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区分开来。文化形态的划分,有不同的取向,我们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将文化分为这三种。这三种文化形态,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相互间也错综复杂。所以,当我们说天下三分的文化秩序时,需要一种宏观的思维,将文学置于这样一个大的转型背景之中考察。文化制约着文学,这个命题是成立的,但这个制约,我还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关系,它不是单方面的,如果文学仅仅“被”文化制约,那就会导致“文化决定论”。在充分承认文化制约文学时,同样要看到文学的自主与自由。文学总是会打破制约而实现超越。不仅是文化制约了文学,文学反映文化的含义,同时,文学史也是文化的累积史。如果失去对文化实践的主导和控制力量,文学就会丧失它的创造性可能。就当下文学而言,我认为,文化制约文学的一面是强势的,而文学的自主性则显得弱势,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困境。所以,我想强调这里的制约是一种相互关系。
何言宏:看来,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大家所说的三分天下的局面。不过我以为,对于当下中国文化的认识,恐怕不能仅仅停止于对此格局的三个划分上。某种程度上,我们好像很难、似乎也不太愿意进一步去把握隐藏在这三分天下之下更加具有共同性和本质性的东西。但这个工作肯定要做:另一方面,从1990年代就开始形成的三分天下一直到新世纪以来,变化虽然不大,但肯定还是有的,那么,这些也许不大的变化,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两个问题,我想尝试着作点简单的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想用国际政治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来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三个世界,其实是很不平等的,其中有绝对强势的超级大国。过去是所谓的“美”、“苏”两霸。现在只剩下美国这一单极了,形成了美国竭力要维持、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很想打破的单极化的世界;第二个方面,那就是所谓的第二世界,包括像英国、法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它们对超级大国是仰人鼻息,唯马首是瞻,很多时候还互相利用,蝇营狗苟,另一方面,对于第三世界,它们有的是挤压和掠夺;剩下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的处境不说也知道,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还是在国际活动中的话语权,都是非常有限的。它们唯一的优势,可能只是处于金字塔的底端,“人多势众”罢了。以此来反观一下我们的文化格局,不知道是否会有启发?不过有一点我想指出的,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文化,或者说是王尧兄所说的精英文化,恐怕连第三世界的“人多势众”都谈不上了,因为在数量上,他们无疑少数派。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变化。我想这方面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主流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了。现在是主流文化财大气粗,消费文化见利忘义,二者的结合越来越自觉,越来越紧密,知识分子文化的空间不仅越来越小,而且被前面两种文化分别或联合招安的也越来越多。我曾经和一位朋友说,实际上,这就是发生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背叛或文化背叛,这样的说法可能太过激愤了。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我们的文学一方面以这样的文化格局作为背景,同时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下文学的问题,应还是有意义的。
新世纪文学的文化制约
何言宏:在新时期文学之初的“寻根”时期,阿城有一篇名文叫做《文化制约着人类》,实际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很明显地受到文化的制约,只是我们不想像“寻根”作家那样纵向地从深远的文化历史源头中去探寻制约我们的文化因素,而是着重于文化现实,反思一下新世纪中国的文化现实对于文学的多方面制约,当然除了消极的制约,积极的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具体的探寻方法上,我们既可以从文学着手,探寻一下在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甚至具体的作家作品中现实文化的制约因素;也可以从文化出发,寻绎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文学的多方面制约。这里,我想先从文化出发,反思一下新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化、消费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从主流文化的方面来看。义勤兄在他的书中说过,“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强制性到90年代已基本消失了”,它“代之而起的对于‘主旋律’的提倡实际上只能对文学发生一种感召或诱导的作用,文学的自由度是空前地扩张了”。这种由“强制”到“诱导”的变化在新世纪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我曾经以“抓评奖,促生产”这样的说法来具体概括199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所推行的文化战略,实际上就是吴兄所说的“诱导”。当然除了评奖,其他一些“感召”或“诱导”方式也很经常地被使用,这除了表现在一些“主旋律”作品中,还很突出地表现在新世纪以来被称为“底层写作”的文学潮流中。至于消费文化对文学的制约,最为突出的,就是它对“80后”写作的影响,另外还有其中的影视文化对很多写作的“诱导”,影响也非常之大。可以说在新世纪以来,不同方面的文化力量非常有力地介入了文学场域,不仅引发了文学场域的复杂变化,也使很多具体的写作变得很复杂,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地去辨析与评价。
吴义勤: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境遇已经是渐趋自由了,到了新世纪以后这种自由度还在增强。但问题在于,在一个“自由”的文学语境里,文学却似乎反而失去了力量。“自由”了,文学不是应该越来越“纯”吗?不是应该越来越先锋吗?为什么纯文学、先锋文学反而死亡了?“自由”了,文学不是可以真正远离我们曾经那么厌恶的“意识形态话语”了吗?何以主旋律文学却如此有市场?我们当然可以从主流文化的战略改变以及商业文化的巨大力量等层面去解释这些问题,但我们更应该从中国作家主体性的层面去作深刻的检讨。过去,中国作家常常会把各种文学的问题归结到外在的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却忘了反思自己是否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文学自我”。说实在的,主体没有足够的艺术能力、思想能力,再“自由”的环境也没有意义。
王尧:尽管我们在1980年代,我们在对现代化的想像中,预期过1990年代以后的前景。但实际上,当1990年代到来以后,我们便发现,现实的状况并不是我们预期的那种。这不是说我们以前如何幼稚,而是说我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在我们原先的各种思想和方案中,没有现成解决1990年代特别新世纪以来的思想和方案。所以,我们觉得1990年代以后各种秩序都乱了,这是我们停留在1980年代形成的感觉。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必然性来看,文化的三分天下是必然的。从原先的政治与文学关系来说,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确实减弱了,而更多地是通过主流文化来引导,或者通过主旋律文学反映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但是,我们说的这种控制力的减弱,并不只是因为重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与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形成有很大关系。精英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都削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也是“市场”带来的一个结果。确实,如义勤兄所说的,主旋律在市场也有不小的影响,而这证明了文化形态之间、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同样,在对“纯文学”、“文学性”等问题的反思之中,也包含了重建文学与世界关系的努力。“纯文学”作家中的不少人,在剧烈批判市场时,其实也看重自己作品的市场,这自然包含了传播自己作品的崇高愿望,但也有市场利益的企图,无疑,这种利益企图是合理的。这种种现象都表明,新世纪以来,文化对文学的制约是在各种文化形态背后的价值观念冲突、妥协甚至也不无“合谋”的过程中完成的。我们已经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语境来讨论问题。
程永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某些方面呈现后现代的特征,进入新世纪,又增加了后结构的元素。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强制性影响减弱了,文学的自由度表面上看大幅度伸展了,实质是被边缘化了。过去把你关在笼子里,你发出的鸣叫满屋子都能听到;现在将你放飞茫茫大海,你的微弱声音对世界已毫无意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不能说消失,在这方面,写作者和办刊物的,还有出版社最有发言权。要深入分析文化语境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是一项十分困难、复杂的工程。这里我想说说最近热映的姜文电影《让子弹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子弹飞》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部电影在艺术上的认同和评价:姜文通过这部电影,已确立中国大陆第一大导演的地位。整部电影的语言是后现代加后结构的,同样是搞笑甚至是搞怪。它的艺术品相远高于周星驰电影几个等级。大的方向完全正确,所有大的方面都值得激赏。多少年来,小说家在影视编导前不乏一种自尊,影视也确实向文学汲取了丰富的养料(这部电影的灵感本身也来自于小说),但我想说,子弹飞来了,击中了我们的尊严和自傲,所有爱文学的人都应该放下身段去向子弹学习,端正态度,潜心研究,深刻领会。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与阿莫多瓦、伍迪·艾伦相比,看完《让子弹飞》又有些许的不满足,多么希望子弹也能把那些像大山般横亘在中国导演面前的大师们击倒。姜文的艺术才华毫不逊色。已具备这样的实力,那么这些许的不满足,又来自于何处呢?我曾在一帮大学年轻教授(他们都是子弹壳)面前表达过类似意思,不料同济教授郭春林从饭桌那头跑来拽住我,执拗地要和我谈论商榷。当时人多嘴杂,三言两语又无法廓清思路,我们没有深入交流,于今想来,这不满足就可以归之于文化制约。
我们知道,阿莫多瓦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也非常擅长表现血腥和暴力,但我经常回味的却是他电影中一个温宛而大胆的场景。那是《我的神秘之花》中的一个细节,深夜的街道,《国家报》编辑奥加送已对生活丧失信心的情爱小说家莉奥回家,突然,奥加往前跑几步回转身,由远至近由轻至响回荡起弗拉明戈的音乐,于是。两个人在午夜的街道上翩翩起舞。看到这地方,我被震撼了。让我震惊的不是西方人的浪漫,而是阿莫多瓦在艺术领域达到了一种至境——随心所欲。莉奥因为丈夫的背叛灰心丧气,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而奥加的抚慰和体贴给了她精神上的新生,所以,那无来由的渐渐巨大的音乐是从她内心生发出来的,这一场景具有假想性和幻想性,但因为与内心有关和相通,随即拥有了情感深度,拥有了抒情性。《让子弹飞》里表现了两个女性,她们很像是整部影片的摆设和点缀,谈不上情感深度,影片因此丧失表现艺术弹性和张力的机会。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是姜文对后现代电影语汇的独创性贡献,它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被命名为“延宕”。遗憾的是子弹只有速度的变化,而没有弹道线路的发散性变化。我知道凭姜文、述平他们的能力,丰富与女人有关的戏不是什么问题,增加抒情性也不难,但与我们粗糙杂乱的文化语境相一致,在飞速驰骋的时代列车上,也许根本顾不上去表现温情和诗意,致使整部影片只在一个艺术层面上粗砺地运行。另外我想说,仿真、超现实、幻想性的电影语言,必须借助现实的扶手,一如马尔克斯让傻姑娘坐着毯子飞上天需要寻找生活的依据。电影中给老百姓发银元发枪支的重要环节,缺少令人信服的内在逻辑,也过度动漫化戏谑化。
即便如此,《让子弹飞》仍然是一部足以让文学界汗颜的大作品,它符合这个时代对幻想性作品的需求和审美理想。
何言宏:说到电影《让子弹飞》,倒是又一次显示了影视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大家知道,这部电影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马识途先生是一位很让人尊重的老作家,也是一位革命老干部,前不久读到他关于自己“文革”亲历的回忆录《沧桑十年》,非常震撼,我认为其价值绝对不亚于很受关注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和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等作品。但是说实话,要是没有姜文的《让子弹飞》,即使是很多“业内人士”,差不多都已经忘掉了这位老作家,更不用说是社会大众,恐怕都是闻所未闻。但这部电影,却一下子改变了这样的状况,极大地扩大了马识途及《夜谭十记》的影响,到处都可见到这部重印的小说。新时期以来,电影和电视的改编对有些作家作品影响力的扩大甚至经典化的促成起到了非常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在莫言、苏童、余华和池莉等作家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影视文化对文学作品影响力十分巨大的“放大”作用,加之以改编所可能带来的经济报酬,这些年来,“触电”的作家越来越多,有些作家甚至在作品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叙述方d9e137b997799756610deb12f7d83448式或画面感的营造方面,程度不同地照顾到或者是有意迎合影视改编的需要和可能,这对作品的文学性肯定是有损伤的,对此,其实已经有学者做过专门性的研究。影视文化之外。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其他一些方面的文化因素,可能更需要我们的注意。
文化建构与文学的可能
何言宏:新世纪文学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文学刚好经历了一个相对独立和相对完整的阶段,十年只是一段完整的自然时间而已,不过,我们似乎仍然应该想像一下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文学的可能,在我们的具体论域中,实际上就是想从文化的方面来想像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建构和营造一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文学实践和文学发展的文化语境?就我个人的关切来说,我所希望营造与建构的文化语境,一方面要有非常自由和非常活跃与蓬勃的文化生态,另一方面,针对当下中国的文化格局与文化生态,还是应该进一步拓展知识分子的文化空间,呼唤那些具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写作。
吴义勤:就文化生态来说,我当然同意言宏关于“非常自由和非常活跃与蓬勃的文化生态”的设想。对我们来说,我们呼唤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环境、再好的生态都是合理的。问题是“生态”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自我”之外的客观的“无我”的存在,它必须是有“我”的、与“我”密不可分的一种价值性的存在,必须有“我”的奋斗、思想与艺术的探索。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任何时代既有伟大的文学与伟大的作家也有大量庸才和庸作这一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似乎更应该关心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问题。只有当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强大到真正“物我两忘”,真正凭内在的力量完全超越外在环境,而外在的环境对作家的内心也丝毫无法撼动之时,中国文学才会有大的希望。
程永新:面对“三分天下”的局面,面对网络和新媒体的冲击,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走出谷底,文化语境和文化生态恐怕也不是随意可以改变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悲观的理由。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说文学的整合:比如说鼓励作家多多贡献像《让子弹飞》这样带幻想性元素的作品;比如说提倡一种与当下新八股文截然不同的新批评文体;比如说净化汉语言。不要出了一个“给力”,满世界全是“给力”;但这里,我最想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修行。
过去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钙,现在我觉得还缺很多其他微量元素,比如铁啊锌啊等等,我还想说:中国知识分子毛病比较多。最近史铁生离我们而去,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铁生最让我尊敬的是,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在他那儿完全是融为一体的,他活着他感悟,感悟到的变成文字,那就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里有宗教,有哲学。他只有一副面孔,不像我们,常常会有人格的分裂,常常会有两副面孔甚至几副面孔。
记得新世纪初,铁生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务虚笔记》,他希望在《收获》上发表,时任《大家》主编的李巍听说后,一次次打电话给铁生,希望他改变主意把稿子给他们,并承诺把当年的十万元《大家》年度奖给铁生。李巍为此专门飞到上海,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放弃铁生的稿子。我当时的感觉李巍实在是喜欢铁生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片赤诚,十万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我们知道身陷轮椅的铁生经常要做透析,非常需要钱,但我们又怎么能把“放弃”两字说出口呢?经过一次次的沟通,铁生还是不为所动,坚持要让他的第一部长篇通过《收获》面世。我想,没有等到铁生稿子的李巍,除了遗憾,还有满满当当的敬意留存心间。
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说出来也许得罪人,我觉得中国可以而且应该有优秀的农民作家,但我们的作家不应该全像旧时代的农民。说起来有一个很好听的称呼:“灵魂工程师”,但骨子里的意识非常陈旧,行为方式像守着一亩三分地、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村夫。福克纳自称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农民,但他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却充满了艺术气质。如果要问我中国作家最缺什么?中国作家最缺的绝对不是钱,而是——艺术家的气质。
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知识分子理应有担当,理应对公共事务发出正当的声音。价值标准的重估和定位,也是当下中国文化现实迫切要做的一件事。什么是抄袭,什么是剽窃,要有明晰的界定,要有文化的法。不然,公说婆说各说各的,使用的价值标准不同,很容易变成马拉松式的官司,永远没有尽头。我们的文化人,也不要只有在骂街的时候,才显现个性和魅力。摆事实讲道理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哪怕是尖锐的意见,我们都是认同的,但专门通过糟践别人来扬名天下,说严重一点,有文化恐怖主义之嫌。此风不可长。鲁迅先生也打碎很多东西,但他同时又建立起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知识界的一些人,虽然常常把鲁迅挂在嘴边,却没有真正学到鲁迅的精髓,搞爆破是高手,搞建设像侏儒。
王尧:对当下文化生态的评价,我很谨慎地使用“自由”这样的措辞。比起曾经有过的历史,当下要自由得多。那是相对于政治对人的控制而言。1980年代的一大遗产,就是承认个人,承认主体,为什么在新世纪我们又会感觉到个人消失了,主体瓦解了?这说明,限制自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当年是有一套相对完备的知识话语来支撑个人、主体、自由等观念的,并且因此把“人”解放出来了。现在文化三分天下的形态,能否合成一个我们所期待的自由、生长的文化生态,也取决于文化内部冲突的结果。我觉得其中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形成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不能,知识分子就不能恢复历史论述的主体位置。所以,知识分子的“内在资源”状态和品质如何,影响着文学的未来,也影响着文化累积的进程和品质。
何言宏:看来诸位所重点关注的,还是作家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本来我以为各位可能会对文化语境的重新建构多提一些意见或设想,但是在具体讨论中,侧重点却发生了偏移,这真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不过这对我很有触动,也很有启发。起初我看到义勤兄在谈到文化语境时很快就转向对作家自身问题的思考,就激灵了一下,后来看到大家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也便多做了点思考。我以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目前文化语境中的种种问题。比如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诱导与文化规约、消费文化的利益诱惑,我们都不用讳言,当然也有值得改进的必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我们的文化宿命,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作家实际上都有着被文化制约的问题,谁都无法彻底地摆脱它。所以我们务实的选择,可能在尽力改善文化环境的同时,更应该加强作家自身的持守。我们都应该承认,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即使是在黑暗和专制的时代,一样会出现伟大的作家,远的不说,就说在前苏联时期,他们出现了那么多杰出的诗人与作家,这也是人们时常用来批评我们中国作家的一个比照。这样一想,我们就能认识到,虽然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学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且正如王尧兄所说的,二者之间,文学似乎更处于弱势。但我们的作家一方面要认识到自己的创作同样也是一种文化实践,它与文化语境间的张力与冲突,或者是媾和,本身就有文化意义的,因此文化环境的改善也依靠文学自身的努力,我们不能总是指望靠以往那样的文化革命来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的作家对自己所不太认同的文化,就应该拒绝,而不应该同流合污。我很认同义勤兄所说的,只有当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能够强大到真正“物我两忘”,真正凭内在的力量完全超越外在环境,而外在的环境对作家的内心也丝毫无法撼动之时,中国文学才会有大的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