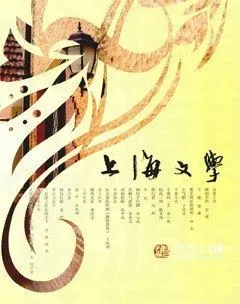编辑室的“老右”
2011-12-29周良国
上海文学 2011年4期
我1960年初调至《北大荒文艺》编辑室时,发现有两位年岁较大的长者,原来是文化部下放至北大荒的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文化名人:聂绀弩和丁聪。
聂绀弩当时已六十岁上下了,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我很早就读过他的杂文,觉得其文笔的犀利,堪比鲁迅,是我崇敬的老作家。凭我的资历和年龄做他的学生都不配,想不到竟在一处共事,所以我对老聂是十分敬畏的。
聂绀弩有着非常传奇的革命经历,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南洋办过报纸,留学前苏联时,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人是同学。回国后,从事文化工作,与鲁迅、胡风等文化名人过往甚密。抗战时,担任新四军文委会秘书,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和稀有的文化专家。1955年,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被解除领导职务,留党察看,“反右”斗争时又被“升级”为“右派”,被开除党籍,于1958年发落至北大荒劳动改造。
聂绀弩在北大荒的经历也颇“精彩”。那年冬天,他以六十高龄的老迈身体,被派往完达山参加伐木战斗,干着“归楞”的劳动,即将伐下的木材用手撬肩杠的原始方式集堆,等待拖拉机爬犁运出山去。这种超强劳动,使得老聂佝偻着腰,两腿直晃,这就影响了集体作业,使同时抬着一根巨木的十几个人无法随着号子齐步行进。这是非常危险的。领导就指派老聂留守宿舍,给大家烧火坑取暖。
聂绀弩善提笔杆子,却不会拨弄烧火棍,竟然把房子烧着了,被认为是“阶级敌人”故意纵火,蓄意破坏,把他抓进公安局法办,被虎林法院判了一年徒刑,关进了监狱。他妻子周颖在北京得知消息,忙赶来虎林,就住宿在文人聚集的《北大荒文艺》编辑室内。
周颖在“反右”时,也成了“右派”,因她是中央民革的发起人之一,仍保留政协委员的头衔。为统战需要,法院对聂绀弩的“纵火”事件进行复查,将他放出监狱,并征询周颖的意见:你看怎么安排?周颖说,我住宿的单位不错,于是老聂就成了编辑室的一员,
聂绀弩是个高大精瘦的人,脸上布满饱经沧桑的皱纹,在编辑室做着来稿初阅和分发的工作。他初见我时,问:“你是x××吧?”原来他所问的那个人,是某农场一个青年作者,曾有一部长篇小说投寄《北大荒文艺》,老聂看后觉得不错,因此留下深刻印象,把我误认为此人了。其实,那时候垦区的文学青年很多,我只是机缘巧合被调入了编辑室,比我文学基础好的、功力强的大有人在。我对老聂说:“我是从859农场来的。”老聂鼓励说:“那是个紧靠乌苏里江的好地方,希望你能写出好作品来。”
聂绀弩睡在小说组靠门的一张木床上,保持着老年人的慢动作,无论生活起居或是说话举止都要比我们年轻人慢半拍,参加劳动更嫌迟钝。一次,丁聪在现场替老聂画了一幅速写。老聂见了不禁大笑,当即写了一首《丁聪画老聂上工图》:
驼背猫腰短短衣,鬓边毛发雪争飞。
身长丈二吉诃德,骨瘦瘪三南郭綦。
小伙轩然齐跃进,老夫耄矣啥能为。
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
(诗中的南郭綦是《庄子》中的一个人物,其人形同槁木。)
尽管这样,可谁也没有嫌他,而参加集体劳动,动作慢了就会影响单位形象。遇到这种情况,单位负责人虞伯贤总要在他身旁不断鼓劲。后来,干脆留他看家值班,免除他参加劳动。
一次,我们劳动回来,看到聂绀弩一个人在写着思想汇报。我好奇地凑上去观看,见稿纸上赫然写着:“我是名共产党员……”我觉得十分惊讶,他不是被开除党籍了吗?再一想我明白了,他虽然在组织上被开除出党,在思想上,他始终认为自己仍是名党员。理想和信念仍在坚持,这不由引起我对他深深的崇敬。
聂绀弩处事非常低调,很少与人交谈,空闲时只是与符宗涛、王忠瑜两人下围棋“手谈”。他赢不骄,输不急,不像符宗涛输棋时脸红脖子粗的,也不像王忠瑜争执时拂袖而去。真是修炼到家了!
那一年,由崔嵬领衔在垦区拍摄电影《东方红》。我在街上经常看见崔嵬戴着假胡子,穿着戏装与剧中演员说戏。崔嵬与聂绀弩是老朋友,又都是党内知名的文化人,崔嵬来垦区很想会会聂绀弩。
崔嵬是通过剧中的女演员秦文来邀请的。秦文是著名演员秦怡的妹妹,因在电影《青春之歌》中扮演角色而走红。当时她只有三十多岁,那天她穿了一件格子衬衫和一条蓝色工装裤(可能是戏装吧)来到编辑室,老聂却避而不见。我想,这大概是他感到心理落差的缘故吧。
这年冬天,文化部把下放在北大荒的文化名人召回北京,分配工作。聂绀弩就此离开了编辑室,以后我在报章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作品,也看到有关他的报道和评论,知道他返京后又历经磨难,发生了许多“故事”。
丁聪是画家,原是《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反右”时落马,发配至北大荒,在《北大荒文艺》担负装帧工作,并以“学普”和“阿农”的笔名为刊物画插图。因其绘画风格独特,一看便知是丁聪的作品。
丁聪与符宗涛、林青同住在散文组的一个统铺上,我调入编辑室后,就挤睡在丁聪身旁。因为挤得难以翻身,符宗涛和林青分别在他们的办公桌后边各搭了一个小铺,丁聪和我就用统铺的材料靠门也各搭了一个小铺,两人相对而卧,成为最接近的人。
因同睡一处,又都是上海人,交流比较方便,话题就多了起来。主要是他讲我听,断断续续,归纳起来有如下内容。
丁聪告诉我,旧时中国文化界有四大神童,分别是万家宝(曹禺)、吴祖光、丁聪和黄苗子,在二十多岁时就以文名享誉全国。现在除了曹禺外,其他三人都成了“右派”,都发配到了北大荒。丁聪与我朝夕相处:吴祖光在局文工团工作,都在大食堂吃饭,我曾见过;黄苗子(画家郁风的丈夫,名作家郁达夫的侄婿)我未曾交往。想到他们的遭遇,我不胜感慨。
丁聪还说,他们这些人所以沦为“右派”,与抗战时的“二流堂”旧事有关。那时在重庆,一些青年文人经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以文抗日之事。一次郭沫若也来与会,开玩笑说:“你们这帮二流子,又在干什么?”自此,这帮年轻文人,干脆把聚会场所称作为“二流堂”。不想“反右”时,“二流堂”被定为“反党宗派团体”,于是丁聪等“二流子”就厄运难逃了。
丁聪还谈到建国后美术界的趣闻。那时齐白石年事已高,他原配夫人和续弦的几位夫人都先后去世。不想齐白石以九十高龄还要续弦,而且在住院时看中了一个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女护士。美协领导认为不妥,丁聪就与华君武等美协领导轮流到医院陪伴齐老,与他说天谈地,分散老人的注意力,终于使齐白石打消了续弦的念头。我听了,认为美协此举有干涉婚姻自由之嫌,但当时的年代就是如此,从爱护老人,避免家庭矛盾角度出发,丁聪等人也是有着良苦用心的。
徐悲鸿则是个潜心艺术的大画家。他对政治和各项运动似乎不甚关心,他说过能震撼他心灵的只有三样东西:原子弹、地震、模特。我听了感到,原子弹虽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徐悲鸿未必对政治不关心,而是对大的方面关心,他更多的关切是艺术方面的,无怪乎他会成为享誉世界的大画家。
丁聪给我看过一幅在垦区劳动时的画作,题名《大礼拜》。当时垦区并不每星期休息一天,而是实行大礼拜制度。即每十天休息一次。因为劳动紧张,往往要几个月才会休息一次。他画的是,在某个大礼拜日,职工们在马架内下棋、看书报、洗衣服、聊天、拉琴,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个个神态逼真、生动,显示出北大荒生活的一个侧面。我看后觉得他过分美化当时的生活了,因为我在生产队时,碰到难得一次的大礼拜,连洗衣被、捉虱子都来不及,那有空闲看书报、下棋和拉琴。但我想各地情况也有不同,况且,即使丁聪美化生活。也正说明他对生活充满着信心。
丁聪当时四十四岁,正当盛年,又是矮矮墩墩的个头,参加劳动不输我们年轻人。他生活比较随意,可是总觉得钱不够花。他原是文艺四级,降级后月工资仍有一百四十元,但文化部将一百元发至他家中,仅给他四十元生活费。按说当时在北大荒,伙食费每月不足十元,四十元钱应该很充裕了。可是他要买书,还要吃些高价食品,就显得拮据了,所以他常常要问我借钱。我当时的月工资是六十多元,不嗜烟酒,除了每月寄给上大学的大妹十五元生活费外,还有余款调剂。丁聪基本上只向我一人借款,而且月中借,月底还。第二个月再借,再还,每次都是二十元为限,周而复始。直到年底,他还我款后,不再借了,因为他也调回北京了。
丁聪有一双红色的高筒胶皮靴,下水劳动很得其利。我是生产队出来的人,对这种高筒胶靴情有独钟,因为北大荒多低洼地,生活、劳动都离不开此物,简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父亲好不容易在上海为我购到的一双短胶靴早已坏了,所以我很眼热丁聪的这双靴子。我认为他回到北京大城市,已无需这种装备,很想用他最后一个月的借款来换取这件“宝贝”。丁聪可能看出我的心思,他说:“小周,按我俩的关系,这靴子送给你也无妨,不过我头上还戴着‘帽子’,返京后仍需参加劳动,所以我离不开它。”
丁聪离开后,我一直都很想念他。隔了一年,1961年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绕道北京小住数日,由王忠瑜陪同去拜访丁聪。
此时丁聪已分配在全国政协文史组工作,可以在家研究著文。他夫人上班去了,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埋头写作,见到我非常高兴。他指着书房的四壁书架说:“小周,你看我的书比起王观泉如何?”
王观泉是我们编辑室藏书最多的人,抽屉里、书架上全是他的书,其中还有不少珍品。可与丁聪的藏书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由于彼此相熟,谈话比较轻松,时而谈到别后的各自经历,时而又谈到他的藏书。他走近书架,如数家珍地讲述一些书籍的来历和内容,使我获益匪浅。忽然在一本书中翻出一张照片,是毛主席与丁聪亲切握手的画面,丁聪告诉我,那是他从香港刚到北京时,毛主席接见他时的场景。
我惊讶地说:“这照片多么值得纪念呀!”
丁聪说:“值得纪念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他把一件件“宝贝”拿给我看。
首先是一幅毛主席的手迹,在一张宣纸上写着“孙中山先生展览会”几个大字。原来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丁聪设计和布展了“孙中山先生展览会”,会额由毛主席亲笔题写,展览会后丁聪便将它留了下来。我在垦区时曾在尹瘦石那里看到过毛主席题写给柳亚子诗稿的手迹,不过诗稿手迹被中央档案馆收走了。在丁聪家中我第二次看到了毛主席的手迹。赠柳亚子的写得龙飞凤舞,题展览会的则比较端庄凝重,笔体厚实,各有千秋。尤其是这幅题额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名人联结在一起,弥足珍贵。
丁聪接着又拿出一张八寸照片,拍摄的是宋庆龄搂着丁聪脖子的图像,照片上的宋庆龄是个美艳少妇,而丁聪则像是个大孩童似的青年。其实,丁聪那时已在《生活》等进步杂志上屡屡发表作品,业已成名,又参加了抗日爱国团体,宋庆龄当然要像大姐姐似的关爱这个小弟弟了。
接着,丁聪又让我欣赏一件实物,那是茅盾先生为鲁迅先生《阿Q正传》所作的序言原稿。原稿上是茅盾先生用毫笔书写的蝇头小楷,文如其人,非常秀美严谨。《阿Q正传》有多种版本,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读者欢迎的当数丁聪插图本,茅盾就是为丁聪插图本所写的序。
告别时,丁聪送我一本《丁聪漫画集》。这本画册出版于50年代初期,主要是描绘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的题材。丁聪在画册扉页亲笔题词:“小周留念,小丁敬赠。”我看后十分感慨,此小非同那小,小周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而小丁则是丁聪成名成家的笔名。遗憾的是这件纪念品在“文革”动乱时遗失了。
此后我与丁聪再无联系。“拨乱反正”后,我常在报章上见到丁聪的作品和评介文章,我庆幸丁聪能够长寿,能为文坛再作贡献。前年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凭着我和他虽则短短一年,然则过密的交往,本想写些东西以作吊唁,再想吊唁他的人一定很多,未必有人会注意我这个在县级文化馆工作的小人物,但心中一直耿耿于怀。就借着写自己回忆文章之机,寄托一份小周对小丁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