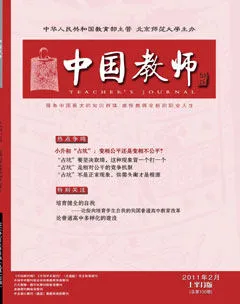真正的学者(中)
2011-12-29于述胜
中国教师 2011年3期
三、道志言情,高扬诗教传统
陈友松自幼饱读诗书,经典之言烂熟于胸。当时虽未见其大用,但在经历了新知的激荡与岁月的发酵之后,它们逐渐积聚成深沉的思想、精神的能量。1942年,他接长成立仅1年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当时正值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学院早创、教学条件极差、学生多思离去”。[1]他上任后,即定宗旨以励学风、延名师以植学基,与师生共辟草莱以广黉舍。方辉盛先生(1922年生)于1945年冬毕业于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他目睹了从湖北省立教育学院至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之历史性跨越;在此跨越中有着特殊贡献的,则是陈友松院长:
价值显于比较,意义显于变化。在陈院长到来之前,当初恩施办大学几乎得不到上级教育部的认可。办起来也不得不小打小闹,起手只有一系一科,没有摆脱乡村师范学院的格局。陈先生来后,专修科开始细胞分裂了:一分为五,又分为八。业务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物质建设全面推进了。到后来,点石成金、水到渠成,跃入国立师范学院的行列。[2]
对于陈友松这样一位大学者来说,此一事功或许只是小试牛刀。但牛刀毕竟是牛刀,虽小试亦凛凛生风。他高扬吾国诗教传统,道志言情、鉴古励今,让沐浴在战火中的湖北教院精神抖擞。
他掌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校门口立起一座牌坊,“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十个颜体大字分列牌坊两侧。寓意深远的十字院训让这所小小的学院拥有了顶天立地、继往开来的文化气概。他还把此一精神,灌注到所撰院歌之中:
大别嵯峨,大江激昂,山川相缪,是我家乡。清江河畔,五峰之阳,唯楚有才,爰胜甘棠。松柏桃李,计划周详,三户壮士,于兹发皇。春风时雨,我院之光,不厌不倦,勿忝勿忘。
筚路蓝缕,摧坚锄强,移风易俗,继绝存亡。立心立命,志大志刚,力行此训,领导发扬。日教日育,学海汪洋,新旧中西,取精用长。春风时雨,我院之光,不厌不倦,勿忝勿忘。[3]
作者以懔懔之心、临云之志,歌家乡山川之壮丽,咏先人功德之峻烈,发继绝存亡、立心立命之宏愿,取春风时雨不厌不倦、新旧中西取精用长之教育精蕴,情深意长,怎能不让歌之者闻鸡起舞!
在校园精神氛围的营造中,开学和毕业典礼自是两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当口。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俞宜瑄(1909-2008年),是陈友松湖北教院时的老同事,她回忆说: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友松院长在教育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笔者特将当时记录下来的友松院长鉴引古语、警策时人的一段话照录于此,以飨读者:“士何事?曰尚志。志何在?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忧天下之忧,‘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和命运!”友松院长的肺腑之言,用意并不仅限于对学生的勉励,同时也是对全院教职员工寄予的期许与厚望。我作为一名学院教师,深受感动,获益匪浅。[4]
他的话语激情志于典坟,让一己的生命与时代的脉搏一齐跳动,本身就如歌如诗。
1943年夏,湖北教院第一届学生毕业。陈友松主持典礼并为《青冰畏言》一文以勉诸生。文章首引荀子“青,取之于兰,而青于兰;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言,更以“变”“胜”“新”三义发明之;继引孔子“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之语,改“畏”字之喜义为忧义,并以毕业即止学、好为人师、博约无当、明变而不知常、知长楚人精神之善而不能救其失五者,力戒诸生;末复展其诗家之才,为联一幅,重为青冰之祝:“以施鹤为会稽,训之若敖蚡冒,勿忘筚路启山林,惟楚有材皆将蔚起;寄黄龙于鄂渚,学彼伏龙凤雏,共抒经纶复省国,时日曷丧我必凯旋。”[5]此联以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激发奋进、复国之大义,深得吾国诗教之精髓,深沉而有力。有此明师,五峰山麓的“清晨、傍晚,三三两两的同学在树荫下诵读古诗文,学习着吟诗作赋……”[6],就不足为怪了。
陈友松先生晚年,积六、七十年之阅历与思考,重述其“五全教育观”,由何光荣先生记于其病榻之前,名曰《我的教育观》[7]。于此“全”之要义,他不仅辩之于其文,亦且证之于其诗。1991年11月12日,他同时完成了两副对联。
一名《外为中用》:
苏格拉底杜威洛克桑代克赫巴特康南特合理取内核
夸美纽斯卢梭皮奈斯宾塞凯洛夫赞可夫辩证为中用
一名《古为今用》:
孔曰学习博文约礼周游列国寻师问老因材善诱过勿惮改爱众成仁毋厌毋倦毋愠铎音宛在
孟乐教育专心尚志私淑诸人称尧道舜知言好辩书不尽信贵民取义不淫不屈不移浩气凛然
尤其是后一联,含英咀华、提要钩玄,把孔、孟的教育精神提点无遗。真可谓“诵先人之清芬”、“采千载之遗韵”(陆机《文赋》语)。而毋厌、毋倦、毋愠和不淫、不屈、不移,早已化作他的人格,成为其情、其志的生动呈现。
四、不移不屈,不变书生本色
陈友松早在博文书院读书期间,即受胡适思想影响;留学菲律宾归来后,又与胡适有过密切的接触;后留学美国,系统地研究了杜威思想,更与胡适有了共同的思想渊源;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北大教授,再一次跟从胡适,成了胡适所创办的“独立时论社”成员。[8]从思想归属来说,他与胡适一样,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推崇民主宪政,主张个性自由、独立思考和社会改良。他也以这样一种形式,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人格独立思想。他出长湖北教院的时候,湖北省主席是国民党要员陈诚。他的学生回忆说:
有一次,在上课中,院长室秘书徐声和先生,到教室向院长报告说:“陈长官来了!”(说完便)退在旁边,听候指示。院长在教材告一段落时问:“他来校有什么事?”徐答:“来校看看。”直到下课铃响,(他)才从容迎宾。陈院长从此又获得“书呆子院长”的外号。
他为了抗拒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专制和政治压迫,愤而辞去院长职务:
我素性习惯于西南联大那种自由的学习空气,不满于恩施的政治气氛和严格的统治。……促使我离去五峰山的导火线是,在一次省城扩大会上,陈诚公开责骂教育学院两个左派学生闹事,当场宣布逮捕这两个学生,使我难堪。我想,这两个青年有什么罪过?我实在难以忍受,一怒之下,向张伯谨(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引者注)提出辞职不干。这样我毅然离开了湖北教育学院。
1945年,“一二•一惨案”爆发后,目睹青年学生惨遭屠戮,他“悲痛凄怆,愤慨激越”,发表《吊潘李二同学》,以“沉沉怨气撼乾坤,白昼狰狞兽食人……五岳三江方怒吼,普天齐吊自由魂”的悲怆诗句,揭露独裁政权的狰狞面目、吊祭青年学生的抗争精神。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学习苏联教育和教育学的高潮中,他虽参与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苏联教育理论,但也深知苏联教育学的利弊得失,故告诫学生“学习苏联教育学的教学原则、方法,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切忌机械搬用……要多读书,要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也要博览各家教育理论。”(P650)在批判胡适、杜威运动中,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陈友松也曾违心地进行过批判和自我检讨,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良心,仍使他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鼓足勇气,对新中国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十分中肯地指出:
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在领导贯彻学习苏联这一不变的基本方针上。教育部门在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的时候,就没有真正体会其精神实质,完全照抄照搬。……
在学术上,教条主义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一棍子打死”的作风。“批判了”三个字好比“推出午门斩首”一样,一切都完了。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篇文章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受到了批判,于是大家都抱不齿的态度。“判”字本身含有判断的意义,而我们却把“判”字理解为判罪,因此就只判罪不判断了。……
过去几年,我们惯于对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学术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惯于骂街或断章取义地引用经典著作来代替我们的独立思考。……[9]
难能可贵地是,他在那个时候就深刻指出了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的内在联系:
凯洛夫(对于苏维埃教育学理论落后于实际的分析)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就是没有深入分析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个人崇拜。凯洛夫是苏联的权威,反对凯洛夫的意见不能存在。[10]
苏联现在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章千篇一律,先是马恩列斯怎么说,然后是马卡连柯、加里宁怎么说,再就是某某娃怎么说,最后作者自己的意见只有一点点。[11]
对于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在此环境下所养成的教条主义空疏学风,他也深以为忧:
“只学了一些苏联的教育学,又是一些条文,他们不懂得中国古代的东西,又不懂得外文,不懂得其他国家的东西,像浮云一样飘在空中,这样没有东西,是架空的。”[12]
这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使他罹祸蒙冤,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不许讲课,只能做文字翻译工作,从一位名教授变成了教学辅助人员。据程舜英先生(1920—2008年)回忆:
1957年7月陈先生被戴上“右派”帽子,又定为“极右分子”。当时我和他是同类。一次教育系命令右派分子开会时,到会的有十几个人,谁也没有说话,我忍不住哭着说:“真冤死了。”这时谁也没有搭茬儿,只有陈先生轻声说:“我们都是这样。”[13]
那轻声作答,表现的是一位学者临大患而不惧的从容与淡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友松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程舜英回忆说:“我曾两次在师大主楼前亲眼看见陈先生被他原来教过的弟子拳打脚踢的场面,亲耳听见陈先生求饶挣扎之声,吓得我不敢近前。一位姓刘的老师曾亲眼看到陈先生被造反派踹倒,不久又起身昂然返家的全部过程。刘老师说,他佩服这位年近七旬的老教授,这才是能担当大事的人。”[14]在其后持续不断的摧残与折磨中,他以非凡的毅力与恶劣环境抗争:
在他刚住进309(北师大四合院北楼的一个过厅,“文革”中造反派把陈友松从工字楼的四室套房发送到这里;他又被迫与自己的家庭分离,独居其中,一住就是10年),还没有全瞎时,竟然买了些彩色乒乓球,按照星座的位置,悬挂在天花板上。然后他就躺在单人床上,仰望星空,自得其乐。挨批斗也有间隙,他常乘看管不严的当口,满北京的跑,去看于谦、文天祥的祠堂,去看利马窦建的宣武门教堂,等等。“吾养吾浩然之气”、“活着就是胜利”,朋友们总是这样互相鼓励。[15]
即便如此,他还日译数千字文稿,直到1973年彻底失明为止。失明后,因已无用,他又被发配到街道居委会、在其监督下劳动改造;且仍一人独居,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生存下来。据他的老学生张渭城、何光荣回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80年代末的一天傍晚,我像往常那样搀扶他从住处下楼到外面散步时他对我谈及的古今圣哲之言,如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养吾浩然之气”,老子教人“为而不有”,庄子提倡“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等等。他说他常反复吟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句话,又说,“我特别欣赏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哲理”。说“那些哲人哲言对我摆脱失明所带来的孤寂感,好处太大了”。这时我才深切感悟到,先生晚年遭此大不幸,而能丝毫未流露消极悲观情绪,原来就是由于他心灵深处有这种高尚的精神寄托![16]
若非高尚其志、与古来圣贤为友,焉能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参考文献:
[1][2][3][4][5][6][7][13][14][15][16]方辉盛,何光荣.陈友松教育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11、641、517、645、519-520、647、473-475、666、667、668、662.
[8]陈友松.检查胡适在教育方面的反动影响和胡适思想对我的影响[J].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