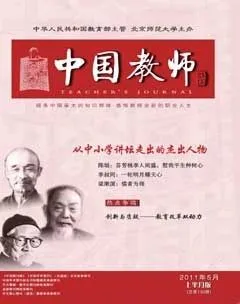陈垣:芬芳桃李人间
2011-12-29李欢
中国教师 2011年9期
编者按:
2010年教师节,温总理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出息,我认为不是这样,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业。”遵循总理讲话精神,《中国教师》将以“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为主线,展现这些历史人物的中小学教师生涯对其本人终身成就的影响,与所有教师共勉。本期推出历史学家陈垣、艺术家李叔同和儒学大师梁漱溟。
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则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的全身像。陈垣,这个在史学界让人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可能会让人们感觉有些陌生。作为一个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胡适、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坊间段子,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陈寅恪就曾说过,他平生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和陈垣,陈垣学问踏实,德才兼优。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棠下镇石头乡(棠下现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和那个时期的众多大家不同,陈垣是靠着《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启蒙的,无师承,自学成才,也没有留学列国的背景。他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饮誉海内外,被学术界誉为“一代宗师”。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教育界的传奇经历,陈垣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年,通观古今中外,有如此长期教育生涯的教育家是不多见的。他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在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担任过教授,并连任了46年的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其培养的人才之多,用他196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今日》一文中的“芬芳桃李人间盛”一语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陈垣先生逝世后,回忆、纪念他的文章有200余篇,其中作者大多是他的学生,而许多已经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或史学界的领导人。
师意: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
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陈垣对启功语
陈垣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坛时年仅18岁,自己还是旧式学馆的学生,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邻里就请他到一家蒙馆教书。彼时的老师,总是在学生背不下书时打手板或打腿,陈垣自己也挨过打,所以对这样的体罚很反感,他教蒙馆后,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欢迎。
1906年,陈垣因在《时事画报》经常发表反清文章而引起了清政府官员的注意。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回到了家乡新会,任篁庄小学堂教员。这是一所新式的乡村小学,他在这里教国文、算学、体操、唱歌、美术等科目。这些课程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很受学生欢迎。放假时,他便常和学生去远足,并采集一些植物标本。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学生们很喜欢这样的新课程,所以他们欢迎我这个从广州来的新教师。”[1]他是小学堂里思想很新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有时腰间还系一条绦带。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即制服),同学们都说他很精神,师生感情很融洽。没多久,广州的风声稍缓和,他便离开篁庄回广州,同学们纷纷前来送行。陈垣晚年曾回忆起江边送别的情景,说:“启程那天清晨,同学们半夜就来到江边送行,船已开了很久,他们还站在黎明的晨曦中,挥帽告别。”[2]55年后的1961年,他在这所小学教过的学生欧阳锦棠,从广州来北京开会,到他家去看望,两人都已经须发斑白,当他们谈起在小学上课、远足的情景时,仍然会完全沉醉在少年的回忆之中。
1913年的春天,陈垣怀着对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美好向往,只身从广州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短暂的政治生涯。但很快地,在参加了所谓的众议院的几次活动后,他逐渐看到了很多过去想象不到的事情:议会成了争权夺利的场所,成了派系夺权、集团牟利、尔虞我诈、置国事于不顾的官衙。推倒了几千年的帝制,换来的却是一批军阀。他们利用民国之名,巧取豪夺;盗得议会名义,以充当自己的工具。
1920年,华北旱灾严重,农民逃亡外乡,北京街头每天都有从外县灾区涌进的大批难民,扶老携幼,缺衣少食。陈垣看到这种惨状,便和朋友们商议,集资办起一所半工半读学校,起名为“北京孤儿工读园”,陈垣担任园长,并负责教务。该园不收任何费用,还供给食宿,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儿得到了较好的照顾,深受社会的欢迎和称赞。3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黎莉莉姐妹,因其父母都参加革命,幼年时就在园内就读。陈垣还为该园题写了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挂在园门两旁。从这副对联中,陈垣关注教育、开办学校之意,可窥一斑。[3]
1920年9月,他又与朋友创办了平民中学,即今北京市第41中学前身,这座中学除招收一部分本市小学毕业生外,大部分收容的是河北灾区逃难到北京的青年。学校不收学杂费,对清寒学生还有补助,这使得许多小学毕业无力升学的学生,也得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陈垣自己任校长,兼教国文、历史,包括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中国文学史这个课,是他在别校从未教授过的。而当时的平民中学,也因其授课出色、纪律严明,在北京的中学里鹤立鸡群。[4]
1921年,陈垣还担任了教育部次长(即副部长),但是在旧政府工作的经历让他觉得筋疲力尽,常常事与愿违,件件事情都不易推动,理想的实现更是遥不可及。经过观察和体验,他认为当时的政治是“肮脏的”,也更加坚定了他“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的人生观,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教书育人、读书治史的道路。
师心: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
陈垣身上有着很强的战斗因子,他反抗过清朝、北洋军阀和日伪政权,除了在报纸杂志上对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口诛笔伐之外,陈垣还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融入到了教育事业当中。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扬“品行第一”。在辅仁大学的返校节上,陈垣给大家讲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礼记》有一节是讲孔子主持射箭比赛的事情,让谁把门呢?弟子子路。孔子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一种是败军之将,一种是为敌人做事情的,一种是认敌为父的。很多汉奸听了以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敌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