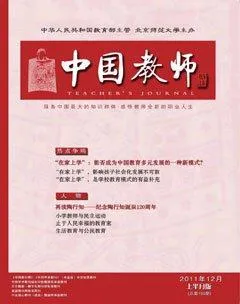止于人民幸福的教育家
2011-12-29储朝晖
中国教师 2011年23期
1891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钟灵毓秀皖南黄潭源村诞生。对现实生活中贫病与痛苦的切身体验使他产生行医济世思想,参与辛亥革命地方议会与武装暴动的经历以及金陵大学的学习生活,使他开始思考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终成为医治人心而非人身的教育巨匠。
一、止于人民幸福选择终生从教
陶行知在人生中选择教育,是由于他主张民主共和,反对专制横威,认为“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主张共和应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之机会,谋国民全体之福利,应“视人民为社会之主体”,而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程度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一党自画”的党祸难防、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出现,陶行知把防止共和险象的目光投向了教育:
“避之之道唯何?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但其为可教,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关键在于清除专制荼毒,启发人的自觉,反对施行愚民政策。他在美国留学原本学的是政治学并在伊利诺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当他进一步认识到学习市政将来只能做官,不能真正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在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官员,于是便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进一步坚定了他献身教育的人生目标。
1915年12月,他写信给黄炎培,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定向,询问中国教育最急要的问题。黄炎培回复称这也是自己“棖触于心,极愿掬以奉告者,盖江苏最急要之问题,无过于教育与职业之联络”,慨叹当时“所谓教育者,不惟不能解决世界最重要之生计问题,且将重予生计问题之困难”,引发陶行知对职业教育的系统思考而写成《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
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致罗素院长的信中道:“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陶行知亲身参与过的武装起义和议会工作让他感到新建民国犹如聚沙成塔,存在着种种严重缺陷,单纯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此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教育而非军事,唯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
1917年8月,陶行知离美回国,在轮船上和同学们畅谈志愿时豪迈地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介书生,无钱无权无势,却立下如此宏愿,实令人惊诧,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毕生始终不渝地朝这个目标去做。他抱着建立民主共和中国的宏愿改造教育,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以试验为根本方法,先后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
二、止于人民幸福创立生活教育理论
在教育实践中,陶行知感到旧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是吃人的教育,它不只叫人吃别人,还教人吃自己,是不可能创造人民幸福的,因此不仅要提倡新教育,还要建立新的教育理论。因而他主张叫人创造幸福的生活教育,它要教人做人,教人生活,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它要教民众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
这种新教育理论是为了适应建立“富而强的共和国”的需要,一方面要培养好领袖,另一方面要培养新国民。其目的一方面使学生具有利用自然界的能力,一方面谋人类共同的幸福。于是他大力倡导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以实现师生选择得当,“教学咸得其宜,则国家造就一生利人物,即得一生利人物之用。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他倡导男女同学,认为在社会无法大量设立女子学校的情况下,以求精神粮食为喻反问那些反对者:“既不能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
在晓庄学校建立三周年纪念日,陶行知发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提出:“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有了爱便不得不去找路线,寻方法,造工具,使这爱可以流露出来完成他的使命。”于是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行是知之始、政富教合一的理念在试验中逐渐建立,社会的中心问题便成为学校的中心问题,生活教育是教人做工求知识管政治的教育。我们共同的使命便是教导乡下的阿斗做国家的主人,“凡是凭着特殊势力,以压迫人民,致民之欲不得遂、民之情不得达的,都是我们的公敌”,要负起这个使命,不能不有特殊的修养:一是自立与互勉,做人中人;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立法,共同守法;三是自由与纪律,晓庄不但是平等之乡,而且是自由之园,学园的成立由园长选同志,同志选园长,试验自由是各学园的础石;四是大同与大不同,晓庄是一个“人园”,在这里面的人都能各得其所,现出各人本来之美,以构成晓庄之美,现出一种和谐的气象。而非要找出一个人中的模范教一切人都学成他一样,晓庄的同志要创造出和晓庄大不同的学校才算是和晓庄同,才算是第一流的贡献。最后指出:“乡下阿斗没有出头之先,我们休想出头。乡下阿斗没有享福之先,我们休想享福。我们若是赶在农民前面去出头享福,只此一念,便是变相的土豪劣绅。与农人共甘苦,共休戚,才能得到光明,探出出路。”
1930年1月16日至2月7日,晓庄学校举办乡村教师讨论会,陶行知在会上演讲《生活即教育》,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生活教育理论,倡导康健、劳动、科学、艺术、改造社会的教育,过有计划的生活,就是有计划的教育,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社会即学校”是说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主张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顺民之意,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生活即教育是要解放人类的,“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
1936年6月1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3卷7期发表《新大学》,明确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并将大德定义为觉悟、联合、争取解放。1944年7月,在育才学校创建五周年之际,陶行知写文再次强调“止于大众之幸福”,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大德不能小于“天下为公”。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人民的亲人,是必须亲近,打成一片,并肩作战。“一切所教所学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
1939年3月1日,生活教育社总结12年来所做的三件且尚未做完的事: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这种教育必须是战斗的、生活的、科学的、大众的、计划的。强调:“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1940年3月10日,陶行知给白桃写信道:“在一般的生活里,指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把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1941年6月11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讨论会上强调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不可分,指出生活教育的远景是建立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近景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2年3月15日,陶行知理事长报告15年来推行生活教育的动人的故事后,说生活教育一向有而未曾公开的两个朋友:一位是贫穷,一位是患难。并以“友穷、迎难、创造”六个字与大家共勉,一切为创造,创造为除苦。1944年6月,陶行知总结育才五周年的五条优良传统为:奉头脑作总司令;止于大众之幸福;全校团结成一个巨人;虚心,虚心,虚心,承认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建立起健康的堡垒。
1945年1月28日,陶行知在四川壁山县国立教育学院演讲《创造的社会教育》,再次阐明了新大学之道。认为“新民”有给老百姓洗澡的意味,因而要亲民,与老百姓站在一条战线上,同甘苦,共患难,说出老百姓心中所要说的话,教老百姓,与老百姓共同创造。大众之幸福包括福禄寿喜,要止于大众之幸福,就必须解放老百姓的创造力。解放他们的双手、双眼、嘴、头脑、空间和时间。民主时代的创造,是给每个人以同等的创造机会,是动员整个民族力量以创造民众的福禄寿喜的。民主程度愈高,则创造愈开放、愈好。
1946年1月2日,陶行知撰写《社会大学运动》,系统阐述“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课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的主张。
三、止于人民幸福倡行民主教育
陶行知意识到中国“人民还没有受到过民主教育”,所以今后没受过教育与受过教育的人都要来上民主第一课,“政府应该还教育于民!”
陶行知从平民中走出来到美国留学,成为大学教授,早年艰苦求学以及受助于人的经历养成了他助人为乐的品质,也奠定了为民立言的思想基础。新文化及五四运动使平民思想深入人心,陶行知决心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也要打通深沟竖垒的纵阶级,使人人受到平民教育。
陶行知主张学生要通过自治学习民主,认为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能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有自己立法、执法、司法的意思。自治的重要性在于“养成共和的人民,必须用自治的方法”,“自治可以养成我们对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才力”,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学生自己共同所立的法,比学校里所立的更加尽情,更加易行,而这种法律的力量也更加深入人心”,能适应学生的需要;学生自治还能辅助风纪之进步,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要避免将学生自治当做争权的器具,不可误作治人,不是与学校对峙,不可闹意气,因此应有相应的范围和标准。
1919年3月陶行知在《新教育》第1卷第2期发表《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系统分析德国的教育变革,肯定它在打消旧宗旨的同时,一面提倡平民主义,一面脱离宗教的束缚,取消分阶级的学校,实行男女同学,注重学问自由。进而他将眼光转向通过日本模仿德国的中国教育上道:“最重军国民主义的阶级制度的学校,一变为平民的共和的学校,岂不是世界的一个大大的幸福么?现在这军国阶级主义的祸根,既然为一阵狂风拔得干干净净,我很希望他在东亚的枝叶,不久也要凋落了;我更希望当这军国、阶级两主义凋落的时候,那抄袭德国精神的国家也能回心转意,培植平民主义的教育,使他能够开花结果,为东亚放一异彩。”这段话讲德国的事实,盯着日本的走向,关注中国现实,寓意极为深刻。
1944年4月1日,陶行知发表《创造的儿童教育》,呼吁创设民主的环境发挥人的创造力,他指出民主应用在教育上有三个最要点:教育机会均等、宽容和了解、在民主生活中学民主,强调“专制生活中可以培养奴才和奴隶,但不能培养人做主人……只有民主才能解放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陶行知在《新华日报》上发文认为民主政制下的教育应具备的条件是:天下为公,教育为公,不以教育为一党一派及任何小集团谋利益;尊师重道,不以侦探作教员,不使教员兼侦探;使师生之间没有隔阂;使学生打开眼睛看事实;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校内团体生活,要有民主的组织使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更进步之民主;动员广大民众,在真正民主的组织生活中学习真正的民主。指出思想统制与追求真理不能相容,统制的“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想消灭,统一于愚”。
陶行知主张民主教育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管